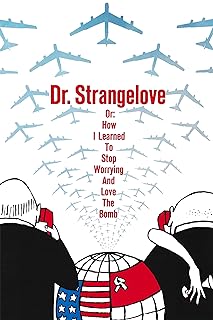電影訊息
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
編劇: Peter George (Ⅲ) 史丹利庫伯力克
演員: 彼德謝勒 喬治史考特 史特林‧海登 Keenan Wynn
奇爱博士/密码114(港)/奇爱博士或者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
導演: 史丹利庫伯力克編劇: Peter George (Ⅲ) 史丹利庫伯力克
演員: 彼德謝勒 喬治史考特 史特林‧海登 Keenan Wynn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6-08-17 19:14:28
重提瘋癲與文明
重提瘋癲與文明
——評《奇愛博士》、《發條橙》和《飛越瘋人院》
福柯自有《瘋癲與文明》一書,而結合福柯異於常人的性傾向來看,也許真的有很多不明就裡的人會認為福柯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瘋子。可是,要知道《瘋癲與文明》本質上是一部歷史學著作,而福柯的哲學思考,或者說他人對福柯及其理論的哲學解釋,都是基於歷史而言的。然而要在中國的語境下去理解福柯所敘述的瘋癲與文明的關係史,幾乎很容易產生偏差,尤其是只有印刷文本的情況下。因為中國並沒有瘋人院,或者說精神病院的歷史,要說有,那也是20世紀的精神病院,這與西方漫長的處理「瘋人」的歷史相比,是小巫見大巫。所以,當一位不研究西方的中國人提到「瘋狂」這個詞時,貶抑的含義是會首先進入他或她的腦海的。在中國考察「瘋」一字,恐怕沒有一段與之相關的歷史。《集韻》稱「瘋」為頭風病,即腦血栓之意。以「瘋」指稱「精神錯亂」,怕是20世紀之後的含義,說不定也與東亞某國的語言有關。而到近些年,我們學著西方,把一些中性的含義也加入了「瘋」一字,指做事的反常。這便慢慢接近西方語言了。另外,「癲」字更常見地是與「瘋」同義,而自近代以來也逐漸包含了「不羈」的意思。福柯在他的瘋癲歷史書中,講述了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的西方「文明社會」對「瘋癲」以及「瘋癲之人」的看法的流變,正如我剛才所說,這並未在「例外的例外」的中國土地上出現。
進入21世紀,影像文本開始廣泛參與「文化研究」。所謂「文化研究」,想必反映了博學的大師們,對人文領域的一切現象進行考察的夢想。文化研究者的一個預設是,某一現象絕非單純的哲學的、歷史的、文學的或社會學的現象,它必定為各方面因素聯動的結果,任意一方面因素的單獨解釋都是不完美的,都不能揭示這一現象的「真實」。因此,它們致力於讓自己博學,於是影像文本便成為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對象之一。在拙文中將要提及的三部影片,《奇愛博士》(1964年)、《發條橙》(1971年)和《飛越瘋人院》(1975年),除了第一部,想必都是文化研究者不應遺漏的文本吧。筆者不願意,也沒有能力成為一位博學的文化研究者,只是希望在拙文中胡亂書寫一些小感想,其拋磚引玉之功,便是想讓文化大家們略略回頭,你們是否在考察過去的現象時也不應忽視影像文本呢?
《飛越瘋人院》的英文原名大意是「飛越杜鵑巢之人」,將「杜鵑巢」譯為瘋人院,是一個並不非常聰明的做法。儘管字典上很明白地寫著,「杜鵑」在某些情況下就是指「缺乏理智、愚蠢、瘋狂」,不過我想不是每位觀眾都會去翻字典的。和拙文主題聯繫最緊密的也就是此片,它直接地將故事設置在一家精神病院之中。很多時候我們還是會把取難而舍易,認為精神病院就是一個社會,或者說一個政府,病人就是社會中的被政府所管轄的個體。這樣想沒有問題,但是,影片所表現的精神病院的規則,並沒有太多的誇張和虛飾——就應該如此(網上某篇影評認為此片表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精神病院的罪惡」)。我們不應在還未弄清楚精神病院和病人本身關係之前,就開始大談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個人的問題,然後去聯繫捷克裔導演佛曼「布拉格之春」後的逃亡。
是精神病院認為病人是有精神問題的嗎?理解影片之後,我們會得到否定的答案。首先,除了麥克墨菲,其他病人幾乎都是自願來到醫院接受治療的。其次,從某種意義上說,麥克墨菲也是自願前來的(裝病),他的個人特殊性在於他在來之前是一名罪犯,因此他終究無法「想走就走」。第三、醫院無法確定麥克墨菲是患病的,所以他們才將他留下繼續觀察。這樣,精神病院是影片中包括麥克墨菲的所有人的避難所,只是因為麥克墨菲本身有著強烈的個性,所以他儘管逃避了監獄中的繁重勞動,但並沒有在醫院中獲得滿足。麥克墨菲的個性和身份是為了情節發展而設定的,是一種偶然性的因素。要分析瘋癲,我們的關注點就不應在麥克墨菲身上: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認為自己發生了精神錯亂。而那些像哈定、比利之類的人物,他們自己覺得自己不正常,這才是關鍵所在。
讓我們暫停一下,跳到《發條橙》一片上。筆者認為此片最能揭示中心的一句台詞,是在影片第二部份的結尾處。那裡,主角亞歷克斯接受了研究所的心理治療,從而對暴力和性產生了極度的厭惡。嘗到這項心理治療計劃的內政部長弗雷德里克認為,痊癒的人們將不再使他人受難,而是永遠使自己受難——人人都將被拯救,人人都將是耶穌。可惜的是,目前只有亞歷克斯一人得到了「拯救」,如果世界上只有他一位神靈,那麼他的結果就是被惡魔所擊垮。當然,影片最後讓亞歷克斯這位現代世界的耶穌如聖經故事所述一般復活了,那麼,如同老年黑人所說的失卻法律和秩序的骯髒的現代世界,就因耶穌的死而警醒了嗎?影片的結束畫面仍然是性愛,受人們所鼓勵和支持的性愛。內政部長的得意的「消滅犯罪」的計劃,在舞台上就差點為一名似乎反對黨政治家的發言所完全駁倒。這名反對黨說,亞歷克斯現在已經沒有任何選擇了,尤其是沒有道德上的選擇,他無法選擇去從善或者從惡。反諷的是,不論是內政部長還是亞歷克斯自己,亞歷克斯走出研究所的時候,都不斷地暗示:從現在起,你自由了。顯然,影片希望說明的是,當道德標準也成為政府的統一政策時,那人們就真正是被上了發條了。
回到瘋人院。瘋人院是政府或者社會,或者說「文明」所設立的,歷史地看,瘋人院中的瘋人便是「不文明」的人。亞歷克斯被強制送到監獄或者研究所去「文明化」,而哈定和比利則自願地或半自願地進入醫院接受「文明化」。如果後者不進入醫院,那麼他們會被「文明」看作「不文明」的人,最終的結果也是強制性的。觀眾可能還記得這樣一個場景。麥克墨菲問拉契德護士,他能不能不吃藥,搞特殊。拉契德護士回答他說,他不自覺吃藥,醫院自然有辦法強制他吃藥。在《飛越瘋人院》的整個劇情中,麥克墨菲始終在抵制醫院的治療,但他沒有一次是能戰勝醫院的警衛而按照其自由意志行動的。那麼,「文明」所認為的瘋癲與不瘋癲之間的界線是什麼呢?正如福柯所說,一切都是理性惹的禍。自文藝復興時期到19世紀,瘋人的悲慘史決不能怪罪於某一特定的社會或政府,而是應該讓理性,還有秉持理性理想的人們進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可以這麼說,沒有理性,就沒有瘋癲的歷史。
理性本身是無罪的,理性也不負有原罪。但在瘋癲史上,為何理性如同魯迅筆下的禮教一般吃人了呢?在《發條橙》和《飛越瘋人院》兩部影片中,我們都深深地為不理性的罪犯和病人們同情。我隨機問過一些《飛越瘋人院》的觀眾,問他們:拉契德護士是正面角色還是反面角色?回答都是反面角色。然而,理性沒有錯,同時理性也不能被迷信。犯罪難道不應該被打擊嗎?如果不是,那為什麼幾乎所有觀眾都會在《發條橙》中的暴力和強姦式或濫交式性愛鏡頭感到不適?影片的第三部份瀰漫著深深的憂慮和思考,到底應該讓「文明」去為人們選擇理性,還是讓人們在犯罪之前自覺地選擇理性?這種自覺性是否可能?也許,自願進入瘋人院的那些病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是自覺的了,但是他們在進入醫院之前已經對社會造成了某種危害和混亂,所以這裡的自覺並不完全。印第安人最後成功逃出醫院,奔向未知,我們仍然沒有看到答案。
答案在《奇愛博士》之中嗎?影片很短,一群「瘋狂」的人們將人類文明導向毀滅。影片的反戰主題十分明顯,然而,核戰爭的爆發原因卻是荒誕的。片中,美國總統可能認為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已進入瘋癲狀態,殊不知,對蘇聯實施核打擊的作戰制度卻是通過「民主」討論後得出的,美國總統也參與了這些討論。因此,民主也並不意味著根本的理性,否則,「理性」的美國總統也不至於很難挽回嚴重的後果。也許,里帕將軍的過於敏感和性問題確實讓他不會理性;也許,奇愛博士對世界末日和人類毀滅和地下生活的嚮往使他看起來是最不理性的一個人;可是,世界末日的到來卻不僅僅來自於這兩個人的衝動和科學技術,也不僅僅來自於美國人民的民主制度所造成的無可挽回的核攻擊計劃,而是還要加上會被自動觸發的蘇聯人的「末日武器」。如果將世界濃縮為冷戰時期的兩個超級大國,那麼人類的毀滅竟然是人類自己導致的,也就是說,自殺,這一永遠被定義為瘋狂的舉動的動機,竟然是大多數人的不瘋狂、大多數人的理性。
綜合三部影片看,理性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理性首先無法為人類自覺地選擇,而強制地灌輸理性則是不理性的;另一方面,大多數人的理性甚至有可能導致世界末日,而非烏托邦。三部影片的拍攝年代距今已有三十年,今天的我們重提理性的話題,但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理性的人已經變少了。在這個連思想都是可以被消費的時代,人類能夠從財富的汪洋之中探出頭來,靜心凝望頭頂的星空並敬畏之嗎?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