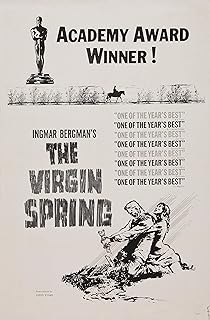電影訊息
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
編劇: Ulla Isaksson
演員: 麥斯馮西度 Birgitta Valberg 岡紐爾琳德布魯姆 Birgitta Pettersson Axel Duberg
处女泉/TheVirginSpring/处女泉
導演: 英瑪柏格曼編劇: Ulla Isaksson
演員: 麥斯馮西度 Birgitta Valberg 岡紐爾琳德布魯姆 Birgitta Pettersson Axel Duberg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7-03-26 04:37:00
處女泉
瑞典1960年出品
編劇:烏拉•伊薩克森
導演:英格瑪•伯格曼
攝影:斯文•尼克維斯特
主要演員:馬克斯•馮•席度(飾特利)
伯吉塔•瓦爾伯格
阿倫•艾德沃
故事取材於瑞典十三世紀時的歌曲。講述了十六世紀瑞典一處偏僻鄉下的一個春天的早晨,農場主特利讓女兒卡琳去為教堂送做彌撒用的蠟燭,這是只有貞潔的處女方能做的工作。於是卡琳和女僕英格麗一同啟程前往。
途中她們來到一處樹林,碰到了一個古怪的老人,英格麗由於受到老人的誘惑加上自身的恐懼而不敢繼續前往。而堅定的卡琳卻決定繼續獨自上路。在路上卡琳遇到了三個牧羊人,開始他們談得很開心,但是後來他們卻強姦了卡琳,並打死了她,將她的衣物搶走。而尾隨而來英格麗則躲在暗處嚇得不敢出聲。
到了黃昏,三個牧羊人來到卡琳家,由於天色已晚,主人家同意收留他們借宿,並招待了他們。然而臨睡前,牧羊人卻向特利的妻子兜售起卡琳的披肩來。特利的妻子認出了女兒的東西,她忍住悲痛,假意說要與丈夫商量,然後將牧羊人鎖在屋內,接著她叫醒了特利,特利立即明白過來,他決心復仇。而此時英格麗也回來了,她證實了這一切,於是,特利在清晨舉行了一個異教儀式後殺死了三個牧羊人。天亮後,英格麗帶著特利夫婦找到了卡琳的屍體,特利發誓要在女兒的屍體處為上帝建造一座教堂,但就在他們抱起卡琳時,從卡琳的頭下的地上冒出一眼泉水來。特利夫婦認為這是上帝的施恩。
從《第七封印》到《處女泉》再到「沉默三部曲」(即《猶在鏡中》、《冬日之光》、《沉默》),英格瑪•伯格曼一直在思索同一個問題——上帝是否存在?而本片正是伯格曼對於上帝存在與否的一次質疑。本片取材的是瑞典十三世紀的歌曲,這本身就使故事幪上了一種傳奇性的色彩。影片以一種近似於神話故事的結構講述了一個關於復仇與救贖的故事。而上帝存在與否是這個故事矛盾衝突的主題。從本片中我們可以看出伯格曼對上帝提出了質疑。這表現在上帝在整個事件中始終扮演著一種旁觀者的角色,只是到最後的神蹟才表明它的存在,而這神蹟也僅僅是特利夫婦認為是上帝顯靈而已。這時的伯格曼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質疑上帝為什麼會縱容罪惡的發生,讓無辜少女死去,又讓少女的父親因為復仇而沾上罪孽。但另一方面,他卻對上帝這種行為不是報以指責(這些都是通過特利來表現出來),而是以一種贖罪的態度乞求上帝的寬恕。而最後的泉水湧出也有了洗清全部的罪孽的意義,通過這樣與上帝達到一種內在的平衡。在這裡伯格曼仍是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只是他對此產生了質疑。
這部影片不同於伯格曼其它著名的影片那樣在結構與形式上充滿了複雜的隱喻與奇怪的夢境,而是簡單得如同一首詩。也許正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神話,因而伯格曼就這樣平靜地為我們講述了這個神話故事。伯格曼曾說過:「沒有什麼藝術比音樂更接近電影,二者都直接影響我們的感情,而不是通過理智。」他又說:「電影的第一性應該是音樂性。」這也體現在他的影片幾乎從來不用配樂,而只是在影片開頭放一段音樂(大多是巴赫的,巴赫成為他永遠的精神合作者,拯救者,撫慰著他痛苦的靈魂)。在他的影片中大都是直接採用自然聲,他認為真正的音樂在於大自然中,任何風吹草動,蟲鳴蟬唱都是音樂。也正是這樣,他的影片總給人一種樸素、自然之感。而《處女泉》則是在他所有影片中可能是最為安靜的一部,不論從畫面還是對聲音的使用上來說,都給人一種莊重、樸素、寧靜的感覺。伯格曼通過這樣一個方式向我們講述了一則神話故事,而一切的思考都通過故事傳達給觀眾。
影片從結構上可以分為四個部份:即開頭事件起因——途中遇難——發現真相復仇——出現神蹟。本片雖然並不復雜,但伯格曼仍使用了許多隱喻,好在這些隱喻並不是十分複雜難懂。如開始出現了火,然後下個鏡頭就是女僕英格麗在詛咒卡琳,期望奧丁神降罪於她,而在這裡奧丁神是屬於北歐神話的異教神(相對於基督教而言),而此後每當英格麗嫉妒卡琳時,幾乎總會有火出現。這裡火成為英格麗對卡琳貞潔、美麗、快樂相對於她自己的卑微、不貞的嫉妒的象徵。還有那隻被英格麗夾在卡琳食物中的蟾蜍也表現出了她的嫉妒,而當三個牧羊人想強姦卡琳時那隻蟾蜍從食物中跳出來與他們相對,這更襯托出人性的醜惡勝於外表醜陋的蟾蜍,有意思的是這隻蟾蜍當時也是與英格麗相對,而她才將蟾蜍夾進食物的,這更體現出英格麗不敢面對自己醜陋的內心。而在林中誘惑英格麗的老者似乎就是奧丁神的化身,同樣篤信上帝的卡琳就沒受誘惑,而是獨自前行。通往教堂之路可以視做朝聖之路或通往上帝之路,而奧丁和樹林則像徵了這條路上誘惑人的魔鬼,顯然英格麗受了誘惑,這也表現出了她信仰的搖擺與不堅定,而這點在三個牧羊人身上也得到了體現,當卡琳在分完食物準備做祈禱時,除了最小的那個牧羊人外,另外兩個都迫不及待地吃了起來,這體現了他們的無信仰與信仰缺失。「上帝」在影片中始終在觀望著,從卡琳要走很遠才能到達教堂可以看出上帝離人類是多麼的「遠」。而當特利復仇時他似乎在行使上帝的權力,人的意志與神的意志被互換了。但反過來說這也可以被視為上帝對人類的考驗,通往上帝的道路是艱辛的,甚至是令人沮喪的。所以從中可以看出伯格曼對待上帝的態度是矛盾的,他仍在這條道路上苦苦思索。
而在影片的所有人中,只有卡琳才是真正值得歌頌的,她也是唯一沒有受到上帝懲罰的人,雖然她失去了貞潔與生命,但這更可以視做是通過自我犧牲來完成的救贖而達到與上帝精神上的和諧。雖然她在這條通往上帝的道路上蒙難了,但從最後的泉水中我們可以看出她犧牲的意義,她為世人洗清了罪孽而換得了上帝對他們的寬恕。她被牧羊人殺死而具有的意義也似乎與耶酥這「天生的羔羊」的命運相符。伯格曼通過卡琳這個角色對耶酥的犧牲做出了思考。反過來我們再來看下其它人,特利因為復仇而使自己幪上了罪,從他殺人前的那場異教的儀式可以看出他強烈的憤怒與痛苦以及他對上帝的懷疑,以致於要依靠異教的儀式才能鼓起復仇的勇氣,但同時他這樣卻無法面對上帝。特利的妻子由於對女兒的溺愛而對女兒與父親的愛產生了嫉妒,而懲罰她的是她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英格麗由嫉妒產生的種種行為以及她後來陷入痛苦的懺悔,將卡琳的死歸結於自己的詛咒,她已經在精神上受到了最大的懲罰。而三個牧羊人中年長的兩個用死亡償還了他們對上帝的不敬,最小的那個在事後由於恐懼而幾乎崩潰,而他也最終難逃死亡的命運。伯格曼以他特有的冷酷為人與上帝的關係劃上了這樣的句號。但隨即又提出了新的問題:「如果自我犧牲能洗清已犯下的罪孽,那麼人類原始的罪惡又該如何洗清?」雖然他用卡琳的犧牲在表面上完成了為他人的贖罪,與上帝達到了和諧,然而質疑仍在繼續。
本片的攝影是個不得不提的人物,他就是瑞士人斯文•尼克維斯特。而從本片開始,他也開始了與伯格曼的長期合作,成為伯格曼的御用攝影師。他高超的攝影技巧與伯格曼的主題完美的結合在了一起。如卡琳與英格麗去教堂途中的多個全景、大全景鏡頭的使用體現了斯文高超的運鏡水準。攝影機的移動輕靈飄逸,使畫面如同田園畫般寧靜莊嚴。而到了特利接待以及殺死三個牧羊人時,畫面儼然有一種審判之感。而最後特利質問上帝時攝影機更是從演員背後去拍攝,更給人一種強烈的感情衝擊。同時本片繼承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瑞典學派所開創的北歐自然主義的拍攝風格(尤其以伯格曼的老師史約斯特羅姆的《風》為代表)。環境在影片中被賦予了同影片角色同樣重要的含義,無論是風、水、樹木這些最普通不過的事物都變成了對人物內心狀態的外在反應。如最典型的特利使用異教儀式時風吹大樹的段落里,風與樹都將特利內心的緊張與矛盾成功的視覺化(外化)了,將人與環境的關係有機的結合到一起,給環境賦予特殊的意義。
伯格曼這個偉大的思想者終其一生都在思索著幾種伴隨現代人的關係,「人與神的關係。上帝是否存在?人與人的關係,交流是否可能?愛與恨的關係,愛恨是否並存?生與死的關係。生命是否有意義?」而他的影片也執著地為如何解決現代人最大的精神疾病「孤獨」尋找答案。
《處女泉》獲得了1960年美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編劇:烏拉•伊薩克森
導演:英格瑪•伯格曼
攝影:斯文•尼克維斯特
主要演員:馬克斯•馮•席度(飾特利)
伯吉塔•瓦爾伯格
阿倫•艾德沃
故事取材於瑞典十三世紀時的歌曲。講述了十六世紀瑞典一處偏僻鄉下的一個春天的早晨,農場主特利讓女兒卡琳去為教堂送做彌撒用的蠟燭,這是只有貞潔的處女方能做的工作。於是卡琳和女僕英格麗一同啟程前往。
途中她們來到一處樹林,碰到了一個古怪的老人,英格麗由於受到老人的誘惑加上自身的恐懼而不敢繼續前往。而堅定的卡琳卻決定繼續獨自上路。在路上卡琳遇到了三個牧羊人,開始他們談得很開心,但是後來他們卻強姦了卡琳,並打死了她,將她的衣物搶走。而尾隨而來英格麗則躲在暗處嚇得不敢出聲。
到了黃昏,三個牧羊人來到卡琳家,由於天色已晚,主人家同意收留他們借宿,並招待了他們。然而臨睡前,牧羊人卻向特利的妻子兜售起卡琳的披肩來。特利的妻子認出了女兒的東西,她忍住悲痛,假意說要與丈夫商量,然後將牧羊人鎖在屋內,接著她叫醒了特利,特利立即明白過來,他決心復仇。而此時英格麗也回來了,她證實了這一切,於是,特利在清晨舉行了一個異教儀式後殺死了三個牧羊人。天亮後,英格麗帶著特利夫婦找到了卡琳的屍體,特利發誓要在女兒的屍體處為上帝建造一座教堂,但就在他們抱起卡琳時,從卡琳的頭下的地上冒出一眼泉水來。特利夫婦認為這是上帝的施恩。
從《第七封印》到《處女泉》再到「沉默三部曲」(即《猶在鏡中》、《冬日之光》、《沉默》),英格瑪•伯格曼一直在思索同一個問題——上帝是否存在?而本片正是伯格曼對於上帝存在與否的一次質疑。本片取材的是瑞典十三世紀的歌曲,這本身就使故事幪上了一種傳奇性的色彩。影片以一種近似於神話故事的結構講述了一個關於復仇與救贖的故事。而上帝存在與否是這個故事矛盾衝突的主題。從本片中我們可以看出伯格曼對上帝提出了質疑。這表現在上帝在整個事件中始終扮演著一種旁觀者的角色,只是到最後的神蹟才表明它的存在,而這神蹟也僅僅是特利夫婦認為是上帝顯靈而已。這時的伯格曼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質疑上帝為什麼會縱容罪惡的發生,讓無辜少女死去,又讓少女的父親因為復仇而沾上罪孽。但另一方面,他卻對上帝這種行為不是報以指責(這些都是通過特利來表現出來),而是以一種贖罪的態度乞求上帝的寬恕。而最後的泉水湧出也有了洗清全部的罪孽的意義,通過這樣與上帝達到一種內在的平衡。在這裡伯格曼仍是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只是他對此產生了質疑。
這部影片不同於伯格曼其它著名的影片那樣在結構與形式上充滿了複雜的隱喻與奇怪的夢境,而是簡單得如同一首詩。也許正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神話,因而伯格曼就這樣平靜地為我們講述了這個神話故事。伯格曼曾說過:「沒有什麼藝術比音樂更接近電影,二者都直接影響我們的感情,而不是通過理智。」他又說:「電影的第一性應該是音樂性。」這也體現在他的影片幾乎從來不用配樂,而只是在影片開頭放一段音樂(大多是巴赫的,巴赫成為他永遠的精神合作者,拯救者,撫慰著他痛苦的靈魂)。在他的影片中大都是直接採用自然聲,他認為真正的音樂在於大自然中,任何風吹草動,蟲鳴蟬唱都是音樂。也正是這樣,他的影片總給人一種樸素、自然之感。而《處女泉》則是在他所有影片中可能是最為安靜的一部,不論從畫面還是對聲音的使用上來說,都給人一種莊重、樸素、寧靜的感覺。伯格曼通過這樣一個方式向我們講述了一則神話故事,而一切的思考都通過故事傳達給觀眾。
影片從結構上可以分為四個部份:即開頭事件起因——途中遇難——發現真相復仇——出現神蹟。本片雖然並不復雜,但伯格曼仍使用了許多隱喻,好在這些隱喻並不是十分複雜難懂。如開始出現了火,然後下個鏡頭就是女僕英格麗在詛咒卡琳,期望奧丁神降罪於她,而在這裡奧丁神是屬於北歐神話的異教神(相對於基督教而言),而此後每當英格麗嫉妒卡琳時,幾乎總會有火出現。這裡火成為英格麗對卡琳貞潔、美麗、快樂相對於她自己的卑微、不貞的嫉妒的象徵。還有那隻被英格麗夾在卡琳食物中的蟾蜍也表現出了她的嫉妒,而當三個牧羊人想強姦卡琳時那隻蟾蜍從食物中跳出來與他們相對,這更襯托出人性的醜惡勝於外表醜陋的蟾蜍,有意思的是這隻蟾蜍當時也是與英格麗相對,而她才將蟾蜍夾進食物的,這更體現出英格麗不敢面對自己醜陋的內心。而在林中誘惑英格麗的老者似乎就是奧丁神的化身,同樣篤信上帝的卡琳就沒受誘惑,而是獨自前行。通往教堂之路可以視做朝聖之路或通往上帝之路,而奧丁和樹林則像徵了這條路上誘惑人的魔鬼,顯然英格麗受了誘惑,這也表現出了她信仰的搖擺與不堅定,而這點在三個牧羊人身上也得到了體現,當卡琳在分完食物準備做祈禱時,除了最小的那個牧羊人外,另外兩個都迫不及待地吃了起來,這體現了他們的無信仰與信仰缺失。「上帝」在影片中始終在觀望著,從卡琳要走很遠才能到達教堂可以看出上帝離人類是多麼的「遠」。而當特利復仇時他似乎在行使上帝的權力,人的意志與神的意志被互換了。但反過來說這也可以被視為上帝對人類的考驗,通往上帝的道路是艱辛的,甚至是令人沮喪的。所以從中可以看出伯格曼對待上帝的態度是矛盾的,他仍在這條道路上苦苦思索。
而在影片的所有人中,只有卡琳才是真正值得歌頌的,她也是唯一沒有受到上帝懲罰的人,雖然她失去了貞潔與生命,但這更可以視做是通過自我犧牲來完成的救贖而達到與上帝精神上的和諧。雖然她在這條通往上帝的道路上蒙難了,但從最後的泉水中我們可以看出她犧牲的意義,她為世人洗清了罪孽而換得了上帝對他們的寬恕。她被牧羊人殺死而具有的意義也似乎與耶酥這「天生的羔羊」的命運相符。伯格曼通過卡琳這個角色對耶酥的犧牲做出了思考。反過來我們再來看下其它人,特利因為復仇而使自己幪上了罪,從他殺人前的那場異教的儀式可以看出他強烈的憤怒與痛苦以及他對上帝的懷疑,以致於要依靠異教的儀式才能鼓起復仇的勇氣,但同時他這樣卻無法面對上帝。特利的妻子由於對女兒的溺愛而對女兒與父親的愛產生了嫉妒,而懲罰她的是她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英格麗由嫉妒產生的種種行為以及她後來陷入痛苦的懺悔,將卡琳的死歸結於自己的詛咒,她已經在精神上受到了最大的懲罰。而三個牧羊人中年長的兩個用死亡償還了他們對上帝的不敬,最小的那個在事後由於恐懼而幾乎崩潰,而他也最終難逃死亡的命運。伯格曼以他特有的冷酷為人與上帝的關係劃上了這樣的句號。但隨即又提出了新的問題:「如果自我犧牲能洗清已犯下的罪孽,那麼人類原始的罪惡又該如何洗清?」雖然他用卡琳的犧牲在表面上完成了為他人的贖罪,與上帝達到了和諧,然而質疑仍在繼續。
本片的攝影是個不得不提的人物,他就是瑞士人斯文•尼克維斯特。而從本片開始,他也開始了與伯格曼的長期合作,成為伯格曼的御用攝影師。他高超的攝影技巧與伯格曼的主題完美的結合在了一起。如卡琳與英格麗去教堂途中的多個全景、大全景鏡頭的使用體現了斯文高超的運鏡水準。攝影機的移動輕靈飄逸,使畫面如同田園畫般寧靜莊嚴。而到了特利接待以及殺死三個牧羊人時,畫面儼然有一種審判之感。而最後特利質問上帝時攝影機更是從演員背後去拍攝,更給人一種強烈的感情衝擊。同時本片繼承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瑞典學派所開創的北歐自然主義的拍攝風格(尤其以伯格曼的老師史約斯特羅姆的《風》為代表)。環境在影片中被賦予了同影片角色同樣重要的含義,無論是風、水、樹木這些最普通不過的事物都變成了對人物內心狀態的外在反應。如最典型的特利使用異教儀式時風吹大樹的段落里,風與樹都將特利內心的緊張與矛盾成功的視覺化(外化)了,將人與環境的關係有機的結合到一起,給環境賦予特殊的意義。
伯格曼這個偉大的思想者終其一生都在思索著幾種伴隨現代人的關係,「人與神的關係。上帝是否存在?人與人的關係,交流是否可能?愛與恨的關係,愛恨是否並存?生與死的關係。生命是否有意義?」而他的影片也執著地為如何解決現代人最大的精神疾病「孤獨」尋找答案。
《處女泉》獲得了1960年美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