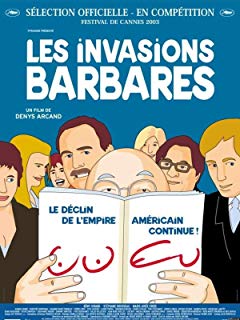野蛮入侵/老爸的单程车票/老豆坚过美利坚
![]() 7.7 / 26,487人
99分鐘 | Canada:112分鐘 (DVD version)
7.7 / 26,487人
99分鐘 | Canada:112分鐘 (DVD version)
編劇: 丹尼斯阿坎德
演員: 雷尼吉納德 史蒂芬洛素 桃樂絲芭莉嫚 Louise Portal Dominique Michel

2007-05-25 22:12:25
消逝的野蠻人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寫道:對希特勒的仇恨終於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我想,他所意指的絕不僅僅是納粹,甚至主要不是納粹,而是製造了無數流放、殺害和對主權國家的粗暴踐踏的前蘇聯。與此對應的是我的導師王先生的一句話:納粹作為對英美原則的最後一次浪漫主義的抵抗,其最終失敗之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從此實現了全球的統治。我不是說因為王先生沒有父兄在納粹鐵蹄之下喪生,因此他才能有足夠置身事外的心態來這般談論過去的歷史,這樣的談論似乎對納粹不無讚美,不,不是這樣。其實王先生同米蘭昆德拉所要表達的,無論是對納粹的控訴還是看似讚美的感嘆,其實是幾近相同的意思。那就是:一方面我們不得不面對歷史車輪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滾滾推進,一方面我們誠然不會懷疑——有一種價值或者理想在文明演進的同時無可挽回地逝去了。
而這種與文明演進相對抗的理想或者說價值尺度,通常就被稱為野蠻。
也許911事件表明,英美原則尚未完全實現它的統治,但是,正如《野蠻人入侵》中萊米教授所說的,不用說二次世界大戰,就算是相比起發生同樣發生在美洲的種族滅絕來說,911事件也實在算不得什麼,儘管是一樣鮮活的生命,可是這個可憐的傷亡數字只會比對希特勒的仇恨消逝得更快。可是正是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導演Denys Arcand卻作出了一次不能忽視的努力,一次力圖想要挽留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緬懷什麼的努力。
商業成功的兒子塞巴斯蒂安無疑是文明世界的代言人,他的月薪要超過其父的年薪,並且比他有錢更重要的是,他深諳錢的法則,他能夠用他的錢去換得他所要的那些東西。在《野蠻人入侵》一劇的前半部里,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按照他的原則(錢的原則)成功地實現了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為他的父親爭取了高級的病房、解除痛苦的海洛因、高科技的醫療手段,也為自己找回了筆記本電腦,等等,甚至,他用錢收買父親的學生的人情,以使得父親獲得慰藉。看上去真的如同我的一位朋友看完所感嘆的:有錢就是好!的確,即便是面對歐洲傲慢的法蘭西人塞巴斯蒂安的原則還是毫無例外地奏效,如此說來,他毫無疑問是成功的。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了,縱然他所有的行為都是按照金錢法則運作的,他所有行為的目的卻正是金錢法則的反面——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誠然身患絕症的萊米教授是頑固不化的,他在奉行他的做人原則的時候十分地迂腐,可是他的兒子卻絲毫不頑固,對父親盡孝和對世俗世界行賄二者並行不悖,這一點表明塞巴斯蒂安並不曾背棄父親的原則,只是,按照通常的話說,他比較識時務,或者刻薄一點地說:比較現實主義一些。
但是,塞巴斯蒂安並非自己很明了這一點,他也許本來是在理智上拒絕承認這一點的。他覺得他有自己的原則,而對此他的父親是一無所知的。在片中他無時無刻不在打手機,雖然不是一種炫耀,但卻毫無疑義地伸張著自己的原則:效率是資本的內在要求,一通電話,那就是上百萬的生意。在救護車裡,時日無多的父親就這樣望著兒子,兒子也望了望父親,神情微妙,但是他不曾停止打手機,為什麼要停止呢?在影片的開頭,兒子看不到其中的理由。由此可見當筆記本電腦丟失後兒子同父親的爭吵也就可想而知了——兒子本來是用這種高科技手段來讓父親見到他遠方的女兒,這在兒子看來誠然是一種照顧,而父親卻對筆記本電腦的被竊毫不掛懷。這令我想起王先生的另一句話,他說當有人看到他打手機,就取笑說你享用著現代文明的成果,卻還要一個勁地批判現代文明。劇中亦然,父親的幾乎一切待遇,全都是兒子的金錢堆砌出來的,可是父親卻要蔑視給他帶來福利的金錢。這難道不可笑嗎?
這的確不可笑。有一次我去朋友家作客,由於相距甚遠,而由於時間過晚而錯過了末班公車,我若是堅持要回家就必須付出我所承受不起高昂的計程車費。於是朋友開玩笑說:知道錢的好處了吧?若是你足夠有錢,你可以在任何時間來去自由,這表明為了你的朋友(朋友是你的原則)錢也是好東西,你就不要批判了吧。這樣玩笑般的責難只有似乎無可辯駁的道理,其實是不經一駁的。我這樣回答他:你說我為什麼要叫計程車回家呢?為了速度,只能是為了速度,而速度意味著效率(因為我們明天都必須更有效率的工作)。由此可見,這乃是資本原則所規定的。為了見朋友我非要追求速度嗎?這只要讓我們看看古人是怎麼做的就知道了。在那些流傳千古的詩句中我們不難發現,李白或是別的誰,若是要探望他的朋友,他從三個月前就開始上路,一路跋山涉水(順便留下了無數詩篇),一路抒發著想念的心情、等待的焦灼以及即將見到的期盼等等,然後三個月後,他到了,可是朋友在嗎?對不起,古代通訊不便,朋友碰巧還外出了!於是詩人在別人門後留字一首(那時候管這叫風雅,沒有七不規範束縛,也不需要交罰款),名曰尋人不遇,滿懷惆悵地又花三個月回老家去了……還有一位老兄更絕,他就在快到的時候忽然掉頭走了,說是乘興而來,興盡而返。這要是擱在現在,絕非是境界高,而是腦壓高的結果吧?
米蘭昆德拉在《慢》中發問道:為什麼高速公路上到處是如獵鷹窺探獵物一般等待超車機會的車輛呢?他們急急忙忙地到底要幹什嗎?那些史詩中游手好閒的好漢們都到哪裡去了?而伯爵夫人為了一夜風流需要設計那麼多繁複的調情過程,可是現代人卻只知道迫不及待地叫喊:來吧!來上我吧!直奔主題吧!……
所以就讓我們承認吧,迫使我遵從資本原則的通常是資本原則本身,只有在醫療和教育等這些關係到終極關懷的事業上,尚且還存留著一點點的人味。
回到影片來。不久,當兒子尚未開始贊同父親,父親首先開始注視兒子了。這不奇怪,父親始終關注兒子,他同兒子的對抗源自這種關注本身,而非其它。因而當父親感受到兒子的孝心,他不難抬頭看見兒子的優越,這同許多的父親並無不同。同樣是在救護車上,有一次萊米教授在塞巴斯蒂安掛了手機之後不無疑惑地問:你到底在做些什麼?兒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回答了父親的問題,於是父親接著問:那麼你很在行羅?兒子挺起胸膛回答說:足夠在行。父親聞言哈哈大笑了。這段簡單的父子對話,若是你不留心細想,也許真的會僅僅以為是父親向兒子妥協了,可是事實上,正好相反,那是兒子開始認同父親的開端。因為正是在父親包含寬慰、自豪和諒解等等複雜心緒的大笑聲中,兒子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快樂,兒子遲疑的笑容詮釋了他內心悄然的頓悟:原來父親的肯定是如此的重要,自己多年來的奮鬥累積的金錢並沒能帶來這樣的滿足(資本只會要求自身無限地增值而已),而父親的和解卻讓做兒子的自己竟然莫名地快樂了——他在此前誠然不完全明了自己的盡孝行為不僅僅是利他的(因而是違背資本的利己原則的),而且是成全自己的(真正的人的行為)。
於是,後來接近片尾的那個小插曲就明白無誤了。坐在營火面前的塞巴斯蒂安剛剛接起手機,旁邊的女孩娜塔莎卻一把搶過來扔進了火堆里。塞巴斯蒂安先是一怔,然後望著娜塔莎淘氣而快樂的臉龐,他也笑了。他沒有像丟失筆記本電腦時那樣咆哮說:「那裡面有我幾十宗大生意!」相反,他只是笑著問娜塔莎:「你覺得這樣很好玩嗎?」兩個年輕人在營火面前像孩子一樣嬉鬧,卻令坐在螢屏前的我怦然心動。
如果是我,我會趁此一把攬過女孩的肩頭,可是我們的主人公到底也沒有。
作為萊米教授好朋友的女兒,娜塔莎是劇中的另一個重點,雖然篇幅不如主角那麼大,但是在邏輯上同等重要。因為她和塞巴斯蒂安代表了年輕人對待原則交替的兩種最典型的態度:塞巴斯蒂安是力圖遵循新原則的一類,當然他是這一類中頗為成功的(絕不是作為人的成功,而是作為人格化資本的成功),很多人也想依附資本原則,但是不那麼成功而已;而娜塔莎則是代表了消極逃避的一類人,他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對抗新原則,但是也無法融入其中,因此他們採取的方式往往就是邊緣化。邊緣化是對原則自身純粹的否定,而並不建立任何新的原則,他們的靈魂早已游離出世界之外,而他們的肉身卻不得不受著新原則的制約(這是誰都無法逃脫的,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是最正確的),他們用可能的一切方式破壞規則,吸毒、濫交,這些方式毫無疑問都是自殺性的,絲毫也不成全他們自己(他們都是潛在的或者庸俗的911事件製造者),對那些不諳規則的人來說他們也許比較清醒,但是事實上他們遲早完全麻木,因為他們在抹殺自己的生命。這是兩種典型,而我們更多的人則是這兩種典型之間的搖擺者,當我們加薪或者升職的時候我們感到自己在享受規則,當我們受挫我們便難免自暴自棄,當然,最後,在發完牢騷之後,我們全都按照馬克思的鐵則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去了。
現在我們知道什麼是小資了。小資就是身處資本原則之中,依靠資本原則建立自身,然而又因為佔有的資本份額(社會權力)較少而常常受挫,自身的個性無法得到實現,從而產生一種搖擺不定的狀態。他們的個性同原則融合最好的時候是第三等級上升的階段,那時候世界的舞台是同樣屬於他們的,而當二戰結束,資本一統天下,他們的好日子便過去了。因此小資的基本情調就是懷舊和感傷。在字典里我們可以看到,從唯美主義到浪漫主義,所有小資藝術樣式後面都標有「頹廢主義」的解釋,這與我們所理解的多少有些偏差,浪漫主義不是同理想連在一起的嗎?唯美主義追求純粹的美也是頹廢嗎?答案是:是的,都是頹廢的。不僅因為面對全球化的新原則,那一切都是反動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說它們頹廢不是為了肯定當下的原則,而只是說,它們埋頭沉浸於過去的脫離現實生活的想像和情緒之中,是並非積極的,在當代,唯有馬克思是最積極的,因而按照薩特的話來說,是「不可超越的」。
還是回到影片中來吧。娜塔莎幾乎是一個人類的廢品,當她帶著神經質的眼神出場的時候,我活脫脫看到了一個垮掉一代的翻本。他們是時代的痛覺神經,我說過,無一例外有著神經質的眼神。可是幾乎是同時我察覺到她的美麗,第一個眼神就令我愛上了她,我相信她已經知道了她所面對的塞巴斯蒂安是怎樣一個人,作為同時代人,他們之間的相互了解也許不會需要那麼多周折。塞巴斯蒂安說我委託你買海洛因給我的父親,我自己不懂這個,你來。娜塔莎說:可是你不能信任我,因為不能信任一個吸毒的人。塞巴斯蒂安當時其實沒有很明白(在規則之外的事情他總顯得沒有那麼警醒,他的嗅覺全都放到股票行情之類的事情上面去了,難怪他父親說他其實什麼也不懂)。其實娜塔莎洞悉了塞巴斯蒂安,因為她不遵循資本原則,當一個人跳出功利法則,看事情總是會更明白一些;但是同時她也清楚自己,她的肉身受到生理制約(毒品的制約和衣食住行、簡言之日用商品的制約),她常常不能按照她所洞悉的心靈法則辦事。於是,她對老萊米說:我不能按照契約辦事。老萊米為了一種潛意識裡的救贖而對娜塔莎說:你要照顧我到最後,言下之意我沒有放棄你就不能放棄。可是娜塔莎說我不能,我做不到,她心裡清楚她的世界就是否定一切規則,無論是金錢的,還是人情的。
當然,最後她同母親的和解(那一個悲傷的擁抱)還是表明,老萊米多少是成功的,但是這樣的成功很有限,因為導演沒有安排她和塞巴斯蒂安實現他們的愛情(最後的Kiss證明了他們毫無疑問的愛情)。原因早就已經宣佈過了,娜塔莎在吸毒過量的暈眩狀態中對塞巴斯蒂安說:你是個完美的男人,可是我從一開始就不好了。塞巴斯蒂安誠然不是完美的,因為他所熟悉的原則不能實現他同娜塔沙的愛情,或者說罪責不在他,也不在導演,而在於這個時代本身不會成就那樣的愛情。導演最後的安排是巧妙的,他安排娜塔莎給老萊米注射藥物結束了老人痛苦殘留的生命,而老人則以另一種方式安排了她的結局:老人通過兒子將他當年同情人風流快活的公寓交給了娜塔莎,娜塔莎可以在這個四壁砌滿書本的房間裡度過此後的人生,也算是某種程度上少許脫離了物質的束縛吧。可是,老人縱然能通過兒子將公寓留給娜塔莎,但是他卻不能通過公寓將兒子也留給她,要知道老萊米說過,那滿滿一房間的書,塞巴斯蒂安一本也沒有讀過。因此,在那個掙紮一般的吻之中,娜塔莎掙紮一般地推開了塞巴斯蒂安,將他推回到他那早就不相信愛情了的未婚妻身邊,推回到這個金錢法則統治的世界,甚至躲在窗子背後沒有接受塞巴斯蒂安那多少有些悵然若失的回眸——那個回眸一直伴隨他上了飛機飛向他原來的世界,哦,讓我們詠嘆吧!那個多麼小資的回眸呵。
可是,這是愛他的最好的方式嗎?究竟是將他留在一無所有的自己身邊,還是將他推回到他能擁有許多卻唯獨不能擁有她的愛的資本法則的世界呢?這個問題導演是回答了,雖然也許這不是這個劇情本身唯一允許的回答,不是一個個案的最好回答,但是卻是這個時代最真實的回答,也是最普遍的回答。
只不過,我們時刻要記得,當我們說這個回答真實而且普遍的時候,絲毫不等於我們就此認同了這個回答,絲毫不等於我們將這個回答視為好的回答。同樣,當我們不嫌殘酷和非人道地稍稍忘卻了集中營和雙子大廈的死難者,而對那些被我們的文明世界日益拋在身後的所謂野蠻人的方式給予深刻同情的時候,也絲毫不等於我們願意像天真無助的小資那樣去懷舊和惆悵。我們走在文明的道路上,身處歷史極端之一度,縱然沒有被給予更多選擇,可是自始至終我們也絕不放棄選擇的自由,因為那樣的自由是真正屬人的。
老萊米臨終擁抱他的兒子,他問你知道其實我最希望得到的是什麼?塞巴斯蒂安一如既往地懵懂,老人告訴他說:我希望有一個像你那樣好的孫子(老人最後稱呼塞巴斯蒂安為「野蠻人的王子」)。這一次,塞巴斯蒂安立刻就明白了。像你一樣好的孫子,是的,那也許意味著一個尚未消逝並且可能永遠延續下去的野蠻人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