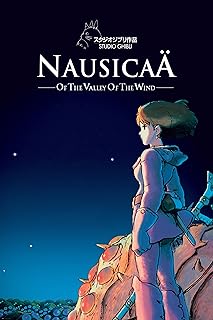電影訊息
風之谷--Kaze no tani no Naushika
編劇: 宮崎駿
风之谷/风谷少女/KazenotaninoNaushika
![]() 8 / 183,824人
117分鐘 | USA:95分鐘 (edited version) (1985)
8 / 183,824人
117分鐘 | USA:95分鐘 (edited version) (1985)
編劇: 宮崎駿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7-07-13 01:18:54
《風之谷》隨筆
無意中翻出動畫片《風之谷》復習起來,這部宮崎駿導演的成名作可以稱為是他後來所導演的一系列作品的引子。
七日之火與工業文明
記得看過的一個電視採訪:日本第一位太空人秋山豐寬(1990年乘坐原蘇聯太空梭進入太空)在太空旅行結束後不久,便從大眾的視線中消失了。他來到福島縣的山區,開始從事無農藥栽培農業。*1 面對記者的詢問,秋山解釋了自己的選擇。他說,當他從宇宙中看到自己的家園-藍色的地球時,突然明白了對於自己而言,最為重要的工作是什麼。
其實每個人的經歷,家庭的經歷,國家的經歷,往往會在渾然不覺之中介入你我的生命。廣島,長崎那兩顆原子彈爆炸的經歷,就給日本民族的心裡留下了諸多爪痕。從這個世界上唯一經歷過原子彈的恐怖記憶,同時又信仰萬物有靈的民族裡,《風之谷》這樣的作品誕生了。
故事所設定的時代背景是工業文明消失於七日之火後的第1000年。在森林和王蟲的進攻下,人類苟延殘喘,等待著預言中的藍衣救世主的出現。
娜烏西卡是秘境-風之谷的公主。這位能御風,能與動物甚至王蟲交流的精靈般的少女,同時也肩負著守護谷中居住的族人們的責任。當娜烏西卡發現了森林和王蟲其實是在淨化被人類污染的自然的真相,喜極而泣時;她所屬的族群-人類,卻依然固守著即使是七日之火也未能燒燬的征服自然的「常識」。
征服自然的「常識」
正如1443年設計的,反時鐘方向轉動的佛羅倫斯大教堂大鐘向我們所揭示的那樣。我們常識當中所謂時鐘運行的順時鐘方向,其實是當時選擇了另一個方向的鐘錶匠在市場競爭中失敗的結果。被固定和遺傳下來的人類常識的森林裡,隱含著無數其他的可能。
偶爾在恍惚之間,你還會記得幼年時的夢嗎?
當你聽見第一朵花在清晨開放的沙沙聲,第一隻甲蟲扇著棕色的羽翅在你面前嗡嗡飛起,第一條斑斕的小蛇寶寶在草叢中蹣跚而過,第一隻大耳朵大眼睛的幼鼠和你對視,如果你和它都沒有各自物種的常識,會是怎樣的相遇?
一如影片中娜烏西卡那個金黃色憂傷的夢:
在金黃的田野里,幼年的娜烏西卡被父親帶上馬背和族人們一起出行。當她發現族人們漠然前行的方向是她的玩伴-小王蟲藏身的樹洞時,對悲劇的預感讓娜烏西卡跳下馬背,拼命奔跑起來:
「不要往那邊去!不要!」
她跑到樹洞邊,緊緊護住那個小小的洞穴,大喊著:
「這裡面什麼都沒有!」
而天真的小王蟲卻爬出樹洞來迎接自己的朋友,用小小的前爪拍打娜烏西卡的小鞋以示友好。
「你不要出來,不能出來!快進去!藏起來!」
娜烏西卡把小王蟲塞回樹洞,然後向父親和族人們哀求:
「求求你,它什麼壞事也沒有做過!」
「求求你們,求求你們,不要殺害它!」
娜烏西卡孤單的呼喊,被捉小王蟲無措的擊足聲,都湮沒在人們的對話背景里:
「娜烏西卡是妖精,能和王蟲溝通。」
「娜烏西卡,人和王蟲是不能共存於一個世界的。」
森林之民
在當今歐美的主流文化中,西方文明與科學精神來源於希臘,一神的信仰來源於耶路撒冷的基督教,而當上個世紀後期,哈里波特等魔幻類小說,電影文藝作品風靡世間時(魔戒系列除外),事實上是歐洲的另一支古老信仰的復甦。
哥爾特人(The Celtic),這是紀元前5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希臘人對阿爾卑斯山北邊的異族的總稱呼。這些居住在森林中的民族沒有留下多少關於他們生活的文字記載。
隨著羅馬帝國對歐洲的征服,森林採伐的擴大,哥爾特人退到了歐洲的邊緣地帶,現在在愛爾蘭等地還有留存。居住在森林中的哥爾特人信奉的是萬物有靈的自然崇拜,在歐洲中世紀的魔女審判里,可以看到這種古老信仰的殘存。
歐洲北部是茂盛的原始森林,這片森林向東綿延,穿過歐亞大陸的西伯利亞,與我們這片土地的北方相連。在東北的森林裡,少數民族信奉的薩滿教和哥爾特人的信仰有些類似。沿著古森林繼續向東延綿,穿過白令海峽,在北美的印第安人那裡,你也可以看到類似原始崇拜。
在娜烏西卡身上隱藏著這些森林中民族的影子,後來宮崎駿導演將其放大而塑造了幽靈公主這一角色。
這些被文明人蔑稱為野蠻人的族群,大都選擇了人類順服於自然的生活方式。當哥倫布宣佈發現新大陸時,似乎忘記了在美洲生活著幾千年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另一群人類。
娜烏西卡被自己的族人視為異類,因為她具備與動物以及森林的守護者-王蟲聯絡的能力,而她也因此成為人類的救世主。
征服自然的未來
對於中國人而言,科學技術帶來社會的繁榮,核武器帶來民族的復興,我們更為容易擁抱征服自然的思想。而經歷過那如地獄之火的原子彈爆炸惡夢的日本,雖然奔走在科學進步的大道上,心靈深處卻殘留著對未來未知命運的恐懼。《風之谷》就是這樣一部詢問人類命運的作品。雖然故事草草結束,有了一個明朗的結尾,但那只是矛盾的暫時調和。
「你們的命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謎。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把所有的野牛殺光,把所有的野馬馴服,那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景像?如果原始森林中儘是人類的足跡,幽靜的山谷中佈滿橫七豎八的電線,那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景像?如果草叢灌木消失了,空中的雄鷹不見了,馬匹和獵犬也失去了用場,那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景像?這一切,只意味著真正生活的結束和苟延殘喘的開始。
當最後一個印第安人與荒野一同消失,他們的記憶就像草原的雲影一樣在空中浮動的時候,這些湖岸和森林還會在嗎?我們的靈魂還會在嗎?」
--- 引自印第安人西雅圖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的信
後記:
經歷東日本大地震和核電站危機之後,回頭看幾年前寫的這篇小文,感觸良多。今天的科技和文明雖然看起來高度發達,其實是建立在如沙土般脆弱的技術極限和認知極限之上。工業文明才二百多年,在地球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其巨大的能量和規律我們還遠遠未能了解。當我們在商業利潤,眼前繁榮的誘惑下,打開自己不能掌控的核技術,基因技術......一個個潘多拉魔盒之後,技術的進步將使我們人類存在的風險加劇。《風之谷》就是這樣一部讓人深思的作品。
初稿寫於2007年3月27日,最後修改於2016年7月29日
*1 補充:由於2011年3月11日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在離發生事故的福島核電站僅三十多公裡的山區務農的秋山豐寬,成了核電站災難的「原發難民」。11月1日京都造型藝術大學聘任他為藝術學部教授。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