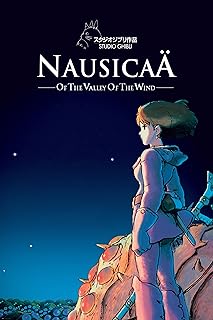风之谷/风谷少女/KazenotaninoNaushika
![]() 8 / 183,824人
117分鐘 | USA:95分鐘 (edited version) (1985)
8 / 183,824人
117分鐘 | USA:95分鐘 (edited version) (1985)
編劇: 宮崎駿

2007-07-25 04:01:06
風之谷諸神之一 風之谷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宮崎駿的經典漫畫——《風之谷》,是在下認為的最值得一看的少數幾部漫畫之一。場面之宏大,絕對不在《銀英》、《五星》之下,而其對人性的感悟,在下認為更在兩者之上。因為喜歡,所以想說說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也希望有人看了在下的介紹而去看《風之谷》。
第一篇選擇風之谷,並不是因為風之谷在全書中的重要作用。看過的朋友都知道,風之谷在書中的作用極其微弱,除了主角娜烏西卡生長於谷中外,幾乎與主線沒什麼聯繫。但是,之所以選它開篇,一個是因為本書以風之谷命名,但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我想,風之谷是宮崎駿理想中的國度,是人類社會的典範,就像柏拉圖的理想國。
全書直接描寫風之谷的,只有區區三處,分別是第一本、第二本、第六本最後和第七本開頭(指8本一套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版本)。除了第一段因為介紹娜烏西卡的關係,有78頁,其它兩段均只有寥寥十數頁的戲份。但正是這些短短的描寫,將這個受上天獨特寵愛,遠離戰爭和腐海的威脅,人民安居樂業,熱愛和平,熱愛生命的小自治國的方方面面展現給了我們。在我們跟隨著娜烏西卡逐漸進入「漩渦中心」時,在我們經歷了死亡、屠殺、背叛、欺騙……體味了仇恨、絕望、悲傷、憤怒、瘋狂……之後,還能為世界上保留有這樣一塊淨土而欣慰。可以說,風之谷是人類的希望。或者……至少,在娜烏西卡看來,風之谷是人類的希望。所以她才在最後毀掉「修瓦的墳墓」,將真相隱瞞,而帶領人類走上痛苦的再生之路。
關於風之谷,書中有這樣的敘述:「巨大的產業文明消逝於時光的黑暗彼方後一千年,陶器時代末葉。風之谷,因為靠海,有風抵擋孢子,是少數倖免於腐海毒瘴的邊境土地。」可以說,在那個時代下各異的民族中,風之谷也算是有自己獨特的一面了。因為有風,這裡得到保存;因為有風,人們發展出了滑翔翼、蟲笛、鳴彈等科技;也是因為有風,這裡的族長的稱號叫「御風使」。作為一個不滿500人的邊境小國,風之谷是沒有在亂世中存活下去的能力的,她必須依靠某個強大的國家,即多魯美其亞王國。雖然政治上取得了自治權,但軍事上時刻受到制約,「風之谷族長擔任駕駛炮艇的戰士,加入多魯美其亞王的戰爭行列……」,這個古老的盟約將風之谷與多魯美其亞的命運聯繫在了一起。從歷史上來看,有點像中世紀歐洲國家的君主和諸侯的關係,君主有自己的軍隊,眾多諸侯也有自己的武裝。當君主要侵略別國時,便會借諸侯的軍隊,與自己的軍隊並肩作戰,而戰爭取得的領地和戰利品,則與一起出征的諸侯共同分享。對於多魯美其亞的鳥王來說,管理此地頗費心神,又確實沒有很大的領土,進攻又困難(因為有炮艇),所以也樂得讓它保留自治權,而在戰場上可以隨心所欲的利用它的力量。
但是,風之谷的歷史其實也不是那麼簡單的。300年前,風之谷與其它邊境民族同屬於名為「艾弗達魯」的強大王國之下,後來,因艾弗達魯王國因爭奪王位而引發戰爭,進一步威脅了腐海的守護神——王蟲的生存,終於惹怒了腐海,爆發了大海嘯,吞沒了艾弗達魯王國的大部,驚人的科技也隨之消失。而倖免於難的一小撮人只好生活在腐海邊,淪為多魯美其亞的附庸國…………
風之谷的谷民信仰的神,是「風之神」。關於風之神,書中並沒有做更多的描寫,僅有娜烏西卡與古艾弗達魯教的聖僧對話時提到:「我們的風之神指示我們要生存下去呀!」而在這教義指導下的風之穀穀民,是無比熱愛生命的。不只是人類,陽光、天空、草木、甚至其他人懼怖的昆蟲也加以關懷和憐憫。這樣的性格,使得谷民們能夠擁有一個快樂和寬容的心,儘管環境已變得如此惡劣,但仍能過上相對美滿的生活。而在土鬼的那雷族飛船墜毀時,谷民雖然有過猶豫和不安,但最後終於決定加以援助,並成功地與那雷族相處。這在當時的環境——土鬼與多魯美基亞戰爭達到白熱化,土鬼皇帝為儘快贏得戰爭的勝利,大規模動用瘴氣與昆蟲,而不惜令國土廢棄,雙方都受到重創,流留失所的人民紛紛起來反抗,民族的矛盾進一步被激化的背景下,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試想其他任何一個民族在戰爭局勢不明朗,吞噬古艾弗達魯的大海嘯即將重視,而且對方是說的話不通,祭的神不同,連吃的東西也不一樣的土鬼民族時,還能出去救助,實在是很不容易的!
寫到這裡,我想起一個有名的試驗,叫「囚徒的困境」。最早我是在理察·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上看到的,理察為證明互助合作對基因自身得到複製有利而做的一個改進了的試驗。試驗的目的就是要驗證「合作」和「背叛」,究竟何者能夠在社會生活中得到更大的利益,當然,是在一個極大的數量尺度之下的。對於試驗的過程,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看書,而結果則非常有趣。在眾多「合作-背叛」模式中,最後達到最大利益的出乎人們的意料,是一個以合作開始,若對方選擇合作,則下一次也選擇合作,反之則背叛的程式。
這樣一個結果,似乎是預示著人類社會的基礎――合作。這種合作是與蟻群、蜂群有根本區別的,因為在那些社會中,生殖權都是在少數特權個體中的。所以整個群體其實與一個個體無異。人類社會的合作是建立在文化基礎上的合作,而這種合作所帶來的利益,不是馬上就能體現出來的。大多數時候,甚至要先受一定的損失才行。這些,都是與我們寫在基因裡的「自私」的特性不相容的。所以,做到完全的「合作」,是一件極之困難的事情。我們的文化,才僅僅出現5000年,對於進化來說實在是太短暫了。我們自身絕無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進化出完全適應社會化合作的基因。所以我們在合作時會有疑慮,也會有欺騙。風之谷的谷民也是一樣。究竟在面對我們不熟悉的事物時,第一次的選擇是「合作」呢,還是「背叛」?在道金斯的試驗里,這將直接影響到最後的結果。在面對這種情況時,我們每個人又都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呢?我們能夠像娜烏西卡那樣豪不猶太豫地選擇「合作」嗎?
人類在達到他自身形成的文化所預示的理想狀態之前,還有太長的路要走了。痛苦是社會的正義戰勝我們個體自身的邪惡的必然代價。任何形式的逃避,比如「補完」,都是絕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作用的,反而會延緩了進化的腳步。這就是人類前進的道路上所必須克服的「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