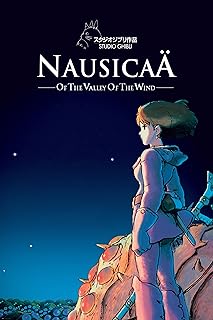電影訊息
風之谷--Kaze no tani no Naushika
編劇: 宮崎駿
风之谷/风谷少女/KazenotaninoNaushika
![]() 8 / 183,824人
117分鐘 | USA:95分鐘 (edited version) (1985)
8 / 183,824人
117分鐘 | USA:95分鐘 (edited version) (1985)
編劇: 宮崎駿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7-07-25 04:06:56
風之谷諸神———之三,森林人
森林人的設定可以說是《風之谷》中的一個亮點。人究竟可以怎樣活著?我們的慾望到底有多大?怎樣才能滿足?自古以來,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各個世代的無數人們。似乎沒有人能夠回答這些問題。
森林人的出場有7次,最早是在猶巴一行被僧會追殺,飛船被擊落時,正當馴蟲師們要砍下昏死過去的猶巴的手作為證據時,聽到了森林人的笛聲。馴蟲師對這些像鬼魅一般的人又敬又怕,迅速逃走了,猶巴一行人因此得救。其實,第一次看到這裡,我還以為猶巴他們會被抓去吃掉(笑)
森林人其實是馴蟲師的始祖中血統最尊貴的一族,是是古艾弗達人的後裔。在300年前大海嘯發生時,他們跟隨藍衣人進入了森林。從此,捨棄了用火,身穿昆蟲腸衣,食用蟲卵,並且居住在昆蟲體液形成的泡沫帳篷中……他們完全放棄了城市的生活,而選擇與腐海融為一體。對外界人來說是恐懼的對象的腐海,對於森林人則是溫暖又舒適的家。另一方面,森林也賜予了他們回報,不僅提供了他們所需的衣食住行,還賦予他們超能力,可以自由地以念力對話,精神可以脫離肉體四處雲遊……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狀態還是很滿意的,尤其是遠離了城市的喧囂,甚至連文明的象徵——火——也捨棄後,內心深處得到的那種平靜——安寧、詳和、充滿生之喜悅和感恩,彷彿微風下平靜的湖水,偶起微漣……其實,這樣的平靜與滿足,便是幸福了。
有一個關於草履蟲混養的實驗,對人很有啟發:第一次實驗者將大草履蟲和小草履蟲混養在一個瓶子裡,超過了允許的密度,結果在種間競爭的結果下,大草履蟲死光了。第二次,實驗者將大草履蟲和另一種袋狀草履蟲混養。這次同樣又發生了種間競爭,但並沒有哪一方滅亡。一星期後,原本都是營游泳生活的兩種草履蟲,大草履蟲繼續游泳生活於瓶上半部,而袋狀草履蟲則改為營底棲生活,居於瓶底。兩者,尤其是袋狀草履蟲,改變了自己的習性和生活環境,使得自身能夠在環境變化時繼續生存下去。
生命本身是有韌性的,這正是生命偉大之處的彰顯。每當環境變化,生物原賴以生存的條件減少時,那麼剩下的生物所能做的只有兩件事:為爭奪剩下的資源互相殘殺,強者生存;或者轉而適應新的環境,改變自己的居住、攝食、生育、甚至呼吸的習慣,從新的環境中獲取自己生存所需的一切。前一種,為與自己近親競爭,久而久之,便變得牙更尖、爪更利、角更大……;後一種,則為了生存於新環境而長出肺、生出腳、展開了翅……此謂之——進化。
實驗室裡,草履蟲如此;泥盆紀後期,上岸的魚兒如此;「大海嘯」發生時,在藍衣人帶領下的森林人亦如此。只不過,這時進化的主體已不是基因,而是除基因外生物社會中另一種重要的進化因子——迷米,即通常所說「文化」的單位。關於這方面的詳細討論,可以看蘇珊·布萊克梅爾的《迷米機器》,作者是我在「之一」里提到過的理察·道金斯的學生。
可以想像,森林人初進腐海時,一定是無比痛苦與不適的,就像魚兒初次上陸一樣。腐海里充滿了瘴氣,吸入一口就沒命,所以要整天戴著面罩;不能用火,吃不到平常吃慣的美味;四週都是巨大而危險的昆蟲,一不小心觸怒了它們便會受到圍攻……在如此眾多危險包圍中,要生存下來都是很難的,即使有藍衣人的帶領,也一定吃了不少苦頭,有很大犧牲。但最後,他們終於適應了森林的環境,熟悉了昆蟲的習性而生存了下來,並且感受到了生之喜悅和心的平靜,以及前所未有的幸福。
那麼,所謂幸福到底是什麼呢?實驗室裡的袋狀草履蟲幸福嗎?上陸的魚兒幸福嗎?多少人畢其一生去追尋幸福,終未能找到;又有多少人為了找尋「真正的幸福」而將自己苦苦追求得來的東西,又摔個粉碎?幸福是什麼?老婆?房子?車?是冬天的暖爐,還是懷裡的小貓?被愛人抱著,是幸福,吃到媽媽煮的久違的紅菜湯,也是幸福。有人說在海邊悠閒的曬太陽就是幸福,那富人和乞丐都可以做的事,為什麼還要追求其他東西呢?
其實,幸福也只是一種感覺罷了,每個人的幸福也是各不相同的,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的幸福也可以完全不同。所以,若要對幸福下一個統一的定義是辦不到的,就像「美」這個概念一樣。當你覺得自己的心和慾望終於得到平靜和滿足了,那便是幸福。換句話說,當你的心對自己說「我幸福」,那你便幸福了。
在世間生存的每個人,或者說每種生物,都是生活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的。那麼,生物也都是對這個環境有一個「期望值」的,或稱為「要求」。這種「要求」,最早是對溫度、鹽度、光照等自然條件的應激性,而原因,則是DNA複製及各種酶起作用的最適條件。比如草履蟲,就有最原始的避鹽性、趨光性,各種生物都有其生存的溫度(凍死其實就是酶活性減弱,代謝停止)。到了高等動物,因為細胞間的組織結構極其複雜,又有了思想,結成了社會,所以要求變的複雜了。但無論人的哪種需求,歸根結底都可以認為是幾種基本生存本能的衍生。這方面的著作,比如弗洛依德的理論,還是很多的。那麼,當環境與生物體的「要求」一致時,對於低等生物,就是適應;而對於高等生物,比如人,就是「幸福」了。
但,對於人來說,整個社會也是環境,甚至比自然的環境更重要。而社會和文化的複雜性,則使得人要求的標準更高、更複雜了。所以,有時候反倒不如動物比如貓貓狗狗來得幸福。其實挺悲哀的,正是我們的文明,給我們的慾望製造了如此多的缺口,而填平他們,似乎永遠也不可能。幸福是什麼?對我們來說,可以是汽車、洋房、嬌妻、孝子或者一份體面的工作、受人敬仰、佔有稀缺的資源,做別人所不能,或者,以上全部。而對於其它生物,比如貓狗,就簡單得多了:每天三頓的美餐,一個照料它的主人,對門的異性。很多時候,我們感慨小孩子的純真,然後又質疑自己需要的究竟是什麼?其實也大可不必。當你放下了心中繁雜的慾念,將追求的目標返回到慾望被所聞所見之諸多事物攪亂之前的狀態,便也可以體味這曾經失去了的純真和幸福。
一個人要達到幸福,有兩種方法:向自己定下的目標努力並使之實現,或者降低自己的目標。這後一種雖聽了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但卻是事實,而且也更實用。因為文明帶給我們的慾望太多了,當你歷盡千辛萬苦實現了一個,另一個又出現了,永遠沒有盡頭。而如果你能夠認清自己心中最深的幾個渴望,並專心去努力,那你將會發現,其實它們並不是那麼難以滿足的。須知,小孩子和其它小動物之所以容易快樂幸福,也正是因為他們的慾望很簡單。羅素曾經說過:「我所需要的,其實只是充足的陽光、新鮮的空氣、安靜的環境、可口的食物以及一個溫柔善解人意的女子。」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