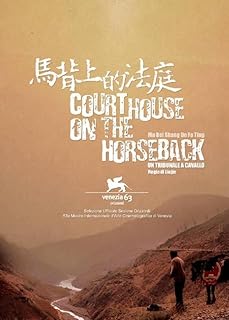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8-04-15 02:57:53
前赴後繼的奉獻
今年十月,我來到南方的邊關,第一次出警到浦寨關卡辦案的時候,車子壓著險惡的崖邊奔跑,一圈一圈環繞的盤山公路使我暈頭轉向,好在師兄的車技一流,我並不擔憂會掉下山崖。他告訴我說,他來的那年和我一樣,一上山就頭暈,慢慢習慣後就好了。我想起《馬背上的法庭》中「流動法庭」成員之一的阿洛,以及他那張在雲南邊陲蜿蜒的山路上顯得稚嫩的暈得發紅的臉。
這是一部紀錄片風格的劇情片,取材於雲南省寧蒗縣法院基層「流動法庭」的事蹟。在大山里做了一輩子的流動法官,把一生都獻給了那些和自己生活無關的村民們,也許會有人說這樣不值得。究竟值不值?電影沒有給出答案。如同那些紮根於邊關的關員們,在為國把關的使命里前赴後繼著,生活也並沒有給出他們關於值不值的答案。
電影中的「流動法庭」有三個成員:老馮、老楊和阿洛。
一、老馮
飾演老馮的李保田是個優秀的老演員,他在戲裡面的一舉一動,讓人覺得他不是在演戲,而是在生活,是一個活生生的法官,在處理家長里短的案件與雞毛蒜皮的糾紛。老馮就像我們身邊的某位老前輩,親切,憨厚,酒後話多,不修邊幅。在執法過程中常常遭遇與少數民族沿襲已久的鄉規民約、宗教風俗的衝突,老馮多次選擇犧牲自身的利益,化解村民的恩怨糾紛,做到既維護法律尊嚴,又尊重村民的風俗習慣,如他自掏腰包買豬賠給原告等。
影片結尾處對於老馮的死,處理的有些突兀,但依然撼動人心。老馮牽著老馬走在回縣城的山路上,邊走邊打瞌睡,忽然就從崖邊滑了下去,去追隨他那位二十多年前以同樣方式犧牲的戰友。那匹忠誠的的老馬馱著法院的國徽站在崖邊,國徽在落日的輝映下很是耀眼。這是電影的記錄,來源於真實事件:2003年9月,雲南省寧蒗縣法院法官魏余發和書記員馬永誌在執行「流動法庭」任務時,不幸墜入河溝……。
如果在現實中找出一個老馮的影子,他應該是個在邊關默默無聞地為海關事業奉獻了一輩子的老關員。他也許不是什麼大人物,但是深受年輕同事及地方百姓的愛戴。生活中的他是一副孤苦伶仃的模樣,因為邊關環境的艱苦,妻子兒女都不願意留在身邊,但是他從沒有怨言,他也從不講出「邊關更需要他」這樣的豪言壯語。我們不能說他不熱愛生活、不會享受生活,因為一個高尚的人,他能夠做到始終如一地尊重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二、老楊
導演特意找來當地一位土生土長的少數民族婦女飾演老楊,也就能把老楊樸實的形象更加生動鮮活地表現出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老楊經過選拔成為城裡法院的民族幹部,而到了新世紀,政策變了,沒有文憑的幹部被一刀切,於是老楊被大學生擠了下來。老楊的言語不多,一心只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從來不去思考這個社會對待她公平與否。當被告知自己要離退,將回到摩梭族山寨里再次做回普通農婦,她的眼神裡也只有服從和接受。這是一位勤勤懇懇的老幹部,即使離退前的最後一次任務,她依然如同過去的幾十年一樣處理好每件事情,依然苦口婆心地調解鄰里之間的矛盾,依然會在那條通往山寨的石路上扭傷腳。
在邊關流傳著一個詼諧的句子——「獻完青春獻子孫」。老楊與我們邊關人比較起來,境況顯得更加糟糕。獻完了青春的老楊,卻連獻子孫的可能都沒有。職業身份與摩梭人的民族身份的衝突使得她必須在工作與家庭之間作出選擇,她堅定不移地選擇了前者,以致於終身未嫁,對於女人尤其是一個傳統的少數民族女人來說,這是多麼難能可貴。她完全有權利像大多數摩梭女人那樣有個屬於自己的美滿家庭,但是她明白,既然她義無返顧地走上那一條執法道路,便不惜錯過最好的年華,即使離退之後只能按照習俗住回母家的閣樓,她樸實的內心依然不會因為孑然一身而感到些許悔恨。
影片並沒有故意將故事的主人公塑造成為英雄人物,這也是一點可貴之處。區別於我們看到的主旋律影片大都刻意迴避普通人的情感問題,該片導演把離異的老馮和終身未嫁的老楊之間的情誼刻畫的細膩含蓄,甚至都沒有點破。幾十年職業生涯的相互陪伴,已經早已不僅是一種生活狀態,更是一種沉厚而安靜的感情。當其中一個將要退休,從此不能陪伴另一個了,湧上來的離愁別緒到了嘴邊,化作一句句的叮嚀囑咐,不捨之情如流水一般源源不斷。老馮臨行之前,老楊望著他的背影大聲地忠告——走路不要打瞌睡嘎(方言),擔憂得如同一個送子遠行的母親。大概這世界上最了解老馮的人非老楊莫屬了,然而命運偏偏不善待好人,愛打瞌睡的老馮最終還是滑下了懸崖,使得他們的離別成為永別。
三、阿洛
年輕的阿洛是第一次到村里辦案,是「流動法庭」的新鮮血液,擁有大學文憑的他將替代老楊的職位。如同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中的兩個老少郵差,一個退,一個替,以共同完成一次任務的形式進行交接。初出茅廬的阿洛儘管肚子裡裝滿了條條框框的法律規章,但是他沒有經驗,也缺乏魄力,在處理突發事件時,慌張、焦急與無奈交織在一起,在複雜的現實面前顯得如此渺小,滿腹經綸在宗教、風俗和司法制度的反覆碰撞中是那麼蒼白。
阿洛的性格倔強、耿直、血氣方剛。他始終堅持原則,嚴格依法辦事,而法律與民風有時是相駁的,所以問題難免會產生。在他的眼裡看到的一切和「流動法庭」有關的匪夷所思,其實也正是觀眾無法理解的。比如普米族原告要求被告賠償的內容包括一場法事、摩梭人只願自己處理偷盜問題、彝族老爹一賭氣不願嫁女了等等,面對這些特殊情形,司法顯得如此尷尬,年輕氣盛的阿洛甚至以為用一句「封建迷信不予立案」就能打發被鄰居的豬拱了「罐罐山」(大意為祖墳)的原告,完全不知這幾乎引起兩個宗族大規模的械鬥。
每一個像我這樣初來乍到的新關員,其實都是一個現實中的阿洛。像一張白紙,每畫一筆都顯得小心翼翼,儘管如此,由於缺乏社會經驗與工作經驗,仍然難免會畫出錯誤。有時候會有好心的前輩指引一下方向,更多的時候則得不到別人的幫助,獨自在摸索前進的道路上磕磕碰碰。每天清晨,對著鏡子穿制服系領帶的時候,告訴自己這一天是新的起點,要有嶄新的姿態,要比昨天跑的更遠。對於一個胸懷夢想的人,信仰就像是母親溫暖的手,輕撫他的後腦勺,鼓勵著他勇敢地走下去。
在電影裡,我們可以看出阿洛的未來,毋庸置疑,他從此走上了老馮的路。在現實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到邊關,履行青年的使命,肩負起老前輩移交的重任,奉獻著美好的青春年華。
這是一部紀錄片風格的劇情片,取材於雲南省寧蒗縣法院基層「流動法庭」的事蹟。在大山里做了一輩子的流動法官,把一生都獻給了那些和自己生活無關的村民們,也許會有人說這樣不值得。究竟值不值?電影沒有給出答案。如同那些紮根於邊關的關員們,在為國把關的使命里前赴後繼著,生活也並沒有給出他們關於值不值的答案。
電影中的「流動法庭」有三個成員:老馮、老楊和阿洛。
一、老馮
飾演老馮的李保田是個優秀的老演員,他在戲裡面的一舉一動,讓人覺得他不是在演戲,而是在生活,是一個活生生的法官,在處理家長里短的案件與雞毛蒜皮的糾紛。老馮就像我們身邊的某位老前輩,親切,憨厚,酒後話多,不修邊幅。在執法過程中常常遭遇與少數民族沿襲已久的鄉規民約、宗教風俗的衝突,老馮多次選擇犧牲自身的利益,化解村民的恩怨糾紛,做到既維護法律尊嚴,又尊重村民的風俗習慣,如他自掏腰包買豬賠給原告等。
影片結尾處對於老馮的死,處理的有些突兀,但依然撼動人心。老馮牽著老馬走在回縣城的山路上,邊走邊打瞌睡,忽然就從崖邊滑了下去,去追隨他那位二十多年前以同樣方式犧牲的戰友。那匹忠誠的的老馬馱著法院的國徽站在崖邊,國徽在落日的輝映下很是耀眼。這是電影的記錄,來源於真實事件:2003年9月,雲南省寧蒗縣法院法官魏余發和書記員馬永誌在執行「流動法庭」任務時,不幸墜入河溝……。
如果在現實中找出一個老馮的影子,他應該是個在邊關默默無聞地為海關事業奉獻了一輩子的老關員。他也許不是什麼大人物,但是深受年輕同事及地方百姓的愛戴。生活中的他是一副孤苦伶仃的模樣,因為邊關環境的艱苦,妻子兒女都不願意留在身邊,但是他從沒有怨言,他也從不講出「邊關更需要他」這樣的豪言壯語。我們不能說他不熱愛生活、不會享受生活,因為一個高尚的人,他能夠做到始終如一地尊重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二、老楊
導演特意找來當地一位土生土長的少數民族婦女飾演老楊,也就能把老楊樸實的形象更加生動鮮活地表現出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老楊經過選拔成為城裡法院的民族幹部,而到了新世紀,政策變了,沒有文憑的幹部被一刀切,於是老楊被大學生擠了下來。老楊的言語不多,一心只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從來不去思考這個社會對待她公平與否。當被告知自己要離退,將回到摩梭族山寨里再次做回普通農婦,她的眼神裡也只有服從和接受。這是一位勤勤懇懇的老幹部,即使離退前的最後一次任務,她依然如同過去的幾十年一樣處理好每件事情,依然苦口婆心地調解鄰里之間的矛盾,依然會在那條通往山寨的石路上扭傷腳。
在邊關流傳著一個詼諧的句子——「獻完青春獻子孫」。老楊與我們邊關人比較起來,境況顯得更加糟糕。獻完了青春的老楊,卻連獻子孫的可能都沒有。職業身份與摩梭人的民族身份的衝突使得她必須在工作與家庭之間作出選擇,她堅定不移地選擇了前者,以致於終身未嫁,對於女人尤其是一個傳統的少數民族女人來說,這是多麼難能可貴。她完全有權利像大多數摩梭女人那樣有個屬於自己的美滿家庭,但是她明白,既然她義無返顧地走上那一條執法道路,便不惜錯過最好的年華,即使離退之後只能按照習俗住回母家的閣樓,她樸實的內心依然不會因為孑然一身而感到些許悔恨。
影片並沒有故意將故事的主人公塑造成為英雄人物,這也是一點可貴之處。區別於我們看到的主旋律影片大都刻意迴避普通人的情感問題,該片導演把離異的老馮和終身未嫁的老楊之間的情誼刻畫的細膩含蓄,甚至都沒有點破。幾十年職業生涯的相互陪伴,已經早已不僅是一種生活狀態,更是一種沉厚而安靜的感情。當其中一個將要退休,從此不能陪伴另一個了,湧上來的離愁別緒到了嘴邊,化作一句句的叮嚀囑咐,不捨之情如流水一般源源不斷。老馮臨行之前,老楊望著他的背影大聲地忠告——走路不要打瞌睡嘎(方言),擔憂得如同一個送子遠行的母親。大概這世界上最了解老馮的人非老楊莫屬了,然而命運偏偏不善待好人,愛打瞌睡的老馮最終還是滑下了懸崖,使得他們的離別成為永別。
三、阿洛
年輕的阿洛是第一次到村里辦案,是「流動法庭」的新鮮血液,擁有大學文憑的他將替代老楊的職位。如同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中的兩個老少郵差,一個退,一個替,以共同完成一次任務的形式進行交接。初出茅廬的阿洛儘管肚子裡裝滿了條條框框的法律規章,但是他沒有經驗,也缺乏魄力,在處理突發事件時,慌張、焦急與無奈交織在一起,在複雜的現實面前顯得如此渺小,滿腹經綸在宗教、風俗和司法制度的反覆碰撞中是那麼蒼白。
阿洛的性格倔強、耿直、血氣方剛。他始終堅持原則,嚴格依法辦事,而法律與民風有時是相駁的,所以問題難免會產生。在他的眼裡看到的一切和「流動法庭」有關的匪夷所思,其實也正是觀眾無法理解的。比如普米族原告要求被告賠償的內容包括一場法事、摩梭人只願自己處理偷盜問題、彝族老爹一賭氣不願嫁女了等等,面對這些特殊情形,司法顯得如此尷尬,年輕氣盛的阿洛甚至以為用一句「封建迷信不予立案」就能打發被鄰居的豬拱了「罐罐山」(大意為祖墳)的原告,完全不知這幾乎引起兩個宗族大規模的械鬥。
每一個像我這樣初來乍到的新關員,其實都是一個現實中的阿洛。像一張白紙,每畫一筆都顯得小心翼翼,儘管如此,由於缺乏社會經驗與工作經驗,仍然難免會畫出錯誤。有時候會有好心的前輩指引一下方向,更多的時候則得不到別人的幫助,獨自在摸索前進的道路上磕磕碰碰。每天清晨,對著鏡子穿制服系領帶的時候,告訴自己這一天是新的起點,要有嶄新的姿態,要比昨天跑的更遠。對於一個胸懷夢想的人,信仰就像是母親溫暖的手,輕撫他的後腦勺,鼓勵著他勇敢地走下去。
在電影裡,我們可以看出阿洛的未來,毋庸置疑,他從此走上了老馮的路。在現實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到邊關,履行青年的使命,肩負起老前輩移交的重任,奉獻著美好的青春年華。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