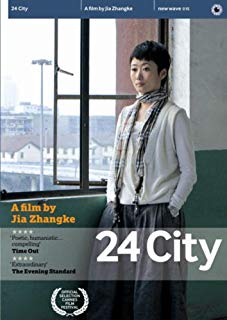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9-03-07 08:28:54
僅你消逝的一面
過去是一個倉庫,滿載著便以取用和裝配的零部件。是詹明信還是誰說過這樣一個意思。
我的過去一片朦朧。這是王小波從莫迪阿諾那裡借來贈給了小說人物王二的句子。
《二十四城記》,如同滿是零部件的造飛機工厰。走出影院二十四小時後,印象藉助睡眠和現即時間而冷卻,那些在上個夜晚曡加成完整電影的零部件似乎已各自恢復其組成部份的角色,四散於頭腦資訊倉庫的中心與角落。「實」訪談、「虛」訪談、穿插於人物訪談之間的半定格影像、蓮花般漂浮於各段落之上的詩句、語句、表情、微小的動作、有人聲的配樂、無人聲的配樂。另有在一切之上(或一切之下)被表述、等待被喚醒、或正在被創造的記憶,以及瑟縮螢幕數米以外座椅中、行走於暗街中、倚靠在酒館中那觀影者搖擺的自省。是,電影觀感從來也是自省。
虛實各半的訪談既是結構方法,又是否定電影(紀錄片)作為純粹真實歷史經驗(它到底存在不存在?)供給者的態度。結構實驗明示著記錄者和記憶召喚者的難以自棄身份,同時暗示著來自於過去的420厰空曠車間業已演化成龐大容器,充滿著可供消費的想像。九段訪談,由演員充任被訪者的虛構記錄輕鬆自若資訊滿溢,相較之下,對原420廠工人的「實」訪談大部份時候充斥著攝影機逼視下的侷促、寡言、真偽難辨的微小肢體動作。穿插在電影各個段落的單人、兩人、家庭人物畫面或許是一百多個素材訪談的副産品,或許是特意為之,但幾乎所有非訪談人物都在鏡頭前僵硬著,如同被定格的無表情靜物。我無法確定導演意圖,但過去和從某個確定存在過的歷史時段走來並在此刻被呈現的人物,或者是被動的講述者,或者是雖然沉重但仍可操控的靜物。他們在被記錄時刻的不安似乎意味著歷史始終是語焉不詳的碎片各自墜落,若要成篇成章,只能等待著來自經驗想像的表述如輕煙一般瀰漫開來。集體記憶由此有了被整合(或創造)的可能,但它難以避免地貫穿著特定歷史經驗的被動和想像編織人與記憶演繹者的主動。
電影的畫面令人焦躁,這樣的效果部份出現在影院時間,另一部份則發生在此刻對它們的零星回憶中。電影開場由主席臺望下去整齊劃一的全厰大會會場讓我難以自禁地記起瑞芬舒丹1914年驚世駭俗紀錄片The Triumph of Mind和BBC講述朝鮮大型團體操的紀錄片A State of Mind。大概是因為潛意識裡害怕追問自己的視點,這個令人不安的念頭轉瞬即逝。對於臺下人而言,這顯然是一個結束意義遠遠超出(開發商)啓程意義的會議。和如此尾音相對應的,是一度作為計劃經濟特有景觀的萬物俱全遍立全國龐大國有企業、資産和人力統一調配、大中專及高校畢業生全國範圍統一分配,以及由此被國家操控的個人與家庭命運。有趣的是,《二十四城記》中的人物(訪談對象和攝影對象)被限制在另一種統一規劃中。他們正面鏡頭,表情匱乏,個體對於歷史的反映竟如此地類同。作為個人和家庭命運操控者的國家至今面貌模糊,我們不知道它是一個空洞卻必須服從的概念,人必須為自己的存在所尋找的基於土地的情感歸屬,一種建立在理想之上的日以繼夜的想像,還是別的什麼。相對而言,要找到電影畫面、訪談形式、演員(職業演員和訪談對象)表情的操控力量來源則可能容易得多。
聲音。聲音在賈樟柯的電影裡常常猶如舞臺佈景,提示著觀衆電影所正摹擬的時代。相較低溫的畫面,《二十四城記》的聲音更加豐厚,也更加溫暖。同時,它們也是重要的懷舊元素。宋衛東(陳建斌)聊著少年時代女友和八十年代日劇《血疑》,巡夜警衛腳踏車行進中途響起葉倩文的粵語歌《淺醉一生》,小花(陳沖)踩著戲服下高跟鞋以黛玉手執花籃之姿婀娜卻一臉無謂地踏出越劇《葬花》戲文,冷硬而宏大的工業史突然在文化變遷和雜糅的聲音文化産品間變得溫情脈脈起來。這或許也是《二十四城記》的矛盾所在,它無疑有著回溯歷史,至少是接近當代工業史的雄心,但到頭來卻是在歷史終結處被抽空了立足點的唏噓鄉愁。最刻意的聲音或許是一首《國際歌》合唱。坐在室內的合唱人群看來是工厰的退休工人文體活動團體,鏡頭掠過一張一張歌唱著的臉,歌聲整齊卻無力。《國際歌》對歌唱者而言,似乎是被過濾了政治意義僅餘下學習練唱用途的尋常歌曲。如此,我們確定那一整個曾經被《咱們工人有力量》無數次歌誦的高大偉岸工人階層並沒有掌控力量,他們是時代盛景追憶者但恐怕並不真正確定盛景是否當真存在過,有著堅信自己是工人孩子必成志業的後代但他們所能做的卻是不斷逃離與拋棄。就連宋衛東(陳建斌)這樣正值四字頭的昔日國企子弟,他所能提供的竟也只是孩提時代企業子弟和地方孩子疆界衝突。這些故事,也宛若盛景當年的傳奇,但卻也不無諷刺地對應著宋衛東們曾經捍衛的疆界終將在市場轉型中不復存在,而當年子弟們強行忽略地域概念的身份認同,也因此終將在他們脫離國企舊疆土回歸「地方」之後落空成虛軟乏力的懷舊。
或許是由於詩人編劇的介入,賈樟柯開始以詩句作為段落的隔斷,通告觀衆電影意圖傳達的訊息。這讓人想起王家衛放置在《花樣年華》中的密匝文字。在《二十四城記》的真實與虛構彼此越界之外,詩人(翟永明)跨了界,導演將媒介由畫面、聲音延展到文字,電影由此設了界。儘管詩解從來是開放的,但詩句的運用似乎仍然意味著我們必須了解該如何去懂得所有已經抵達的訊息。當文字現身於電影中,或許有著點睛之美,但也必須承擔起成為冗餘資訊的風險。《二十四城記》中的詩句所面臨的風險遠遠大於《三峽好人》的「菸、酒、糖、茶」。
We that have done and thought,
That have thought and done,
Must ramble, and thin out
Like milk spilt on a stone.
『Spilt Milk』, W. B. Yeats
作為觀衆,我們在螢幕上讀到的葉慈是翻譯成中文取為電影所用的葉慈。恐怕如牛奶一般潑灑在石上並非我們曾做過的、想過的,而是曾經有所為、有所思的我們,必將面對風流雨散、疏離如葭菔的結局。近兩小時的訪談,到頭來是被串聯組合的自傷身世。
整個玻璃工厰是一個巨大的眼珠,勞動是其中最黑的部份。
——《玻璃工厰》,歐陽江河
用於《二十四城記》時,「玻璃工厰」因地制宜改為「造飛機工厰」,於是,整個造飛機工厰是一個巨大的眼珠,勞動是其中最黑的部份,卻始終敵不過「他日葬儂知是誰」的黯然神傷。直至,氤氳霧氣中我們讀到:
成都,僅你消失的一面,足以讓我榮耀一生
《二十四城記》近尾處四川詩人萬夏的詩句,它似乎曾經是「成都,僅你腐朽的一面,足以讓我榮耀一生」。與此同時,我們看到成都的鳥瞰城貌。這句詩和這個畫面幾乎是朋友們在酒館裡爭論的導火索。《二十四城記》是否關於成都?如果是,成都是所指還是能指?如果二者皆非,那麼《二十四城記》是關幹什麼?在恰逢「五 · 一二」地震之後的坎城影展,這或許並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但是,「成都」是什麼?是宋衛東們曾經與之衝突的非420廠疆界的「地方」?是被挑選出來作為工業史題材載體的420廠變遷的地域載體?是早於三峽移民、早於進城務工鄉村人口的老國企跨省遷徙人生最終賴以託付鄉愁的非鄉之鄉?如此,榮耀否。整部電影,我們聽到的都是聲音,但同時,被經濟體制和國家建設規劃南北一統的衆生命運必須啞言噤聲。老國企人生似乎得到的關註最終不過是漫漶成足以令人問「偽」的懷舊,懷想之中,往事在一個曖昧不清的「成都」皆成榮耀。但除了高高在上無形貌可以描述的操控者,從興建到消失,塵揚霧散父輩自榮光且綿延至我代,誰可確定。
僅你消逝的一面,或足以讓我負累一生。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