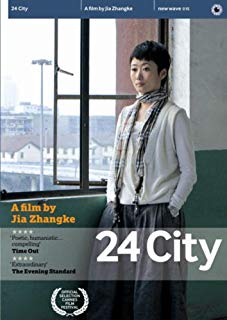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9-03-10 02:10:22
二十四城記:一個廠,一座城,一個國
廠是420廠,城不是成都,國卻是當下的中國。
一、言說
賈樟柯無疑是十足自戀的,這裡的自戀沒有任何貶義,而是說他對自己的電影方式和自己的生命情有獨鐘。《二十四城記》在賈樟柯的作品序列中處在一處轉折點,賈樟柯用這部影片對此前的作品做了一次有趣的總結。原諒我只能用「有趣」這個詞,當然也可以說是奇妙的,因為這部片子在我的視野里,是中國電影序列里僅見的「仿紀錄片」(Mock Documentary指用紀錄片手法和表象拍攝的故事片。當然「紀錄片」這個詞本身也是裂隙縱橫,至少包含了三種以上的不同影片類型,此處從略)。而這次影片又像一次長長的注目禮,對賈樟柯自己的電影作品,更是對中國當代史的後半段——於是我知道賈樟柯無論是從表達欲到敘事野心,都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這部影片顯然是過份表達的,因為「表達」或者「言說」甚至成了直接的表象和影片的主部。此前我與大多數人一樣,沒有在大螢幕上看紀錄片(無論是哪種的紀錄片)的經驗——最多是在教室看過投影。這一次我的震驚體驗大概與超級寫實主義的油畫類似,影院的大螢幕上訪談和「訪談」的單調構圖對我形成了極大的衝擊。而賈樟柯的策略,或者說影片結構,則是「真假參半」,用訪談和記錄引入規定情境,然後再用一樣的手法——被放大的「言說」——來進行敘事。試想倘若不是呂麗萍陳沖趙濤陳建斌,那麼她(他)們的「扮演」行為是不是仍然能夠被指認?或者,那些「受訪者」同樣也是在「扮演」?這裡涉及到攝影機本身的權力問題,也就是說在攝影機下展示出來的是否還是「真實」,那麼賈樟柯的回應則是兩種——第一、有且只有言說,而言說的內容只好請觀眾「腦補」(腦內補完);第二、用職業演員的扮演在某種程度上提示這一「言說」的實質。換言之,我們並無必要去追究那些事「是不是真實發生的」,當然可能有一個丟了孩子的母親,在一本或者可能存在的《成發集團發展史》中有記載;或者也可能有一個酷似陳沖的上海姑娘——但是這些不是重要問題,重要問題在於這一切的呈現方式。
因為「言說」這一表象的存在,以及前30分鐘的訪談和後75分鐘的「訪談」具有了某種程度上的互文關係,有必要強調的是,「訪談」中的「故事」可能是特定場景下的故事,也可能是對生活的某種提煉。實際上除了第一個訪談,此後的訪談都具備充分而完整的故事性,它們就是故事本身,由此也再次對故事進行了自指——賈樟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因為如果不用這種手法,這部片子要嘛是一個N段式電影,要嘛是一個依那裡圖式的多線交織的後現代故事片。
於是從這個表象入手,對《二十四城記》的解讀就會完全改變,因為首先重要的不是影片內容而是影片的形式——對純形式的解讀完全可以導向某種意識形態批判。當然可以把這種手法理解為缺少投資和缺乏能力——試想以這部高清數字電影的成本如何能cover一個跨越40年的史詩級別的故事?但是我傾向於認為賈樟柯的這種手法是有意為之——至少他不隱藏導演和攝影機,並且曝露了故事的講述機制。
二、敘事
或許剛才的分析會導致對這部電影「形式大於內容」的判斷。而就影片試圖表達的內容而言,無疑是大大溢出了影片的範圍。影片呈現的是一段歷史,那麼這部影片自然進入「當代史敘述」的序列中。420廠的歷史,與中國當代史基本是等價的——從「以小見大」的角度來說。雖然當代史的禁區依然是禁區,比如文革(第一段訪談裡的武鬥),比如八九(好像與本片沒有關係),但至少賈樟柯還講到了不可繞開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去年對新時期的回顧之中絕少提到的話題。當然大書特書的則是93年資本主義化進程開始之後的「分享艱難」,呈現方式則是講述之中對「昔日榮光」的懷念和受訪者無一例外的眼淚。賈樟柯最嫻熟的技巧——用流行歌曲來標定時代——又一次成了他在影片中的簽名,也是他一貫從大眾文化的角度結構當代史的方式。
受訪人物的出場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從建廠之初一直到現今的「80後」。一共8個受訪者,其中4個演員,3個「真人」,剩下一個趙剛——大概能各算一半吧。這也是頗具形式感的安排。賈樟柯並無意通過他們的講述構築一個整體的敘事,但這些生命片段的交織卻產生了某種蒙太奇層面上的意義。其實一個人的生命,講述出來不過也是如此幾句。在這些講述之中,我們得知了420廠的變遷——它著實是一處「飛地」,如《世界》裡的世界公園一般,超大規模的移民,一個工廠甚至成了一個小型規模的城市——有學校、電影院、游泳池,大量穿著統一制服的工人——大型國有企業的普遍處境。似乎用「折射了中國社會的變遷」來下按語是個不錯的選擇。但是我想說的是,這部影片裡的「工人階級」多久沒有在影片中出現了?曾經的「工人階級專政」似乎也不再作為一個常見的提法了。而最後工廠變成樓盤,似乎也是某種當下資本取得勝利的隱喻。於是成都終於把曾經的飛地吞入肚中,榮光無限的工人階級也光環不再,終於還是在社會巨變面前成了各謀生路的市民。
就「當代史書寫」而言還可做出一篇大文章,但無論如何,賈樟柯這次展示出來的卻是從《站台》一以貫之的視野,而《三峽好人》之中的潛台詞——郭斌曾就職的工廠,以及作為「福建女老闆」的翟永明開發的地產——在這裡被詳細的呈現。賈樟柯作為「70年代生人」的自覺使得他對80年代的敘述格外地精彩,附帶地也造成了某種斷裂和含糊,尤其表現在某種「更久遠」的歷史的狀態下。
三、觀看
賈樟柯的風格,或者說是「作者要素」,在影片中依然熟悉,比如逆光的窗戶——得自侯孝賢的一種構圖方式,還有很多,比如舉著吊瓶的呂麗萍等等。當然非常明確的一個前文本是《三峽好人》,《二十四城記》同樣在處理「拆遷」這個命題,於是很多鏡頭都很相似,賈樟柯式或者餘力為式的小橫移,但由於高清本身的問題使得運動鏡頭不太流暢,還有最後一個俯瞰成都的鏡頭,明明就是《三峽好人》的情緒的延伸。於是《二十四城記》同樣具有了某種史料價值,我曾在對《三峽好人》的評論中說「《三峽好人》真正所講的故事是後工業時代中國的一個城市如何將要被廢棄,如何正在一點一點消失,從而構建的一個關於現代社會的寓言。」而《二十四城記》要講述的則是更深刻和更直接的層面上的問題——不是因為要建水電站,而是因為資本的介入;不是一個城市的消失,而是某個與紅色歷史相關的「飛地」的最終消失——這是否也是對紅色歷史的某種評判我不得而知。
然而還可引起注意的是訪談人物的選取,女人——四個女人,尤其後三個,承擔了不同程度上的悲劇。如果不是毛的軍工企業「靠山方針」,那麼侯麗君的母親與外婆是否不會分離十幾年,是不是那麼多東北人不用穿越大半個中國來到四川,是不是大麗丟失的孩子能夠被找到,是不是顧敏華不會陷在成都和上海的夾縫之中而孑然一身?這些問題不是我能回答的。但是有趣之處在於,女人們的講述和男人們的講述是完全不同的。除開第一位受訪者何老先生,陳建斌扮演的副廠長和作為主持人的趙剛顯然都是成功人士,或許是我的誤讀,或許也是《渴望》以來的中國情節劇苦情戲的傳統使然。當然最精彩的段落是陳沖的20分鐘——首先視覺上呈現為人物和人物旁邊的鏡像,而顧敏華和小花本身也是一組鏡像,在加上陳沖這個集兩個角色為一身的演員,實在是頗為精緻的結構。當然導演安排陳沖觀看電視中《小花》的段落,於是這就呈現出一組「歷史的鏡像」,影片的結構意義從而也被揭示出來:那正是處在當下的人們對歷史深處自己的回望,以及注目禮——是行禮,更是送別。
放在「第六代導演」的序列里,作為核心表徵的「自視」依然在這部影片中佔有重要位置。不過《二十四城記》更像面對心理醫生的一次訪談,結論,大概是最終的療愈吧。
至於賈樟柯刻意不讓身為易太太的陳沖打麻將,而讓趙濤扮作王佳芝去香港跑單幫,只能看做是他的惡趣味……
四、賈樟柯
最後要說的則是有關「電影的事實」。賈樟柯作為新科金獅導演和法國電影界的至愛,本片入圍坎城理所應當,但是獲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評委大概完全不知道這部電影在說什麼。有趣的地方是本片在國內的某種程度上的悖反——評論以批居多,票房卻是意外的好,上映三天過百萬,雖不及某片和某片的一個零頭,但終歸是小賈老師的個人票房最佳了。
至於原因,我似乎可以拋出一個類似「後奧運時代電影格局」的概念。這個過程大概要追溯到02年《英雄》開啟的中國式大片時代,此後在《無極》形成怪誕的電影文化氛圍,而電影觀眾回歸理性之後,似乎有了「春季檔」的概念——比如去年的《立春》和《左右》,甚至細微到「三八檔」——比如《雙食記》。《二十四城記》號稱也是三八檔,當然這一切都與所謂「三代廠花」的劇情簡介一樣不靠譜。而奧運會開幕式作為08年度第一大片,實實在在地展示了中國電影文化的深刻程度——有個冷笑話叫做中國是世界上最熱愛電影的國家,因為中國連國歌都是電影插曲——而對奧運開幕式的評論,先批後贊,最後抓了央視當替罪羊,又成為終結華語大片時代的怪誕鬧劇的標誌。
我所謂「後奧運時代電影」大約伴隨著院線的增加,公映影片的增加,影評作用的強化以及觀眾逐漸的理性觀看。02年到07年的狂歡客觀上也培育了進一步市場和觀眾,而同時伴有的則是藝術片的逐漸浮出水面,隨著電影文化的發展和資源的普及,看多了各國商業片和大眾藝術片的觀眾也能夠接受國產藝術電影了,這大概是本片小小票房奇蹟的原因。但是對本片批評的聲音卻很多。看了一些評論,好像本片有不止一個版本——至少我今天在影院看的115分鐘版本里沒有華潤的廣告,沒有趙濤哭著說我就想在24城給父母買棟房子這樣的台詞,我猜想大概是公映版本與宣傳的免費版本的不同?當然更核心的原因是,賈樟柯曾經作為一代文藝青年的必修課深人人心,而這些文藝青年未必接受這種影院的觀看方式——賈樟柯的片子,應該是非主流的,被禁的,只能通過下載和盜版得到的,某種接頭暗號式的存在,而如果他上了院線,就是墮落了——這大概是對一部份影評進行精神分析後得出的結論。可是不要忘了,賈樟柯根本就是一個看著港片長大的導演——而且電影說到底是要賣錢的。
現在回想起來,06年還上演過「《三峽好人》pk《黃金甲》」的喜劇,而所謂「觀眾」早已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但電影文化卻實在短短幾年間生根發芽,於是終於我們不再同一時間只有一部電影可看,於是「看什麼」和「怎麼看」也逐漸成了問題。當然賈樟柯的形式主義仍然在考驗觀眾——因為對這部影片,收回成本甚至賺錢都已經不再是問題,大約說到最後,覺得影片值不會票價的人也不在少數,是不是這也是批多於讚的一個原因?然而我想說的是,在與宣傳完全悖離的影片面前,似乎未經訓練的觀眾難於找到一個立場,大概這又導向了「首周輿論決定論」。
五、二十四城記
於是在只有4個人的小放映廳裡,我看到了這麼一部賈樟柯依然在關注流動和尋找的影片。這部影片裡充滿著逝去的歲月的哀傷,它關於一個廠,一座城,一個國:這座廠可以是任何一個經歷了和經歷著中國當代史巨變的大型國企,裡面有眾多渺小的人,也有眾多巨大的廠房和機器,有太多的悲喜日夜上演;這座城不是任何一座城,而是一個漂浮在空中的城市,它在這裡降落,一如《孔雀》和《立春》裡的鶴陽,而這座城市終於會消失,一如《三峽好人》裡的奉節,在這裡,這座城變成了資本洪流之中的一棟樓盤;而這個國家,是反反覆覆被講述的中國,關於歷史也關於未來,關於故事裡的人和我們這些聽故事的人。你說歷史是有意義的嗎?你說是不是只有故事才是歷史,還是歷史本來就是需要被講述為故事?於是我們更願意坐下來聽一個故事,聽那些遠去的昔日榮光,聽這個時代不斷成長。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