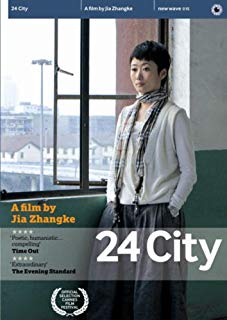2009-03-19 18:31:28
我們當下的城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1
二十四城芙蓉花,錦官自昔稱繁華。
片子起頭的兩句聽著就不倫不類,影院回來網上一查,原來所謂的「古詩有雲」是地產開發商杜撰的,難怪難怪。這個年代全民都有文化,受各級政府「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影響,就算是街邊開的燒餅攤和餛飩鋪也要立塊牌子:「本燒餅源自北宋仁宗年間,安徽有一位屢試不第的舉子……最後發明出一種皮脆油香的燒餅,流傳至今」。這一度讓我覺得幾千年的文化藉助每天的早點在我胃腸間蕩漾。
2
賈樟柯的片子習慣性地關注這些當下中國隨處可見的荒謬,不點破它,僅僅作為一個記錄者。作為記錄者的賈樟柯是合格的,有歐洲人給他的小金獅子為證。從《小武》開始的劇情片,無一不充當著紀錄片的角色。到了《二十四城記》,小賈說,我要商業。於是片頭的演員卡司里不僅僅是趙濤,而是呂麗萍、陳沖和陳建斌。四個專業演員加上若干群眾演員,互不相幹的故事拼接出一部所謂的偽商業紀錄片。就影院反響來看,並沒商業起來。我去的UME雙井店,直到電影開場前的半個小時,仍然只有我一個人買票進場。但是影院人員告訴我,如果只有一位觀眾的話,場次將自動取消。
本場最終觀影人數為,八人。
3
這種商業性的嘗試毫無意義。拋開一切可能的商業噱頭,幾乎所有的情節都只是依靠演員的口述,就像是講故事大賽在海選。在這一表演程式下,專業演員沒有任何優勢可言。很少有人能準確地把握普通受訪者接受鏡頭採訪時那種又原生態又緊張又想矯飾嚴肅的心理狀態,除非他自己就是普通受訪者。在三位大卡司里,陳沖給人感覺最到位,大概是她雙手不斷的揉搓,把這一緊張情緒充分外化了出來。陳建斌中規中矩。呂麗萍的北京口音和表演痕跡則很難讓人信服她說的故事主角居然是她。但無論他們中的哪一個也無法和公交車上的侯麗君相比——和大牌演員不同,侯的表演,或者說表情,有時甚至可以說不合常理,該哭時笑,該笑時哭,但細細想來,生活就是如此。我想這就是專業和非專業的區別,劇情片和(偽)紀錄片的區別。
喜歡看大牌的觀眾不會滿意,因為大牌沒演戲,只簡單地說了幾句話。喜歡看原生態紀錄片的觀眾不會滿意,因為有幾個明知道是假的當事人混了進來。
記得開篇的一個鏡頭,清一色工作服的背景下,人頭攢動。你無法特異地辨識出其中的任何一張面孔。這是讓人放鬆的氛圍。而當演員的面孔被熟讀它的觀眾辨認出來,賈導,觀眾們已經齣戲了。但這也許是導演追求的間離效果。對不住導演,這是我的臆測。
4
間離效果。
也許和編劇的背景有關,包括似通不通的「二十四城芙蓉花」在內的大量詩句,以黑屏字幕的形式強加在講述段落之間。毫無疑問,這處理的功效很強大。比之《三峽好人》中的「煙」「酒」「糖」「茶」四個段落,這些現代詩的點題作用頗為奇異。當觀眾去思考這些晦澀的文句時,實際上他們已經齣戲了。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陳沖飾演的顧敏華,說當年廠子裡的小伙子都說她像《小花》裡的陳沖。場子裡的觀眾都善意地樂了,這並不突兀。
起到類似作用的還有音樂。就像賈導之前的《站台》《小武》《任逍遙》一樣,流行歌自然地穿插在段落與段落之間,但效果卻迥然不同。前面這幾部作為紀錄式的劇情片,流行歌往往出自主人公之口,如《任逍遙》中郭彬彬結尾處大段的清唱,和《小武》中歌廳裡濫俗的《心雨》。《二十四城記》則是標榜劇情片的紀錄片,讓講述者講著講著突然開唱顯然不好——那不就成了《新白娘子傳奇》了嗎?於是導演的處理是,讓講述者說出一首歌或一部電影,在這一段的結尾才將它的原聲覆蓋在鏡頭的畫面上。這讓觀眾更多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外人。於是顧敏華提到了《小花》,結尾處陳沖就立在灶台前看著電視裡她自己扮演的小花。趙剛提到了《外面的世界》,結尾處《外面的世界》恰如其分地響起,也恰如其分地被一塊砸玻璃的石頭斷然中止。
這塊石頭又把我帶入戲了。
5
對於《二十四城記》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專業演員的表演和情節配置「壓抑地做作」上。實際上這是同一個命題:對於一套文化語境的熟悉與陌生。
電影裡的口音是一般觀眾最喜歡挑剔的地方。這容易理解:普通觀眾對枯燥的電影表演理論沒什麼認知,但明白一個理兒——他演員口音不標準,我聽得出來。你說你演的是成都人?那你咋個說起了重慶話?《姨媽的後現代生活》里趙薇演技著實可以稱道,但一口太假的偽東北腔卻輕易地讓螢幕前的東北人出了戲——也許東北以外的觀眾並沒有這種感覺,趙薇學說的可能正是他們心中的東北話。
《二十四城記》里,群眾演員的口音不必說,地道是必須的。相對來說幾位大演員就沒那麼自然了。呂麗萍的東北+四川背景,卻是一嘴北京口;陳沖是個例外,她地道的上海話加上越劇的幾句唱在前後沉悶的段落中間倒顯得十分出彩;原本滿嘴山西醋味的趙濤這回大練倒口,講起了四川話,據當地人評價,聽得想罵人。
在口音以外,人們第二位可以評論的就是劇中人的生活狀態。和地域分明的口音不同,即便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人們也完全可能對彼此的生活狀態不甚了了。於是大批生活在與片中420廠類似的大廠中的孩子們說,向人民幣保證,賈樟柯說的都是真的,我的生活就是這樣,感謝賈導還記得我們。而其他一些人卻認定賈的做作,在他們的視野里,賈樟柯極欲表現的依然是他眼中壓抑的沉悶,而且這沉悶並不具備歐洲式的優雅。
我想毋需懷疑賈樟柯片子的紀實性,即使個別細節出於配合主題的需要刻意安排了某些道具,在大方向上必然是紀實的。問題在於,賈的電影中,這些紀實成份之間的選取和排列是出幹什麼樣的考慮?在以往的賈式電影中,導演習慣於將大量素材擺放在觀眾的面前,而並不給出解釋或者答案。無法清晰地看出導演的意圖和態度,這是所謂第六代導演的通式。這樣的好處顯而易見,缺憾之處在於它有種置身事外的冷漠。在《二十四城記》中,偽紀錄片的體式更加強了這種置身事外的態度,也許只有黑屏時閃過的幾句現代詩或多或少地描述了導演或編劇的意志:「整個玻璃工廠是一隻巨大的眼珠,勞動是其中最黑的部份」。究其根本,仍然沒有說清楚什麼。
這樣看來,「壓抑」一說自然有它的道理。賈導在羅列了大量事實之後一如既往地讓片子戛然而止,只用一句詩「僅你消逝的一面,已經足以讓我榮耀一生」來扣題結束——實際上是讓這些講述中的壓抑延續下去。如何結束這些壓抑?賈導認為沒有必要去在影片裡解決,實際上生活中各人有各人的道行,沒有過不去的事,但這與導演與電影無關。而賈導的願望,僅僅是記錄下成都或大廠們「消逝的一面」。在賈樟柯的片子裡,仍然看不到救贖。你可以說這是壓抑,也可以說這是他的特色鮮明。
6
時代符號仍然在講述中閃著光亮。抗美援朝,對越反擊戰,大軍工廠的興衰,保密單位的保密費,廠子和地方孩子的打架(這段故事很豐滿,與之類似的還有部隊大院和地方孩子的對立,農村和城裡孩子的對立,這些在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和王文濤《假若明天來臨》等作品裡有豐富的參照),知青返城,《小花》引領的新審美時代的開端,甚至,周總理逝世。
7
影片以樓盤為名,卻不夠給勁。結尾處如果導演乾脆剪入一段「二十四城」的房地產廣告,我認為會比現在的環城長鏡結尾更有力量。實際上他所說的商業恐怕並非指找了幾個專業明星,而是直指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的必然變遷。變化中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就像侯麗君所說:大家都沒遲到過,大家都沒出過錯,但大家都下了崗,廠子養不了這麼些人了。言語間明辨而超然:有事幹,老得會慢些。呂麗萍流著淚說:汽笛響就相當於吹了軍號,必須得走。而丟了的孩子再沒找到。
片子裡的大家都很和諧。沒有靜坐抗議的,沒有聚眾鬧事的,沒有消極止步的,有的只有積極地生活。這恐怕也是賈導有意為之了。回到前面的命題:導演的傾向和意圖是什麼?與之題材相似的《鐵西區》,才是真正的紀錄片,相比之下,《二十四城記》中有意無意總會體現出導演取捨的意志:煽情而和諧。
8
說了一些雜亂的看法。回到片子本身,它確是給了我意想不到的感動。呂麗萍說,從瀋陽坐車到大連,再坐輪船去上海,在上海換船,沿長江一直到重慶,再從重慶坐車到成都,從瀋陽到成都,走了十五天。我聽到這裡不知道怎麼,忽然眼淚止不住地流。實際上感動與否全在於影片與個人體驗的交融,不只為片中的他們唏噓,同時值得感喟的還有自己。於是回憶自己在瀋陽的故事,在上海的故事,在成都的故事,也許和他們所說的,也有共通。
病床上呻吟的第一代老工人,廠房間等待機器拆遷的工友倆,為支援西部大廠建設全家移民卻丟了孩子的老女工,下了崗的女工,停薪下海的工廠廠花,把青春愛情記憶都留在廠子裡的上層領導,踏進工廠大門又決心退出的年輕子弟,爸媽就在工廠卻從沒進過工廠的新時期工廠兒女,隱形的採訪者像藝術人生一樣,引導他們講出最感觸或傷感的那一段。相信總有某個段子能讓你淚流滿面。
侯麗君說,我媽從瀋陽來成都,十四年,才第一次回去。家裡人當時真的是,抱頭痛哭。抱頭痛哭。
悲憫或無關己事或高高在上的鏡頭向下俯拍。就看見了來自瀋陽,大連,上海……又豈止是來自二十四個城的無數年輕人,湧入這光榮的工廠大門,他們都是這消逝著的見證,但他們的到來並不僅僅是為了見證這消逝。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