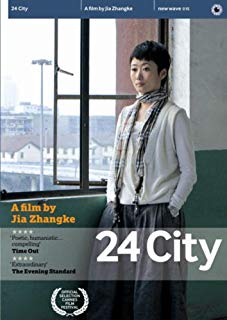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9-03-25 12:16:05
還是賈樟柯
終於盼到24城記在法國上映了,雖然比在國內晚了兩週(在中國2009年3月6日上映,在法國3月18日上映)。我今天一早去看的早場。這是一家專門放藝術電影的老電影院,保持著17世紀的建築風格,問了售票的姑娘,這座建築是在17世紀建成的,最早的時候是個歌劇院,後來在20世紀初改做電影院,還曾經在這裡放過默片。仔細環視了一下,賣票的正對著的牆,有一整面浮雕,雕的是古代劇場的場景。買票的門迎的樓梯是木結構的,上面有精美的雕塑,一對雄鷹。裡面是小廳,放映廳是清一色紅色的座椅,大概能坐100人左右,廳的牆上掛著17世紀人像的繪畫,牆上的燈是典型的傳統的歐式風格的。這一場的上座率並不高,我數了一下,應該有十個人,加我十一個,其他的人都是白髮蒼蒼的法國老奶奶。和其中的一個老奶奶聊了起來,她說起賈樟柯猶如如數家珍,她說她看過賈樟柯的站台,三峽好人,而她最喜歡的賈樟柯的電影是世界,她說起賈樟柯很激動,她說那是她所理解的中國的現實。想想在我們還在到處找賈樟柯的盜版DVD的時候,法國這邊的觀眾就能在大螢幕上看到站台了。
電影準時開始,沒有放像其他電影院開場前的廣告片,電影伴著軍號的響亮聲音如期而至。就這一聲軍號,就彷彿把我從幾千公裡的法國,拉回北京,回到我生活的軍隊大院,也是每天的軍號聲,從早起的第一聲,到中午吃飯前,到晚上開飯前的廣播,伴隨我從小到大,每天生活中的軍號聲。
對於這個電影想說的話很多,這裡只是想記一下我覺得印象深的幾個地方:
首先,是正面。每個人物出現第一面的時候都是正面,都是一個正面的鏡頭,會停留大概10幾秒,就像照一張固定的照片,只不過是用攝影機拍的。讓我第一反映想到戈達爾,戈達爾在他60年代的電影裡就常用這樣的鏡頭,那些工人,直對著鏡頭,對著攝影機「拍照」。24城記裡的那些「人像」,你仔細觀察他們會發現:他們會忍不住的發笑,會動一下耳朵,會動一下眼睛,彷彿是觀眾正在給他們「照像」。
然後,是關於真實,關於記錄,關於真實和虛構,關於演員。什麼是真實?怎樣才是真實的表達?是故事片還是紀錄片?我注意到在法國的網站allocine上面寫到這部電影的類型,寫的是紀錄片(documentaire)。我個人以為,對於這部電影來說,這部電影是真實的,無論是演員,還是非職業演員,紀錄採訪中的工廠工人,這部電影帶給我「真實的感受」,所以我說它是真實的。紀錄片裡時常沒有扮演的角色,而歷史書里,我們又能分得清哪些是真實,哪些是虛構。而對於演員,我想說得只是,再好的演員也總是有演的痕跡,而表演的最高境界就像布列松在他的《電影書寫札記》中寫道:「不在於演得「單純」,或演得「內在」,而在於完全不演。說回來,每個段落,所有說的這些我感到是真實的,每個人說的部份我相信都是真實的,有跡可尋的,換句話說賈樟柯是做了「功課」的,一年多一百多個受訪者,一本中國工人訪談錄。至於電影的形式是用訪談類的電視節目(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還是用「開心辭典」(Danny Boyle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還只是讓不同人上車交談(阿巴斯的十段生命的律動),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電影用他們的方式紀錄了,紀錄了一個廠的變遷,紀錄了一個人的境域,紀錄了一些人的煩惱憂慮生活。賈樟柯在這裡更像是一個藝術家,在今天藝術家的功能重新讓人們審視,藝術家是最後一個能批判現實的武器,作為藝術家的賈樟柯,他用他熟悉的方式,提示人們那些遺落在角落裡的不該忘卻的記憶,那些日常生活中從指縫間溜走得點滴。那些當年的證件,票證,那些拆掉的廠房,移走的機器,是不是連就所有的記憶一起都移走了那?移廠子大門上的廠名的時候,讓我想到了wolfgang becker的電影「再見列寧」,在那部電影裡,當我看到列寧的雕像被直升飛機移走的鏡頭時候的震撼,哪些是真正該移走的?該走是真的都要走嗎?那什麼可以留下來?感謝賈樟柯,留下了這些述說,讓我們留住那些記憶,曾經我們真實的生活的印記,刻在腦海裡的印記是拆不走的,生活還要繼續,讓我們更懂得珍惜,更堅強的面對生活。
關於空間。採訪者在怎樣的環境裡接受採訪,如果看的話會發現這裡每個場景都是精心設計的。這不光是拍電影,電視做節目也一樣,紀錄片又何嘗不是加入了導演的設計在裡面。這裡受訪者都在他(她)們合適的地點接受採訪,每一個採訪的地點都符合被採訪的人的身份和特徵,都是導演精心設計的。那些空間,依舊是賈樟柯注意營造的,在廢舊的工廠廠房,在工廠的禮堂,禮堂的舞台作為人們打羽毛球的地方(空間的多樣性,像他的「公共場所」),在開動的公共汽車上(移動的晚上的城市是變化的背景),在工人的家裡,還有那個像工人活動俱樂部的地方,(有可以打麻將的地方,還有「小花」唱戲的地方,那裡還有圖書閱覽室),在簡陋的理髮店裡,在籃球場上,在樓盤的售房處,在長滿油菜花的田間背景是24城,在廢舊的中學教室裡,在電視塔的旋轉餐廳,所有對這些空間的紀錄見證了變化。
關於細節。在這些受訪者的採訪場面里,道具的設置,有好幾場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水杯,不同的水杯見證了不同的人的身份地位。就像在三峽好人裡的趙濤一直拿著瓶礦泉水的水瓶。每一個場景,每一個細節都是導演特別注意到的,都有時代的痕跡。
關於大眾文化,流行文化。還是一樣的賈樟柯,從「小武」走到現在,他的音樂,他對大眾文化,流行文化和他的電影影像的結合,還是一貫的那個「小賈」,他的選擇,用流行音樂,流行文化作為另一個「演員」,一個「完全不演」卻「演技高超」的「演員」。
關於那些引用,如果說劇情片更像小說,那麼賈樟柯的電影更像是散文,他不講故事,只帶給人們情緒,某些方面應該更像是詩。那些詩句,對我而言就像中國繪畫的留白,中國傳統文人講究的意境,這些留下的空間讓人去想像,有很多的詩句表達的情緒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不知道在和我一個電影院看賈樟柯電影的那些法國老奶奶,通過那些法語翻譯的字幕能否體會出黛玉葬花的意境,但是我相信她們應該能體會到電影的情緒,她們是不是也曾經在窗前久久的等著自己的兒女回家。整個電影,對我而言,就像賈樟柯做的一個當代藝術的展覽,只不過這一次的展廳不是在博物館,而是在電影院,在這裡他給我們呈現了幾代人生命的痕跡,他給我們選了那幾部要重新溫習的電影,連續劇,和歌曲,同時賈樟柯還給我們了一份書目,一個圖書館。
關於煽情,如果說以前的賈樟柯,對煽情還有所收斂的話,那麼這次的賈樟柯,卻完全繼承了某些電視訪談類節目主持人的強項,玩命煽情。我的眼淚嘩嘩嘩的流特別是在公共汽車上的那段訪談:當那個女工人說著一口東北話,說起她的母親從瀋陽來成都,幾十年沒回去看過姥姥姥爺,她第一次回老家的時候,姥姥姥爺抱著她的母親抱頭痛哭的時候,我的眼淚也忍不住流了下來。想起我的母親也是10幾歲出來當兵,回姥姥姥爺家的時候,我還小,當時的我還不懂為什麼我們走的時候姥姥姥爺會哭,現在姥姥姥爺已經都不在了,但是我終於明白了,兩個老人送我們離開的場景,兩個老人一直在那裡,久久的不肯離的場面,卻永遠的在我腦海里,是我最經不起觸摸的神經。現在我在法國讀書,爸爸媽媽每次送我去機場,臨走的場景又同樣浮現,每次在飛機上空,看著漸漸離我遠去的城市,北京,我生在這裡,走到哪裡都懷念的地方,我現在所有的努力,都為有一天能重回你的懷抱。
關於工廠大門。1895年,在法國的里昂,世界上第一個版本的「工廠大門」。那也是一個下午,在盧米埃爾兄弟工廠下班的時候,工人們都從工廠的大門走出來,那是盧米埃爾兄弟帶給我們最初的對電影的認識,工人們穿著20世紀初的服裝,成群的從工廠大門走出,114年後的今天,我們又看到了中國工人從工廠大門中走出,他們將走向何方,等待他們的又將是什麼?賈樟柯從一開始就沒離開電影的真實,真實的電影,他帶我們重新回到電影的本原,讓我們看到那些被我們忽視了的久違了的日常生活和點滴記憶,那才是電影的最初,也是電影的本質。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