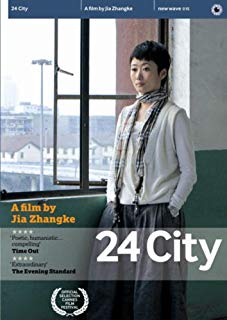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9-03-25 20:17:09
二十四城,傾城之愛
輕傷的人過來了
擔著心愛的東西
沒有斷氣的部份
脫掉軍服 洗淨全身
使用支票和信用卡
一個重傷的城市血氣翻湧
脈搏和體溫在起落
比戰爭快
比恐懼慢
……
——瞿永明《輕傷的人,重傷的城市》
賈樟柯曾在拍攝《二十四城記》前接受記者訪問時提到,為了更準確的捕捉成都這個城市的氣息,他特意選擇與成都著名女詩人瞿永明合作編劇,希望在這部影片中增加一些詩意的想像和女性的感受。而瞿永明的這首《輕傷的人,重傷的城市》已經很準確的說出了城市與城市中人的身體的創傷。在這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城與人一樣傷痕纍纍,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要做的恰好是如何彌補這種傷痕。
成都東二環外一片840畝土地上,存在了50年,是曾有近三萬職工,十萬家屬的一家工廠。過去叫做「成發集團」,再過去叫「420廠」。一年之內工廠遷移拆除,今後這裡將誕生「二十四城」,一片巨大的商業住宅區,整個區域的地產開發將持續30年。賈樟柯的新片《二十四城記》便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開始了一次遷移的記錄。
由於《二十四城記》與新樓盤的名稱一樣,於是有些人開始揣測這是否是賈樟柯給地產開發商做的一次「超長版的廣告」。可是看完整部電影,我感受到的確是毫無保留的愛,一種傾城之愛。
從420廠到二十四城,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在這個劇烈變化發展的過程中,城市與人都面臨著同樣的考驗。在這個劇烈變化的過程中城市中的人從一個穩定的群體逐漸成為一個個動盪的個體,必須以個人的身份在這個世界單打獨鬥。《二十四城記》的意義正在於給了這些生命一個宣洩的出口,讓他們坐在攝影機前講述自己的生命,並在述說的過程中與我們一起撫慰傷口。
瞿永明說,成都在飛速發展,420廠卻停滯了,他跟這個時代脫節,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420廠原本作為一個自成一體的小城鎮一般自給自足,如今癱倒的廠房相比對面平地而起的巨大高樓顯得渺小而又破敗不堪。跟城市中的人一樣,城市也在這種不斷地搬遷變化重建中變得千瘡百孔。表面上,那些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和同樣轟轟烈烈的市場化改革,早已讓一個工廠的盛衰變得微不足道。一個群體的命運,嵌入時代「必然性」的滾滾洪流中,無聲無息,又驚心動魄。時代的巨輪無聲輾過,420們支離破碎,模糊不清,彷彿一夜之間,置換了天地。可誰又能保證今天的「二十四城」不會是明天的「420廠」呢。
這樣說來,《二十四城記》既不是對舊城的貶低也不是對新城的頌揚,對於生命一視同仁的人性關懷才是現代的城市最需要的姿態。
同樣《二十四城記》里深藏在這種記錄風格中的冷靜與客觀,表達出的確是深沉濃厚的情感。雖然有人質疑這種記錄與虛構並用的風格,以及非職業與職業演員之間表演的落差。然而對於一部電影而言,表達永遠是第一位的,只有發出自己的聲音,走自己的路,才能讓這場表達產生意義。雖然早在《二十四城記》之前這種紀錄片與劇情片套用的方式已經開始實驗,但是大部份的導演所做的嘗試是將紀錄片以資料的形式加入到劇情片中,使情感的推動更真實,可是《二十四城記》確是反過來將劇情的部份嵌入到記錄之中。故事就在講述者口中,相比非職業演員的真實講述,職業演員塑造的角色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雖然所有的講述者之間都沒有直接的聯繫,可是這種潛在的人物關係卻在這巨大共通的命運之下產生了更緊密的關聯。他們即是講述者也是其他講述者的觀眾,換個角度,同樣生活在城市中的我們既是觀看者也可能是那個螢幕上的講述者。而《二十四城記》里最大的講述者其實正是城市本身,同樣最需要撫慰的傷口正是城市的傷痕。
「二十四城芙蓉花,錦官自昔稱繁華」,殊不知城市在這樣太平盛世的表象下有多少暗流湧動,而這種湧動的情愫終於在《二十四城記》的傾城之愛中得到了撫慰。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