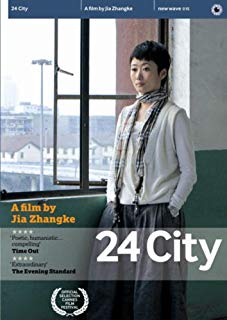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9-04-01 09:29:34
悲情二十四城
1. 詩意
「二十四城芙蓉花,錦官自昔稱繁華」——這是賈樟柯在《二十城記》中給電影定下的詩意懷舊基調。《二十四城記》承載詩意的主體——成發集團,曾經的國營420發動機製造廠——於1958年從東北南遷至成都,2008年老廠房拆除,工廠整體遷移至郊外工業園區,市中心的舊址被房地產商買斷,將開發成為住宅區「二十四城」。420廠的前二十多年歷史是真正的「昔日繁華」,通過多位被採訪者口述片段的邊邊角角表現出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也能月供肉三斤,令人羨慕的福利待遇和工資收入,子女就學分配就業的便利…… 採訪對象的年齡從高到低,視角變化由舊到新,繁華走向沒落,輝煌變作冷落。
從被採訪對象的選擇上來看,賈樟柯對被攝題材的感情是不言自明的。儘管他拍攝電影的初衷是「記錄中國曆史的變遷」,但他並不像拍攝紀錄片一樣站在一個客觀的,儘量脫離個人情感的視點來完成這種記錄——他也無意掩蓋自己的「不客觀」——他選擇的都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從《小武》到《任逍遙》到《世界》到《三峽好人》,再到《二十四城記》,他選擇記錄的是社會的暗角,是弱勢群體面對變遷的徬徨與無所適從,是小人物直面大時代的勇氣與犧牲。在「記錄」的過程中,賈樟柯也並不執著於「發生真實」,比如《三峽好人》中凌空飛騰的樓宇,還有《二十四城記》中由演員扮演的受訪者。他將「發生真實」等同於「故事真實」的手法和美國作家Tim O』Brien的越戰回憶錄寫作手法殊歸同途,這樣的敘事方法早已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故事片」「紀錄片」之分,二者都是導演用來表明白身藝術理念的手法罷了。所以在《二十四城記》中,420廠真正員工的採訪錄和演員表演出來的採訪錄相互交織,「發生真實」為「故事真實」的導入,「故事真實」為「發生真實」的補充。不論是哪一種的真實,他所表達的,都是對被採訪對象的真切同情與敬意,每個鏡頭都浸透了他的無限深情。
2. 悲情
《二十四城記》中九位受訪者,五位真正的420廠工人,四位演員,八個談話段落都有一個悲情收尾。但這還不夠——為了進一步昇華採訪的主旨,賈樟柯在段落之間引用了多首詩歌,插入了相關的流行歌曲,並重複了受訪者的收尾語。這種央視東方時空般的悲情轟炸式剪輯方法讓我有點錯愕。照理說,在觀眾對影片大環境與中國工廠變遷心知肚明的情況下,過份頻繁的重複同一種情緒是政治宣傳才用的低級手法,而一貫以靜默鏡頭語言為標誌的賈樟柯,突然跳到對岸手舞足蹈起來,這讓人在感情上很難接受。就好比顧長衛在《孔雀》中用做番茄醬的細節來表現七十年代,但如果人物一邊做醬一邊頻頻嘮叨物質匱乏冬天吃不上蔬菜,那我就得狠狠皺眉。
為了打破單一化的悲情氛圍,賈樟柯在段落間也使用了多種調劑方法,比如廠房裡兩位拆卸機器的工人,一個摟著另一個的肩膀拍攝靜態鏡頭,兩人本來神情肅穆,可其中一個時不時要動動另一個,結果大家都忍不住笑了;還有下一代的小姑娘站在廠房裡巨大的電風扇前,風把頭髮吹得很亂,她笑得很靦腆很甜。當然,專業演員的使用是電影最大的調劑,尤其陳沖飾演的顧敏華訪談片段。這裡,賈樟柯甚至還幽默了一把,讓陳衝開自己也開觀眾一個玩笑;但嚴肅的賈樟柯畢竟不太會說笑話,或者說,這個笑話講得十分之冷,就跟《三峽好人》里貿然升空的大樓一樣,最後的結果並非幽默,而成了無所適從。
其實早在2007年,杜海彬的紀錄片《傘》就已經嘗試了記錄中國某個弱勢群體面對巨大的社會變遷尋找出路的題材,影片從廣東中山一個小鎮的制傘工廠車間工人的機械重複性手工勞動開始,以河南洛陽某鄉老農的自述訪談收尾,提出了「中國農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的大問題。在表現手法上《傘》過份的追求客觀讓其失去了「觀眾緣」,其反響還不如《二十四城記》的零頭;但如果對比一下杜海彬和賈樟柯對訪談的處理方法,就能夠看出來,賈對情緒的安排是多麼的任性與單一。杜海彬的《傘》採訪了雨傘廠的工人,求職的大學生,還有河南洛陽老農。悲情與沉重的情緒同樣浸透鏡頭,但杜海彬只允許自己結尾放鬆了一次,他在大部份時間裡的敘事風格與許鞍華的《天水圍的日與夜》非常相似;杜海彬缺乏的,是許鞍華所擅長的段落之間的小調劑小抒情,是「放」的層次。而採取了詩歌起題、串聯並高調收尾的《二十四城記》,在表達詩意的同時竟然忘記詩歌語言本是最講究留白的,要想情緒迸發得多輝煌,前面的鋪墊就得多隱忍多壓抑!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缺乏的正是「收」:情急情濃當然是最好的出發點,但導演的情緒再濃烈也不該氾濫到整部影片,完全失了調度,讓悲情悲到滲出水來,從而變得廉價。
3. 觀眾
在比較《二十四城記》與《天水圍的日與夜》過程中,我覺得很難脫離「觀眾」這個要素。賈樟柯是很在乎觀眾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在乎,所以情急意切,生怕觀眾不能領會他在鏡頭背後的想法,所以要反覆明示:述說,詩詞,歌曲,字幕。而且許多處詩詞的插入也並不圓熟,譬如歐陽江河那句「整個玻璃工廠是一隻巨大的眼珠/勞動是其中最黑的部份」,姿態便無比做作。但也許我本來就不該如此苛求,他是大陸唯一一位拿到商業投資後依然在忠實記錄社會弱勢群體的「大格調」導演,比起他的執著,任何批評似乎都是一種錯位。
但每當我想到天水圍,想到許鞍華,我又無法遏制自己心中的某種不滿。這部從王晶那借了五十萬才得以成形的小製作,這部從出發點就洗盡鉛華平實到底的作品,其帶來的心靈震撼,卻遠遠超越了我本該更有生活體驗與共鳴的「下崗」、「整改」、「遷移」。我並不介意「發生真實」與「故事真實」的穿插,一次次的訪談也的確讓我動情落淚;但眼淚不該是情感的終結,也不該是最後的交代,我更想要的,是眼眶潮濕只一滴淚將落未落的度量,是胸中萬言,出口卻只有一聲長嘆的回味。
有人說《二十四城記》像一首晚唐的詩歌,關心民眾民生,悲憫卻不憂傷;但我依然希望賈樟柯能夠將「悲」影像化而不是語言化,將情緒收斂化而不是放縱化。在改革開放的巨變中成長起來的我們,傷痛記憶是心房上的灰色烙印,再沉默也不會消失;我們只需要一個閘門,一個出口,我想要流著自己的眼淚,就像我們的父輩流過他們的汗水一樣。
二十城與天水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ea3820100cwjg.html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