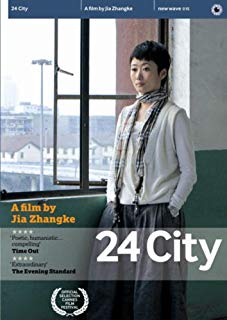2009-04-01 22:24:23
二十四城之二:汽笛. 集結號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60年代。奉節碼頭。
大麗的兒子在船即離港時不見了蹤影,但她自覺到作為黨的女兒,作為一名軍工廠的工人,在壓頂的巨慟面前,與自己的丈夫同志一起,沒有提出要求船隻延遲起錨,沒有脫離隊伍留在碼頭繼續尋找。一聲汽笛,掩過了革命倆口子心底撕心裂肺的哭喊,劃開了大麗數十年無法癒合的傷口,拉起了她餘生悲喜的大幕。
這聲汽笛,與遠在山東汶河畔響起的那一聲遲來的集結號遙相呼應。
漫山遍野,白雪皚皚,40餘名烈士長眠曾經戰鬥過的土地。一目幾近失明的穀子地,再次換上洗得發白的軍裝,手捧兄弟們用生命和歷史贏得的一摞勳章,雕塑一般佇立。首長一聲「委屈了」,鎮魂的集結號清亮響起。四十幾名軍人,四十幾條漢子。組織的集結號,炮火紛飛中,不曾拯救他們的生;硝煙散盡後,卻榮耀了他們的死。
汽笛,集結號——傳遞國家的需要,國家的召喚。對於這些汽笛和集結號的召集下的祖國兒女,誰又能說那就不是一種信仰的召喚?那就不是母親的召喚?
我深深觸動於《二十四城記》中那一群普通人的平靜和堅韌:片中他們在灰暗的現實生活里,他們那樣的娓娓道來自己的故事,沒有口號,沒有主義。他們的表情有麻木、有無奈、有嘆息、有凝重、有憂鬱、有滄桑、有苦澀、甚至有痛楚,但是從他們的眼中看不到,從他們的嘴裡聽不到怨恨和戾氣。而正是有一股怨氣和戾氣,遊蕩在當下的中國,瀰漫在種種對立二元間的鴻溝間,化為質疑、抱怨、謾罵、顛覆、甚至是血腥的報復——群體性事件的多發,讓公安系統從去年起集體升級,上層各級公安局長進「班子」,基層各哨崗加強放襲擊演練。
那位被公交車拉著穿梭城市的中年女縫紉工說,自己應國家減員增效的需要,第一批被裁掉。「其實誰也沒有錯」,被裁職工們自問數十年如一日不曾遲到不曾犯錯——這也得到了主任的承認,然而,他們自己也承認:主任沒有錯,廠子沒有錯,國家沒有錯,其實誰也沒有錯。
那就是時代的錯?作為個體,誰又能與時代理論?不能與之理論,對錯又有何意義?
然而這或許就是最大的意義。
下崗後的她們唯有掩淚裝歡。不只是掩淚裝歡,他們還要徹底收起眼淚,市場看不見眼淚。他們在這座城市,開始自己城堡外的生活,不論是擺地攤,還是做縫紉,不論是陪笑屈膝,還是與城管打游擊。城堡可以在歷史中灰飛煙滅,生活卻不曾一刻停息。
當那場沒有硝煙的革命在中國城市裡漸進展開時,我還是個不聞政治耽於玩耍的孩子。我不曾在當時當地見證、感受到這場變革。而今,作為電影的觀者,我無法斷言眼前眾生經歷和經歷過那場變革時的內心世界。子非魚,安知魚之苦樂?今天的我和昨日的他們,因為文化-心理構成之斷層,因為我們對那段歷史的漠視,兩者之間的隔膜之深,使得我們或許只能以子觀魚。縱使我們懷著「同情之理解」,化而成魚,又奈何我們不曾同屬於一片水域,一則歷史之上游淵源綿長,一則歷史之下游百折千回,一則理想主義的滾滾奔騰,一則市場大潮的水廣浪高:試問又安可真知其樂?又安可真知其苦?
作為他們的後輩,我唯有懷著謙卑之心,真誠地揣度。我是相信賈樟柯的真誠的,選擇這段歷史作為鏡頭的對象,本就是一種真誠的選擇和嘗試。然而,真誠的初念,是否就能帶來真切的理解?即使有幸獲得真切的理解,又能改變些許什麼?
我驚詫於歷史洪流下,這些安靜的角落,這些失聲的角落。在宏大的喧囂下,個體命運的悲喜,竟是這樣的脆弱而堅韌,背負著歷史,也記錄著歷史。
我想,對這種堅韌的理解,可以生發出對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裡的子民,生出嚴肅的敬意,生出痛切的反省,生出溫暖的關懷。
而對這種堅韌的理解,不應成為對既定歷史「是然」輕率的漠視。須知歷史盤點,誰也沒有慷慨的權力抹掉這些「歷史的零頭」。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