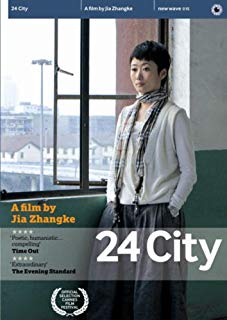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9-04-24 06:15:01
兩部電影一種生活
觀看《一一》和《二十四城記》是一種艱難的過程,這種艱難不僅體現在對單機位長鏡頭美學的接受上,更融入於整個觀影體驗中,當電影中那些訴說和他人單調的生活被我們接受時,我們會覺得生活中隱藏的一小部份開始隱隱作痛。此時電影講述的就不再是激動人心的故事,而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堅忍的活著和傷感的老去,那種生活的體驗成為了我們生命中的一部份。就如《一一》裡的胖子所說的,電影發明後我們的生命延長了三倍,因為電影時我們對生活的經驗至少擴充了兩倍。
《一一》和《二十四城記》的故事都是淡如清水,沒有跌宕起伏的波折和峰迴路轉的高潮,然而這就是生活,如我們多數人的生活一般,有喜有悲。電影把我們的生活壓縮到一盤膠片中,但同時不能損害它的原汁原味,因為這種生活的原味正是使我們久久回味的東西,因此這種電影必須是嚴肅的,鏡頭必須是簡潔的,方有如此才能表達對生活的尊重。單機位長鏡頭取代了多機位蒙太奇,聲畫對位在時空穿越中展現了人物生命的聯繫,這樣的拍攝手法更好的保存了時間和空間的完整性,體現了電影的本體性——對生命記憶的保存。
《一一》和《二十四城記》都講訴了三代人的生活。第一代的人老去,心裡滿是對生活的體驗卻已無力訴說,第二代人體味著時光流逝和生活的枯燥滿是傷感,而第三代人,他們的生活是未知的充滿希望的,是重複過去還是新的開始,這看似自由的選擇背後,當那些生活的經驗被灌輸於意識中,他們看到他們的長輩所經歷的生活而隱約的構想到自身所要經歷的生活,那時生命便是一種重負,每個人都像《一一》中的洋洋那樣開始感慨,我感到我也老了。
在兩部電影中,面對鏡頭所有的人都處於一種訴說的狀態,而這種訴說是欲說還休的。《一一》中的NJ和舊日的戀人互相傾訴著過去的美好時光,《二十四城記》中呂麗萍扮演的工人在訴說著工廠昔日的輝煌,而當他們從記憶中回到現實發現那些燦爛的光只是過往雲煙時,都忍不出潸然淚下,於是回憶戛然而止。他們都承認了現實對於生命的磨礪,繼續堅忍的生活。那時是什麼觸動了我們內心,我們也開始傷感。一種幻想的美的破碎,那一地碎片卻構成了真實中殘酷的美。
最偉大的影片莫過於講述生離死別,宏大的敘事往往滲入到微觀的描述中。在《一一》和《二十四城記》里,這種描述滲入到每個人心裡最脆弱的地方——時間對於生命的破壞。《一一》中的外婆老了,躺在病床上插著氧氣管的她不再是那個氣質優雅的女人,《二十四城記》中老工人的師傅老了,面對著鏡頭表情痴呆的他只有在回憶廠子裡工作的時候才能顯露出神采。那個下崗女工人講訴她姥爺送她去火車站的場景時忍不住哭了,那時我們的心都刺痛了,那樣的場景是我們都曾經歷的,身邊熟悉的人一天天老了,我們在體驗蒼老的過程中感悟到時間的殘酷。
這兩部電影都在講述著一段集體記憶,時代的變遷和個人在時代中的境遇。《一一》中的NJ無法忍受商場的欺騙和背叛而失落。《二十四城記》中的工人因為無法接受下崗的事實而意志消沉,是時代變化的太快還是我們思維轉換的太慢,有時我們或多或少的都會跟不上時代的腳步,而時代的風向何時又會轉變,我們都無從猜想。《一一》中的社會與我們有些遙遠,而《二十四城記》中變遷則是我們每個人都能體會的。抗美援朝,三線建設,文革,總理去世,體制改革,時代變化影響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目前一個鏡頭陳建斌扮演的工人還在工廠的球場上打球,隨著一個黑場球場就變成了一個喧鬧的工地,昔日繁忙的車間只剩下一片慘敗的景像,我們感受到了時代給與我們每一個人的重負。
我們的生活就是如此重複著的,日復一日,而我們似乎難以發覺,電影將我們平時難以發覺的部份殘忍的展露在我們面前,這就是影像的魅力,就如《一一》里洋洋說的,我將你看不到的東西展現給你。我們意識到了我們的生活如此單調,但又無力改變。這是一種尼采式的永恆回歸式的命題。我們只是在重複前人的生活,然而生命的價值如何體現?尼采眼中的超人不做模仿他人而是做被他人模仿之事,是他們創造時代。而我們只是時代中的沙礫,我們活著,死去,體驗著生活的喜怒哀樂,承受著時代加在我們背上的一切,追求幸福,忍受挫折,我們垂垂老去,最後回味昔日的甜蜜,留下淡淡傷感,這種體驗世代傳承,這就是我們的生命。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