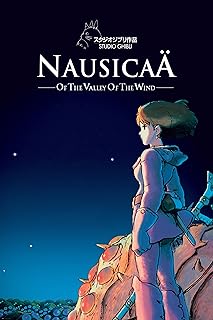電影訊息
風之谷--Kaze no tani no Naushika
編劇: 宮崎駿
风之谷/风谷少女/KazenotaninoNaushika
![]() 8 / 183,824人
117分鐘 | USA:95分鐘 (edited version) (1985)
8 / 183,824人
117分鐘 | USA:95分鐘 (edited version) (1985)
編劇: 宮崎駿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9-12-15 20:54:37
押井守與宮崎駿的戰爭
「其實押井守和高中生的宮崎駿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的相遇成了很大的契機,改變了自己的戰場,從此在同一個戰場上共同戰鬥,因此在不同的方面可以發揮自己的力量,在此期間形成了自己的創作特色。」(鈴木敏夫)
無論我們所敘述的這一對中心人物是否真的帶有一點醜小鴨式的自卑感或是帶著點高頭大馬的高傲形象,由他們名字來看,一方確實是彷彿深不見底,而另一方則像是畫地為牢,但共同點,均不能出逃,從未真正擺脫過自己的命運。在談及兩位大師之前,我們還是先會提及一個19歲少年——在1984年時曾是19歲的少年,那年他在影院觀看了《福星小子2:Beautiful Dreamer》和《風之谷》,於是一切都改變了,不管是他自己的世界,還是對於未來日本動畫界的格局。
《福星小子2:Beautiful Dreamer》和《風之谷》正是押井守和宮崎駿的起點,即便它們並非處女作;而1984這一年被坊間稱作「日本動畫大師元年」,則可謂名至實歸。
這兩位監督在大師元年之前一年第一次相見,但此後共同的頑固性格卻逐漸促成了他們各自為陣,同時他們的特點也因此跟著日益鮮明起來。1985年,押井守和宮崎駿所謂的「交惡史」便從此拉開了序幕。
「他給我的第一印像是個很輕鬆愉快的人,但是當討論漸漸熱烈起來的時候,他卻完全不給你留點餘地。他精力旺盛到令人難以置信。他也很積極而且愛講話,彷彿誰說的多就比較厲害似的。每次說話我們總是想要去說服對方,所以真的很累人。」押井守當然不能算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但這回確實是遇到對手了。這第一次的會面讓宮崎駿在押井守心中留下了「他真是個混球」的印象。
「交惡」這個詞出自《左傳·隱公三年》,意思是「雙方感情破裂,互相憎恨仇視。」因此,我們可以總結到的重點是,交惡雙方必定曾是惺惺相惜的。
自從與大塚康生合作了《魯邦三世:卡里奧斯特羅城》之後六年,宮崎駿再次接到製作「魯邦三世」劇場版的邀請。那是1979年獲得大藤信郎賞的影院處女作,但老爺子沒有再做一次的打算。也許他早已有以後不管做什麼樣的動畫都將成為這個獎項的常客的覺悟。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種商業動畫短週期高強度的作業令他心有餘悸。這「魯邦三世」第2部劇場從開工到影片上映僅僅花了半年時間,按照宮崎先生自己的說法,「從這個作品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體力的極限」,這種玩命的努力對身體力行的人來說尤其會後怕。
在這種情況下,謝絕邀請當然是明智之舉。宮崎駿於是轉而向製作方推薦了押井守。那大約是雙方認識兩年後的事情。
因為大塚康生是「魯邦三世」的作畫監督以及基調奠定者,同時又在東映時期在工會與宮崎駿有同志之誼——1964年的時候宮崎駿當上了東映動畫勞工協會的秘書長,當時高畑勛是該協會的副主席,而大塚康生則是主席——於是宮崎駿的推薦很快成行。雖然之後企劃並未能有著落,大塚和押井仍然結下了濃厚友情,以致在拍攝寫實電影《紅眼鏡》(1987)時,大塚康生不僅客串了該片,甚至還為此提供了自家的吉普車以供拍攝之用——如果換作宮崎駿,是絕對不會做到這種程度的。
1985年,押井守如此興緻勃勃地將自己的《魯邦三世:完結篇》企劃交於製作方——原作粉碎機並非浪得虛名,至少是嚇到了製作方,於是宮崎駿拒絕了製作方,而製作方拒絕了押井守。這件事的陰影使押井耿耿於懷了十年,直到1995年《攻殼機動隊》的上映才得以釋懷:「在攻殼的時候終於能擺脫魯邦了!」
1968年,製作了三年的《太陽王子》上映。這部由大塚康生(作畫監督)、高畑勛(監督)以及宮崎駿(場面設計)合作的動畫被視為突破原本動畫風格的第一大創舉,同時亦為後來日本動畫「原創化」及「漸進式動畫」運動打下了基礎。宮崎駿和押井守亦是參與後來的日本動畫「原創化」及「漸進式動畫」運動的舉旗者——雖然同為偏執狂,但仍然,兩人心存的理念著實相差巨大;比起宮崎駿,押井守也許與高畑勛更有共同點。
押井守在提及高畑勛時說:「表面上,高畑先生也很喜歡和人爭辯,而且拼命想要說服別人,但是在內心他是個很不一樣的人。宮崎先生有著很可愛的特質,他的哲學最後總是一句話:『好的東西就是好,管它什麼邏輯!』但是高畑先生則是個徹頭徹尾一致的人,他非常講究邏輯。我曾聽大塚康生先生這樣形容高畑先生和我:高畑先生像是一個『在走路的邏輯』,而我則像是『邏輯在騎腳踏車』。」
正如大塚先生所說的,他們有著邏輯感上的相似之處,一種持續創造求新的追求,只是緩急的程度不同而已。這也就是為什麼高畑勛可以捨棄吉卜力慣用的透明畫材動畫、嘗試利用數位技術使用鉛筆線的形式與水彩色調的顏色製作出素描般的作品《我的鄰居山田君》;而押井守也可以發明一個「剪貼片方式」(Live-mation)讓弟子神山健治拍出《機動警察 迷你版》、讓同為「龍之子四大天王」之一的西久保瑞穂拍出《宮本武藏:雙劍馳騁之夢》、或讓自己拍出《立食師列傳》這樣的東西來——彷彿某種必需要發生的強迫症;與此同時,宮崎駿甚至連電腦也不會去碰,人工以外的作畫手段都不免會讓他產生鄙視之心。
只比宮崎駿大了6歲的高畑勛就像是宮崎駿的兄長——19歲和13歲的兄弟這種情況,而比押井守大了10歲的宮崎駿卻完全不像是戒掉了孩子氣,並隨著年紀增長滲入的老人頑固脾性而變得愈加傲慢。高畑勛和宮崎駿這對組合能一直保存下來實在是一個奇蹟;另一方面,高畑勛的冷酷、彷彿不會真正受傷或是簡單承認失敗的性情也真正吸引著押井守。
總之,性格決定了押井守與宮崎駿並不能真正走到一起,這也連累到押井守最終不能和吉卜力走到一塊;而「魯邦三世」劇場版的否決則成了這一場背道而馳旅程的導火索。
在押井守入行後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德間書店旗下的月刊動畫雜誌《Animage》創刊。這是個極為重要的事件,至少對像宮崎駿和押井守這些當年還是新人的人來說,它就像是動畫界的《名利場》,而德間康快(作為一個法人代表)就像是他們的伯樂。
1981年,從龍之子分離出去的小丑社由於人手緊缺,才得以讓時年三十而立的押井守著手《福星小子》的動畫改編事宜,也藉此機緣讓押井守得以在原作粉碎機的道路上肆無忌憚。
時年同樣是宮崎駿人生轉折的一年。時任《Animage》總編的鈴木敏夫當年原本打算採訪因「世界名作劇場」系列功成名就的高畑勛,但卻意外遭到拒絕,於是轉而做了資歷尚淺也沒有什麼名氣的宮崎駿的訪問專輯。於是在鈴木敏夫和德間康快的牽頭下,宮崎駿於次年開始在《Animage》上連載《風之谷》的漫畫,連載一年後,《風之谷》劇場動畫開始製作,到第三年《風之谷》上映並大受歡迎。
《風之谷》成了宮崎駿的甘苦分水嶺,而就在此前,也就是拍完「魯邦三世」劇場到得到德間書店提攜並最終催生《風之谷》的「黑暗三年」里,想拍出屬於自己的電影的宮崎駿到處推銷自己的作品,但卻屢屢碰壁。「帶著泥巴味兒」,「陳腐老朽」,企劃案大多都只得到這樣的評價。但遇上德間書店卻並非最大打擊的終結,這只不過是事業下坡路的結束。
這是踏上甘苦分水嶺的前夜,在《風之谷》的動畫製作過程中久病纏身的母親過世,這才是足令宮崎駿懊喪一生的事情。「如果不能娛樂於人,也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這個「人」最開始的自然是指自己的母親。押井守曾隱晦地提及,宮崎駿這個人受過去的羈絆太深,除卻其它一些事情以外,大抵就是暗指宮崎駿的戀母情結。這位堅強的女性對宮崎駿影響至深,以致他眾多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少都會有一兩個源於她的,甚至可以說,宮崎駿最初投身動畫事業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為了讓她高興。化悲痛為力量,這可能是當年喪母的宮崎駿腦中唯剩的堅持,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成全了他。宮崎駿的母親如果泉下有知必定深感欣慰,因為在最黑暗的那幾年之後,她的兒子在日本動畫界國民級的地位從此無人能撼動。
到1985年,吉卜力工作室(Studio Ghibli)也藉此契機在德間書店的投資下建立,取名源自二戰時候義大利的一款偵察機,意為「撒哈拉沙漠的熱風」。宮崎駿的父親是個造飛機的,而押井守的父親不過是個經常得不到委託因此經常多出時間帶兒子去影院的半調子私家偵探和幾乎全職的失業者,這可能也是押井守所有的不安的緣起,而出生富足的宮崎駿則絕對不會存在這樣失衡感的擔憂,他不會像押井那樣對這個人生存在那麼的置疑,再加上吉卜力的成立,就他而言,從此算是有了個家;也許從一開始宮崎駿就把吉卜力當成是自己的了。於是宮崎駿更加安穩地做夢冒險,創作不再推陳出新,只是按部就班,一個個實現那些早已計劃好的夢,對於他來說,人生就是如此,這樣的人生就足夠了;但押井守因為諸多原因卻不得不繼續生活在一個不可名狀的時空中,好像永遠都沒有凝聚實體的機會似的。
這種情況下,直到1988年監督《機動警察》時遇到剛剛由石川光久和後藤隆行成立的Production I.G(在Headgear的前提下),押井守的創作才算正式又邁進了另一個臺階。
當年時任《Animage》第二任主編的鈴木敏夫後來成了吉卜力的社長,而正是因為此人在「福星小子」第1部劇場版製作後的引見,成就了押井守與宮崎駿的第一次面談;那種情況下,《福星小子1:Only You》也成了宮崎駿唯一誇過的押井守作品,到《福星小子2:Beautiful Dreamer》時宮崎駿的評價就變成了:「不明白有什麼好的」。
但不管是宮崎駿還是押井守,他們與《Animage》的關係都非同一般,以致在最初因為1983年那場《Animage》訪談會上建立的「友誼」而做過「開啟時代的終結-宮崎駿與押井守的關於《機動警察2》的對話」(《Animage》1993年10月184期)以及「押井守談宮崎峻」(《電影旬報》1995年7月16日1166期)這樣不可思議的互動性話題的訪談企劃——那時他們終於都是公認的大師了,也許因為《千與千尋》還要過上幾年才上映,而正在路上的《攻殼機動隊》說不定還讓押井守暗自持有更多的自信和優勢。雖然押井守此時的底氣相比十年前會更足一些,但面對喋喋不休的宮崎駿,押井守其實仍是個悶騷男,話會相對少一些,但也看似深奧——只是宮崎駿自然完全不會吃這一套。所以從兩個訪談你會看到一些火藥味,但是屬於那種受潮的感覺,相當的平靜。
總之,押井守並不在乎激怒一些人,但最初對宮崎駿的敬仰之情讓他還是會顯得相當地小心翼翼,至少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葉仍是如此。押井守並不在乎激怒一些人,有時候他就是刻意地去激怒某些人,這也成了他最後被踢出日本動畫工業體系中第一部長篇動畫系列《福星小子》製作組的原因所在——即便他的老師鳥海永行也保全不了他,因為開始有人出於並非仰慕的情感每天給他寄信,恐嚇信,或者內含刀片的恐嚇信,最後小丑社不得不將他從《福星小子》的製作組撤職斬首。然則,這次的撤職斬首與一年後魯邦三世劇場企劃失敗的打擊比較起來簡直可以說是快感無比:押井守於《福星小子》TVA第106話退下陣來,那是1984年3月26日,從1981年10月14日開始,他總共折磨了高橋留美子原作長達兩年半時間,而且有幸在退下陣來的一個半月前(2月11日)將奠定自己影像風格的《福星小子2:Beautiful Dreamer》順利搬上影院並獲得當年《電影旬報》的觀眾票選位列第七位的最佳電影——當年排第一的自然是宮崎駿的《風之谷》。
日本大阪產業大學經濟學部教授高増明這麼看押井守:
「電影評論家前東京大學校長蓮實重彥對同樣在影片中登場人物的對白採用哲學言論的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Arsenyevich Tarkovsky,押井守的女婿乙一便是這位的愛好者)給予這樣的評價:『不愛電影,卻被電影所愛的存在。』借用這句話,押井也同樣,也許屬於『不愛動畫,卻被動畫所愛的存在』。」
當年押井守毅然離開小丑社成為自由人從某些方面來說要拜他在此前一年開創的新的動畫銷售模式所賜,不然縱然是破釜沉舟也只會敗的一踏塗地。這就是原創錄影帶OVA(Original Video Animation)這個新鮮玩意兒的誕生。
1983年12月發售的OVA《宇宙戰爭》(Dallos)第一捲,時長半小時,由鳥海永行參與、押井守監督並由天野喜孝繪製了錄影帶封面。藉此契機,從1983年的OVA元年開始,更多動畫人投身到這種更富自由氣息的創作中來,製作出了諸如《無限地帶23》(Megazone 23,1985/1986/1989)、《機器人嘉年華》(Robot Carnival,1987)、《機甲獵兵》(Armor Hunter Mellowlink,1988)、《超時空要塞 外傳》(Macross Plus,1994)等不朽的經典和傑作;而押井本人也是創作情緒空前高漲,這其中除了腰斬的《迷宮物件》(TWILIGHT Q,1987)以及《機動警察》(Mobile Police Patlabor,1988)第一部OVA——同期宮崎駿的劇場動畫《龍貓》上映,還包括了更早之前的在德間書店資助下製作的「魯邦三世」怨念產物《天使之卵》(Angel's Egg,1986)——同年宮崎駿的劇場動畫《天空之城》上映,等等;與押井守不同的是,宮崎駿此時甚至連電視動畫都極少涉足了,更別說OVA這種新生事物了,《風之谷》的成功讓他開始了對劇場動畫的一生迷戀。
在當年《天使之卵》的製作名單中,除了貞本義行、名倉靖博等人外,還有吉卜力的高坂希太郎以及保田道名等人;此外,據說庵野秀明過了兩週「苦行僧一樣的生活」後逃離了製作現場。換個角度說,相對劇場而言,OVA可以說是窮人玩的東西。沒有最窮,只有更窮,《天使之卵》的推出並未為押井守帶來市場聲譽,因為主題晦澀讓人儘是避而遠之了,「害得我好幾年都接不到委託」,押井多次在採訪中提及此事的後果。這讓雖然非常看好押井守的鈴木敏夫也毫無辦法,尤其是在接二兩三的吉卜力邀請破滅的情況下——企劃敗北的頻繁程度讓1985的「魯邦三世」劇場版未遂事件簡直不值一提。
1987年前後可以說是押井守最糟糕的時期,讓他彷彿頓悟的表面之下受挫的心更加慌恐。而與此同時,宮崎駿不僅贏得了市場的肯定,媒體的讚譽,大小獎項更是拿到手軟;宮崎駿的信心也變得更加勝氣凌人,以致於後來有這麼個非常著名的事件——當美國《新聞週刊》問及他的《千與千尋》獲得奧斯卡獎吃驚與否時的回答:「事實上,我對貴國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更吃驚,更厭惡。所以我對是否領這個獎還有點猶豫。」
押井守似乎從來沒能成功從宮崎駿那裡沾到光,不管是最早的兩部跟義大利合作的動畫企劃《歇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和《滿月傳說》(THE FULLMOON TRADITION INDRA),還是後來的《錨》(Anchor),最終都因雙方創作理念的堅持或是意見不一而流產。《歇洛克·福爾摩斯》就是後來宮崎駿和御廚恭輔共同執導的《名偵探福爾摩斯》,而《滿月傳說》最終也只是由鳥海永行執筆了小說版,《錨》企劃中止後則由夢枕獏執筆了小說版。
後來同樣來自於吉卜力邀請的《墨攻》動畫版企劃(酒見賢一原作森秀樹作畫的漫畫,也是後來張之亮執導劉德華主演的同名電影來源),以及準備OVA化《宮崎駿的雜想筆記本》中的《多砲塔的出場》(多砲塔の出番)等等企劃最後也都在一片爭執聲中成了笑話。
除了押井版魯邦三世,此後像什麼押井版《銀河英雄傳說》(石黒昇換將上陣拍了近12年)、押井版《鐵人28號》(在動畫未果的情況下改編成了舞台劇,最近又有將舞台劇改編成真人電影的打算)、以及《最後的立食師》(立食師怨念可以說與他的戀狗癖一樣的強烈)、日劇版《日劇版 祖先萬萬歲!》(動畫都沒有幾個人看過)等等都幾乎不得善終。能被拒絕到這種程度,大概不上癮都很難了。
說起來押井守確實是有點生不逢世的感覺,先不提與宮峻駿「既生瑜何生亮」的情結,他確實是錯生在了一個自己所不想要的世界觀下。也許出生在西方社會中,他的理念更能得以聲張。你可以顯而易見,如果他出生於西方,《矩陣》(The Matrix)可能就只能算作是《阿瓦隆》(Avalon)的擴展版;而那因為80億日元凍結的《哥魯穆戰記》(G.R.M. THE RECORD OF GARM WAR),一個最初將由詹姆斯·卡梅倫擔當「製作總指揮」、一個故事發生在架空星球上、一個涉及到各種拍攝手段以及新技術甚至可以說「結合了所有類型的映像技術」的影像企劃——看著像不像是另一個版本的《化身》(Avatar)!如今詹姆斯·卡梅倫劃時代的3D電影《化身》中的理念有多少本可能進入押井守這個被凍結的企劃中?但即便現在把《哥魯穆戰記》拍出來了又能怎樣?也改變不了成為諸如《阿瓦隆》那樣的「二世」命運。
《Animage》當年資助並宣傳了不少年輕有為的新人動畫監督,押井守和宮崎駿就是其中之一,而吉卜力就是行使這種功能的一個最主要途徑。因此,除了宮崎駿和高畑勲這兩個吉卜力的創始人以外,畢竟成立時還是在東家德間書店的名頭下,最早受邀參與吉卜力的押井守理論上也算是吉卜力的創始人之一,只不過因為與宮崎駿的創作理念一再相佐而雙方都互不退讓,在討論爭吵像打架的情況下,押井守最後也就徹底對吉卜力死心了。而此後的吉卜力也就成了一個人的吉卜力——吉卜力是個集權專政,它不像STUDIO 4℃那樣的動畫自由人的無政府主義國度,也不像Sunrise那樣包容到催生Bones,Production I.G催生Xebec和P.A.Works——這點就算是鈴木敏夫也無能為力。
押井守曾有過這樣的比喻:吉卜力是克里姆林宮,宮崎駿是黨魁,而鈴木敏夫則是KGB頭目。押井守用這樣一個控制癖欲(Control Freak)的比喻精確地宣洩了自己的怨念:他表達了自己如何被華麗的克里姆林宮吸引,如何被像極了星探的KGB頭目以靈敏嗅覺找到他這樣的天才,又如何被專制獨裁的黨魁爆頭槍斃。
在經歷了六十年代安保運動的失敗、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這段事業上的肆意妄為、以及八十年代中期事業上的挫折這樣大起大落的人生之後,押井守開始更加執意於尋找「存在感」。人與機器人,現實與虛幻(夢),戰爭與和平,正義與邪惡這樣等等的對立主題愈加頻繁地出現在他的作品中;而宮崎駿則仍然堅持著自己對夢想實現、環保、人生和生存的看法,彷彿從未改變過觀點。我們沒有必要去比較他們表達的主題有多少是重合的,但相互懷著恨意的人,有時其實就是最為相似的——
押井守說:「我們總是會過於關注人類,連動畫也不例外。事實上當兩個人在交談的時候,鳥兒可能正飛過他們上空,魚兒正在池塘遊動,而低頭時你會發現一隻狗正望著你。就我而言,動物之眼總是縈繞在我的心頭。」
宮崎駿說:「當我談及傳統的時候,指的不是那些廟宇——它們反正也是從中國來的,我在我的作品中試圖努力捕捉的元素都是些與生俱來的日本感覺。」
押井守說:「我熱愛把電影裡的世界製作得儘可能的細節化。我熱衷尋找最佳的點——比如一個瓶子標籤的背後,看起來就好像你透過玻璃往外看一樣,我猜,那非常非常日本化。我想讓人們不停的回去看電影,好找到他們第一次看的時候沒注意到的東西。」
宮崎駿說;「在開始拍片前,我並沒有一個已完成的故事……當我開始繪畫時,故事才跟著展開。我們從不知道,我們的故事會走向何方,我們只是一邊製作電影一邊編故事。這是製作動畫影片的一種危險方式,但我喜歡它,因為它可以讓作品變得卓爾不群。」
押井守說:「在我拍自己的第一部電影時,對於一個監督必須做什麼早已有一種固定的觀念,那就是監督要努力娛樂觀眾,要拍娛樂電影——但即使你所做的確實是為了娛樂觀眾,也應該明白這對拍電影而言其實並不是絕對的。」
宮崎說:「有一個內部的秩序,就是故事本身的需要,它可以把我帶向結局……不是我製作了影片,而是影片自己完成的,我沒有選擇,必須服從。」
押井守說:「你不能強求觀眾理解,他們不需要理解,因為那樣也許會激怒他們;反之,如果你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做,如果你能充分地表達自己,這樣觀眾即使並不理解你所做的,他們也能從中得到某種享受。你不需要弄懂一部電影,只要它能讓你有所感觸就行了。」
宮崎駿說:「別想得太深刻也別想得太膚淺,這一切只是娛樂而已」。
押井守說:「吉卜力培育了一種只有吉卜力才能培育出來的動畫師,他們的工作人員水準真的很高,從動畫設計到原畫都是。但如果你問我他們的做法完全正確嗎?我認為他們應該立刻被解散。我想如果那些在吉卜力裡面長大的人們能走出去看看,這應該會更有意義些。對一種創造性的工作來說,無政府狀態至少比權威下自由要好多了。 」
宮崎駿說:「我的片子最好一年內不要看兩遍,因為孩子們把太多時間花在電影電視上不是好事,這會讓他們忽略現實世界。」
押井守說:「如果有1萬個人,每個人都看了10遍電影,對我來說,比100萬個只看了一遍的人要更讓我開心。我拍電影不是給一般大眾看的,我的電影面對的是核心的一群fans,我希望電影會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成功了,那麼我就很高興。」
宮崎駿說:「我希望再活30年。我想看到大海淹沒東京,NTV的電視塔成為孤島。我想看到曼哈頓成為水下之城……我對這一切感到興奮。金錢和慾望,所有這一切將會走向崩潰,所有這一切將被綠色的雜草接管。」
押井守說:「人類不懂得珍惜和平。只要有人類存在,戰爭就永遠不會消失。我們無法長久地維持一種和平的狀態,我認為這與人性有關。很不幸,我們無法將天性中的某些東西消除,也無法掙脫它的束縛。」
……
我可以例舉更多這樣摘錄於不同時期面對不同人時兩人所闡述的觀點,沒必要,窺豹一斑,我們可以看到,即便並非一個字一個字對上,他們的思想都是承接延續著的,除卻某些意義上的發展傾向於自己認同會發生的那一面,有時他們的觀點甚至是一致的。
甚至在於押井守成名後的那種勝氣凌人的自信都與宮崎駿來得越來越像了——
宮崎駿會在電影節上表示:「從現場你們就可以看出來,歐洲人非常喜歡我講故事的方式。」
押井守則會表示:「不管怎麼說,我敢肯定我的作品將在奧斯卡獎提名方面會大有斬獲,因為美國人從來沒看到過類似的作品。」
我想即便他們存在共同點,有著許多共同的看法,他們也是會竭力否認存在某種親近感的。面對年少輕狂的世界,倚老賣老的情況也是在所難免。他們都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孩子氣的倚老賣老,先天的,或是後天的。這種孩子氣可以讓押井守在《殺手》(Killers,2003)中按排鈴木敏夫一槍爆頭,也可以安排該吉卜力社長在《立食師列傳》(立喰師列伝,2006)中被碗砸死;對此般對吉卜力的怨念宣洩,宮崎駿可能會一語蔽之:「不明白他在講什麼」。
如此相近的他們又同時有著左翼份子的背景。之前已經提到了宮崎駿的工會背景,而押井守則表明:「說實話沒想進大學,因為當時並不喜歡學習,預計高中三年級時候會有戰爭,結果並沒有發生。人生的計劃就這樣亂了,沒辦法就進了大學,想一邊打發著時間慢慢考慮。什麼時候結束學業,退學也行。」押井守的母校是東京學藝大學。在學生運動中受挫,漫無目的進入大學的青年押井遇到的是電影。加入電影研究會,一年看了近千部電影,變得熱衷起來開始自己拍攝電影。電影夢最後未成,在換了好幾份工作後,押井守才在26歲(1977年)時進入了動畫製作公司。
高増明在「關於中國與日本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的變革」的討論會上總結道:「宮崎的思想是古典左翼思想,相信未來,為了正義而戰是他的思想體現;與之相比,押井的思想則是在左翼運動中遭受了挫折,從而不相信任何信仰。走的是新左翼思想的路線。」
這就是為什麼宮崎駿會說:「好的東西就是好,管他什麼邏輯!」
這也是為什麼押井守會有這樣的想法:「任何宗教都是從悲觀開始到樂觀結束,我承認我是個宗教迷,但是我不信仰任何特定的宗教。」
宮崎駿認為動畫這種手段本來就是為孩子而生的,不會偏離開這一點。宮崎駿用感情豐富的主角來感動觀眾,而押井守的做法與此大不同,世界觀第一位,他會客觀審視登場人物而進行創作,這在日本甚至世界範圍里都是很少有的。在製作方面,徹底的實現著無表情的表演,使本來運動的物體實現了靜止的運動,這樣比較能抓住年輕人的心態。這就和為孩子們拍的動畫有著很大不同,可能有時甚至不招成年人喜歡。
為理念為實現一己之思量往往都是會做出許多反其道而行的事情來的,也許為了讓他人喜歡自己就多少要做出一些不招人喜歡的事情來,這是人的虛偽性所決定的。因此,一向認為文如其人的人可能要失望了。一向認為文如其人或者說動畫如其人的人未必會有其中是否真的存在科學性的概念,因為創作者總比作品來得更加矛盾、不可調和,面對作品,觀眾彷彿有種錯覺可以有條不穩地把它整理出個大概形狀,但面對創作者,你面對的其實就是一個幕後的神,作品永遠只是一種理想之物、一種創作技法的總結,它只是創作者勸服自己、迫使自己承認的那一面,或者僅是和製作方人事上的妥協。觀眾看到的永遠只是自己想了解的形狀,也許只是俯瞰看到了一個正方體的一個面而沒看到剩下的五個面,也因此,對於觀眾來說,看到的永遠也只有侷限無疑。
由此我們大概要有這樣的思考:觀眾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不重要的。但有一點,一個作品一經形成,它就具有了某種神秘性。所以,我並不是讓大家小看他人的作品,反而要足夠的重視,因為,我們所重視的作品是創作者重視的世界的產物。
押井守說:「我小看了這個世界呢,以為做喜歡的事情就可以了,以為都會順利進行下去的,就算做了再怎麼不明意義的作品,也沒有關係,作為監督,我不會失職。說是『如何地、往何處前進』卻變成了『前進前進!』的狀態,這就是犯大錯了……」
要足夠重視,作為世界一部份的作品,不然就會犯大錯。
而這種成為世界一部份的不確定的神秘性正是給創作者帶來的最大快感。
雖然種種愉悅會讓他們盲目的樂觀,以致即便去年冀望極大的他們在水城最終都只撈了點小獎——押井守的《空中殺手》獲得了「數字未來電影影展獎」(Future Film Festival Digital Award),而宮崎駿的《懸崖上的金魚姬》則是「數字未來電影影展特別獎」(Future Film Festival Digital Award Special Mention)以及表彰電影美術表現的「MR基金獎」(Mimmo Rotella Foundation Award)——他們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創作中將還是會維持樂不思蜀的現狀吧。
「每次結束的時候我確實精疲力盡,《攻殼機動隊》結束的時候我也想過『再也不拍動畫了』,《攻殼機動隊2:無垢》(Innocence)之後也想過不幹了,這樣的事情做不下去了,確實是老了,確實頭髮是少了,肝臟也變糟了,因為切實感覺到這些。『拼了命也要工作』,這麼說,也確實是這麼做的。」押井守雖然如是說,但他在未來兩年內仍有包括2部寫實電影在內的3部劇場電影企劃,以及微軟遊戲光暈7部動畫短片集《光暈傳奇》(Halo Legends)其中1部短片的監修工作等等;而每一次推出「卸幕之作」但又耐不住寂寞風生水起的宮崎駿則打算70歲以後再考慮下一部動畫電影——我們只能安靜等待著期望他能帶來一場真正的謝幕高潮。也許押井守仍然會掙扎幾下,帶來新鮮的視聽,但也許宮崎駿彷彿已經沒有希望重現過去的榮耀了,每一次想收手時又想再搏一下,但並不是每一次都能搏出最棒的東西來的。另一方面,吉卜力也進入了一個老年期,近期官方高調宣佈2010年的吉卜力動畫電影將啟用監督新人的原因就是基於這個的衰老恐慌。
宮崎駿坦誠近作《懸崖上的金魚姬》的故事有點類似於安徒生童話,但他又重重地申明白己並不喜歡《海的女兒》,他有自己的藉口來創作這部作品:「已經到達了極限,無法再創造出更新的畫面和故事。」
是年押井守則在威尼斯稱宮崎駿和北野武拍的是「老人電影」,但這並非挑戰權威或挑畔,倒是近於挑逗,也許又是某種事實,《千與千尋的神隱》是宮崎駿不斷低幼化的開始——當然離結束也沒幾年了;另一方面,正像押井在《Animage》中「與宮崎駿對《機動警察 劇場2》的對談」中這麼說過的:「現在不少人都說『如今已經沒有拍一部好電影的視點了』,而我過去就說過是,『沒有拍一部好電影的價值觀了。』」
個人價值觀過度篩選形成的內耗才造成了如今這種局面,也許十年後,押井守會嘆一口氣說「唉,我終於也跟宮崎駿一樣有名了」——或者更有名,然後他發現自己也成師太開始拍老人電影了。
從某些方面的展望看,所謂的前輩們其實都不應該是年輕動畫監督們的榜樣,但這也正是他們的優點所在。動畫細節已經做到了偏執的地步,讓人招打的衝動,這便是他們這認真的一輩的其中一個表現,而現在的這一輩多數則是快餐監督。
「與在現場拍攝的寫實電影不同,動畫是由人類的妄想而生,但如果妄想脫離了現實,那就只是捏造的美麗空想而已。主人公住在怎樣的房間,在怎樣的地方吃飯,坐著怎樣的車,好好的描繪這一切,我想這是電影的基本。」
現在的監督很現實,就是缺少點妄想,缺少點賦妄想以有形的能力。
除去商業荼毒以外,如今年輕監督們的問題還在於,押井守可能對宮崎駿的作品挺深交的,但對他本人則需商詮——反過來的情況可能還更糟糕一點;但年輕監督們有的幾乎不看別人的動畫,或者說其實現在的監督都不看別人的作品了——商業化帶來的必然後果。另一方面,他們也許已經將像押井守和伊藤和典以及高田明美等人一起邊泡溫泉邊暢談創作(在《機動警察》時,Headgear可以說就是泡溫泉泡出來的)的情調發揚到了極致但也仍然未做出任何驚人的東西來。
在這個遍地菁英,遍地大師和師太的世界,批評別人的作品會引起很大的反感。正像押井守早就意識到的,但他還是忍不住說出口來了。這大概就是聲望這種東西帶來的「勇敢之舉」,每個成功人士不免都會有這樣的情結。
舉個例子,監督御三家宮崎駿、富野由悠季和押井守在談及庵野秀明的《EVA》時分別是這樣的反應——
宮崎駿:「沒有看過。」
富野由悠季:「請允許我不做評論。」
押井守:「我只看了2集左右,沒什麼好說的。不好意思了。」
大師們的「勇敢之舉」好像總是永遠惜字如金;而與此同時,「小師太」庵野秀明對這些大師們也不見得會生出多少像當年押井守對宮崎駿那樣懷帶仰慕之情的不同政見,他們甚至會流露出不屑於觀摩對方作品的情緒——這可謂一切的進步所帶來的怪異現象吧,「惺惺相惜」毫無疑問不是如今主流正統的價值觀取向。
總之,總得來說,可能還是時代變了;後生可畏的庵野秀明對前輩監督御三家的感想幾乎是後者對前者如出一轍的演繹,感情色彩都是一致的,只不過是劇本中的人物換了個罷了——
庵野秀明在採訪中對押井守的評價並不高,他甚至聲稱沒看過《攻殼機動隊》。「《機動警察2》還是不錯的,不過這是因為我認識押井先生,從個人角度這麼認為。」就是這樣的情況。
「宮崎駿做的已經不是動畫而是邦畫,就是無聊的所謂日本電影。」這顯然是庵野秀明對當年對方對自己畫作指手畫腳的評論「不怎麼樣」、「太糟」、「三腳貓」的回應。
而至於富野和他的高達,庵野秀明則顯得更為尖刻——他在富野手下打過雜,就像像他也在押井和宮崎手下打過雜,他甚至在GAINAX初期因為《王立宇宙軍》陷入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去參加了高畑勛的《螢火蟲之墓》的作畫以貼補家用——提及富野和他的高達,庵野秀明道:「這種動畫對於那些想自己創作卻又做不出來的人應該很適合吧。」
你完全不會從中讀到任何「我從中學到了什麼」的語氣,這可能就是所謂的動畫以及製作動畫的人固然存在的孩子氣吧,所以其實也不至於說是交惡,這多半還是因為媒體無聊的比較惹出的是非——押井守和宮崎駿的情況也同樣如此,甚至,難道偶爾你不會有這樣一絲想法:這兩個老傢伙其實不是在調情嗎?
孩子氣的怨念總是會存在的,不止他們,比如被京都動畫以「敝社認為山本寬尚且不夠資格成為一名動畫監督」的理由從《幸運星》撤職斬首的山本寬對權威的不信任感造就的之後《神薙》第4話中的一幕:在宅物店前的隊伍中最後那三位知名大叔赫然在列,他們明顯就是押井守、宮崎駿以及庵野秀明。當然,這甚至都稱不上怨念,排除仰慕致敬的成份外,充其量只能算吐槽罷了。
他們之間的吐槽格局看起來似乎異常糟糕,特別是在經媒體渲染後,但又彷彿是極好的——因為這樣各自動畫的個性自然就能最大程度地凸顯出來了,而重合的部份也會降到最小,由此在不同的方面相同的戰場發揮出自己的力量,形成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創作特色。
受媒體器重並非壞事,誠然如此,相對於那些衣著光鮮的大師們,另外一些大師級人物則同樣是具備天賦和熱情、時時前進著的人,他們更為人所吸引。他們是那一類名聲在外但無比低調的人,他們是那些熟知音律的人,他們無比自信、從容,他們是高畑勛,他們是高橋良輔,他們是19歲的少年……
1984年之所以被稱為「日本動畫大師元年」,那不只是因為那一年有押井守的《福星小子2:Beautiful Dreamer》和宮崎駿的《風之谷》,那一年還上映了一個24歲天才機設小鬼的初監督作品。那就是《超時空要塞:可曾記得愛》(Macross: Do You Remember Love?)——也許稱不上真正的大師之作,但卻仍然是一代人的記憶;這個小鬼就是河森政治(雖然在石黑升之下存在著掛牌的情況)。那之後十年,文章開始時提及的那位在1984年時19歲的少年——現在是一個少年心大叔了,他和河森正治一起拍了部名為為《超時空要塞 外傳》(Macross Plus,1994)的OVA動畫——說到這裡,嚴然已成了另一代人的起點。
他跟押井守一樣,最初都只是個電影青年。相對於動畫,電影語言畢竟是大人的語言,也更加結實。
他的優勢還在於,他不會將自己的感情像宮崎駿那樣萬年不變地灌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他講的不是他自己一個人的故事,他會很平實而又不失幽默地將故事娓娓道來,他是以他的旋律在講所有人的故事。相對而言,押井守和宮崎駿都沒能很好地做到這一點,他們都過於自我中心主義。
這個在1984年時19歲的少年就是後來執導了《賞金獵人》(Cowboy Bebop,1998)的墨鏡男大叔渡邊信一郎(你應該看看CB中Spike的飛船和風之谷中的某飛行器有多像)。
接下來的這個時代必然將屬於這些後1984的少年樣大叔們:渡邊信一郎、梅津泰臣、今敏、湯淺政明、神山健治、中澤一登、谷口悟朗……即便有一天連他們也開始拍「老人電影」了,我們仍然是有希望的。因為,總是會有這樣的一個少年,要嘛少女,在巨大螢幕下接受他人作品的洗禮,從而在邁出影院那一刻——空氣中到處都是被光打亮的夢幻般的塵埃微粒——突然拾起一個陽光下的夢想:
加入這場戰爭,做出比他們更厲害的動畫來!
刊載於《現視研》第2期
漫談|Acgtalk
http://www.acgtalk.com/node/1112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