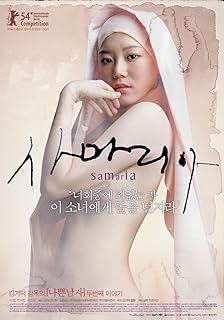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0-04-10 08:31:02
光與影的瞬間,撒瑪利亞重現
[兩個女孩]
電影開篇便呈現給觀眾兩個具有天真無邪靚麗容顏的少女,一個叫餘珍,一個叫在英。她們平淡簡單,如同每天與你我擦身而過仿若無憂無慮的少女們,上網聊天,展露笑顏。
然而,不同的是,她們上網具有強烈的目的性,目的是俘獲嫖客。這便是眾所周知的援助交際了嗎?韓國導演金基德的影片素來都刻意呈現出這冰冷世界浸蘊著的病態和冷酷,這一次他又怎會心平氣和,放過這兩個女孩。
開篇,鏡頭便從電腦螢幕帶出,交談,價錢,地點。電腦攝影頭對準在英燦爛的笑容,MSN上呈現攝影頭的畫面,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則是雙重鏡頭。交談的女孩並非是電腦攝影頭對準的那個,這便製造了一個小小的懸疑。她們,為何要這樣做?
MSN上交談聯繫客源的女孩叫餘珍,在英卻是對準電腦攝影頭綻放燦爛笑容自願出賣肉身的女孩。餘珍用在英的身份聯繫嫖客,餘珍用在英的身份電話通知他們時間、地點,然而,出賣肉體的卻並非餘珍,卻是在英。
為什麼她們會採取這樣一種形式,餘珍為何會存在,又為何要這樣去做?她們不是好朋友嗎?這是導演製造的又一個懸疑。
在英每一次交易後,就把錢全數交予餘珍,餘珍在在英每一次交易時,都是那麼地委屈與憤恨,卻又將所有的錢夾在記事本之中,分文不用。每一次完事後,餘珍幫在英洗澡時,都將自己的痛苦與不滿表露無遺,然而,這一切卻似乎極其合理地繼續存在與發生著。
兩個女孩,做這一切的事情,只為了一次歐洲旅遊。
當我解開這些懸疑後,心中頓時被一種強大的情感所擊中,差一點落下淚來。少年時的友誼和情懷從來都是異常珍貴的,只因它氾濫著極度的執著與完全逃離現實的付出。時間一過,人一成長,一切便灰飛煙滅,不再重來了。
凡塵俗世忠現實的人群是不適宜也看不懂這樣一部影片的。若然人在年少時選擇過如此這般的荒誕,便會明白當中的情深與意重。
[巴蘇米達]
在英心中,援助交際並非是一種罪惡,她將自己想像成為印度聖妓巴蘇米達,固執地認為自己所做的是一件神聖的事,因為自己帶給那些男人真正意義上的快樂。她單純快樂地去享受每一次的交易,單純快樂地去耐心了解傾聽那些男人的煩惱憂慮,並將一切的一切毫無保留地告訴給了餘珍。餘珍對在英是一種超越了友誼的情感,更近似於一種守護式的愛情。她不願意餘珍愛上任何一個有過身體接觸的男人,她要的是一種佔有。佔有在英單純的笑容,佔有在英對自己永恆的依戀,佔有在英的情感世界。
在英從頭到尾始終綻放的單純笑顏,始終令人有慘不忍睹的淒涼感受。她的第一次接客,未穿衣服便逃出生天,餘珍拉著她狂奔逃走,一路上,在英都在笑,她究竟在笑些什麼,究竟與什麼值得那麼好笑的。所發生的這一切,在平常人眼中,不是應該是萬分悽苦的事件嗎?在英卻用永恆的燦爛笑容化解開一切悲楚,餘珍的難過可想而知,在英的笑更令她覺得負債纍纍,苦不堪言。
鏡頭:
兩人在公園奔跑游耍,紅色的楓葉散落四週,鏡頭唯美藝術,而後畫面停頓停留在公園的人形雕塑之上,兩個女孩坐在了淡藍色的雕塑旁邊,整個畫面是靜止的,甚至猶如死水一般,然而兩個人的動作由動至靜,直到與整個大的畫面重合靜止。
不知為何,我尤為地喜歡這一幕,生與死,靜與動,相互制衡,那些充滿宗教意味的雕像,姿態各異地存在著,泛著如同明朗天空般的刺眼淡藍,彷彿象徵著兩個女孩的純潔與不沾惹浮世塵埃的情感。
鏡頭停留在那個被在英隨手丟棄的豬手上面,給了一個特寫。任何人都知道,這種特寫一定會有意味深長的含意,必然與接下來的劇情轉變有什麼關聯,而且大多時候不好的暗示。
在英跳樓的那一瞬間,燦爛的笑容夾雜著緊張與不安,何其慘不忍睹。餘珍背起血如泉湧的在英的時候,我於內心深處徹底地原諒了這個女孩。朋友的自殘,必定令她這一輩子都難逃其咎,即使這其中沒有法律道德的懲戒。
「巴蘇米達」終究是死去了,死後她的面容依然維持在那亘古不變的微笑狀態。
[撒瑪利亞]
餘珍為了在英死前的心願,將戰慄的身軀委身於那個音樂製作人,卻終究未能完成在英的那卑微善良的心願。
「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音樂製作人靈魂在餘珍不顧一切的奉獻下顯得是那麼不堪與渺小。在英終究是一廂情願地做了巴蘇米達,世人並不會感激與懷念。
善—在金基德冷傲的視線下永遠是一種悲哀。
於是,撒瑪利亞重現。
路加福音 [1]10:30-35
聖經故事:一位猶太人從耶路撒冷趕往耶利哥,路上遭遇強盜,被強盜抓住痛打一頓後掠走了財物,路人受傷倒在路邊痛苦地哀號。一位祭司經過受傷路人的身邊,只是看了看揮揮手離去。過了一會兒,一個利未人經過路邊看到傷者,還是不聞不問,自顧自離開。這時一位撒瑪利亞人經過看到,便將傷者救起,馱在驢背上送至一家旅店內,並且留下錢財以支付醫藥費,並說如果不夠兩天後再來付清。
主耶穌說:要像撒瑪利亞人一般愛你的鄰人。
餘珍選擇做撒瑪利亞,我想那並不僅僅是一般影評中所述的救贖情懷。她更多地是希望用自己與在英做最後的溝通與交流,她刻意保持的微笑,她對自己身體的出賣,她歸還的錢財。一切的行為,她都是希望在英能夠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同時,她通過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從那些男人身上最後一次感知在英。
救贖那些人的靈魂,令他們醒覺,只是餘珍所做之事的附加戰利品罷了。這並非出自餘珍的目的。但事實上卻是因為餘珍這樣的做法,無意中成就了撒瑪利亞的傳說,拯救了世人庸俗的靈魂。
[父親]
在這個單親家庭中,父親對女兒的愛,更多地是暗示著一種絕對性的佔有。父親的耐心與執著造就了故事繼續發展的悲哀基調。
餘珍的父親是一位警官,當他發現餘珍所做之事的時候,並非採取與其溝通交流的方式,悲憤得咬牙切齒、怒目圓瞪,卻只是一味地懲戒那些嫖客。
因為他始終是無法接受女兒不潔的這樣一個事實。一次、兩次、最後一次終於是忍無可忍地手刃了最後那個嫖客。
原本暴力與血腥的場面,在金基德的戲弄下,鏡頭始終空是於陽光燦爛,風輕樹搖的場景中起始而後終結的。
餘珍對父親的情感始終停留在尊敬與愛戴的層面之上,她自然是無法感知父親的反常與壓抑著的強大情感憤怒。普天之下的父親都是不善言辭的,這個亦不例外,他無法表達更不願說破女兒身上所發生的一切。一旦說破,他知道,餘珍也就不再是他心目中那個幼稚惹憐的孩童了。
[索納塔]
金基德的影片看過幾部,總是會留有一些晦澀難解的片段,《漂流浴室》中啞女在船中漂流的最後一幕便是如此。
撒瑪利亞也不例外。
1、車卡於泥坑,餘珍下車搬石,父親看見後面上浮現的那個難解的笑容。
2、半夜,父親看見餘珍在窗外哭泣。
3、兩個截然不同的結局—生與死。
對1的解讀:
解讀一:按照正常人的思維邏輯分析: 父親身心俱損,累得坐於車上。餘珍搬石,意味著她的獨立與成長,她開始懂事。父親看見餘珍的成長,感到欣慰,放心自己即將離去。臉上浮現告別的微笑,這意味著一種心理的告別。這個告別預兆了電影第二個結局—生。
解讀二:導演金基德有著跟庫布里克一樣的殘忍視角,若照他固有的拍攝手法分析:父親已經感到累了,他再也承受不住餘珍帶來的痛苦與壓力了。於是,他選擇靜靜地躺在那裡,並不理會餘珍。餘珍搬石,意味著她開始擺脫父親的保護與束縛,開始自我找尋「出路」。父親震驚於餘珍的獨立,內心感到強烈的失落,明白由始至終,女兒其實是不需要自己的幫助的,她已經可以自己處理和解決那原本屬於她自己的秘密。父親感到自己的付出完全是沒有一絲價值與意義的,於是便笑了,他明白到女兒再也不是那個每天早上需要用CD音樂叫起床賴皮不肯考試的孩子了。餘珍不再需要自己,這對父親來說意味著另一種心理的告別。這個告別預兆的是電影第一個結局—死。
對2的解讀:
餘珍深夜在窗外哭泣,鏡頭從父親的視角帶過去,藉助攝影機的眼睛代替父親的眼睛,拍攝的是餘珍抽泣的背影。父親並未出去安慰,這是很奇怪而且不合邏輯的一種選擇。但是這種選擇是存在的,原因就是父親對餘珍的感情已經深厚到不敢過去觸摸與問候的地步了,這是種很複雜的情緒。因為太愛了反而不敢去接近,輕輕的觸碰都只怕會令自己五臟俱焚。
對3的解讀:
我個人只認同結局一,也就是於黑白色類似夢境的拍攝手法下,父親將女兒殺死後將其埋於沙土之中,小心翼翼地為女兒戴上耳機,放好CD。電影就是電影,我不希望涉及真正的人生,戲劇化的結尾更能舒緩觀眾的情緒,更能令觀眾感悟與享受。
結局二其實暗含了現實生活的一種延續,餘珍終將會成長。類似於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的照相本性論:「電影的本性是物質現實的復原。電影按其本質來說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樣,跟我們周圍世界有種顯而易見的親近性,當影片記錄和揭示物質現即時,它才成為名符其實的影片。」我不同意這個觀點,因為我根本上否定電影與物質現實是種復原關係,我認為是一種再次製造。敘事方式可以遵循電影眼睛的理論,但是電影如何構想並非是種單純的發現
,而是需要一種文學意義上的美化或醜化的加工。否則所有的影片不過就是紀錄片的挑剔形式罷了。這樣會完全否決了娛樂性的存在。
總結,金基德是個美學大師,因此他的拍攝手法永遠都令人感受到鏡頭取景的清麗、安靜與唯美。沒有紀錄片中的嘈雜浮躁,彷彿遠離了浮世喧囂,沒有一般商業片的宏大場面,也沒有一般文藝片中貫穿全場的特寫鏡頭。加上猶如天籟的音樂,簡單不多的對白,豐富的人物刻畫,對人內心深處慾望恰到好處的把握,這樣的影片想不得獎都很難。
[1] 引自聖經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