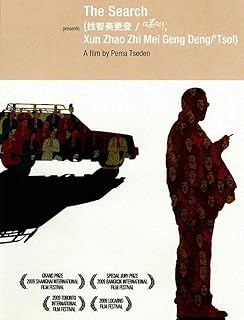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0-09-20 15:11:13
若再見面,就給你看我的臉
若再見面,就給你看我的臉
——關於萬瑪才旦影片《尋找智美更登》
張泠(黃小邪)
去國日久,看中文電影(尤其獨立電影)沒那麼迅捷,故,2008年夏天,在北京初見萬瑪才旦時,尚未看過他的作品。他本人的謙遜平和,在城市的喧囂中令我詫異,如波瀾洶湧的湖畔,一塊沉默的頑石,被水波洗磨得略圓潤和蒼白,卻自巋然不動。待看完他送的DVD,愈生欽敬。在中國電影漫天商業巨製狂潮中,他的作品不嗔不躁,淡定自如。那定力如神秘磁場,引人浸入他以影像和聲音構築的寧靜世界——劇情長片《靜靜的嘛呢石》和《尋找智美更登》。冥想,找尋,各種元素角力,協調,融匯:藏族傳統,宗教,民間文化,精神潔淨,消費主義,現代科技,利己觀念……萬瑪沒有刻意戲劇化這些矛盾,這本是人們日常生活中須應對的問題。他的作品,只平靜展示,巧妙交織,最終總有種慈悲心,篤信誠實和寬容,柔和而堅忍。這或者來自他的信仰,或者來自一種與目前主流社會庸俗化、犬儒主義傾向相左的理想主義。自然,二者密切相關。
如果說如兩片片名所暗示,《靜靜的嘛呢石》講述的環境和氣氛相對封閉、靜止和安寧,《尋找智美更登》則充滿動感和變化,既是身體穿越空間的旅途,也是精神探尋的經過。一部韻味獨特的內心體驗式「公路電影」,與此類型的美國鼻祖(如1967年的《邦妮與克萊德》,1969年的《逍遙騎士》,或1991年的《塞爾瑪與露易絲》)相比,更溫和內斂,去戲劇化,表面看來,目的性更為清晰(實則「尋找智美更登」這個曖昧的心靈象徵只是敘事展開的藉口):老闆,司機,導演,攝影師,幪面姑娘卓貝,同車五人,一路探尋民間藏戲演出狀況,尋找可在電影中扮演智美更登的最佳人選。在這個片斷式的新式「西遊記」中,作為結果的「經書」無關緊要,過程中「偶然」相遇的人和事的細節促發的迷惘、感傷和變化,徐徐展開,如片中一望無垠的荒原;又層層疊疊,如高原中縱橫的溝壑。多重講述者和敘事線索、風景、聲音、面容,織就質地豐富的物質性。
智美更登,藏傳佛教中釋迦牟尼的化身,其故事源於印度,多出自《釋迦牟尼本生傳》。智美更登在同名藏戲中為印度王子,慈心濟貧,施捨了自己的妻子曼達桑姆、三個孩子,及自己的眼睛。《智美更登》為八大藏戲之一,民間曾歷演不衰,近年每況愈下。很多村子的戲服、道具,被丟棄角落,蒙滿灰塵。因年輕人多被電視或其他娛樂方式吸引,道德觀念也受商業社會衝擊。藏族老人看《智美更登》常感動得唏噓,並樂於仿其善行,年輕人則不以為然:片中導演向一位憤世嫉俗的藏族歌手陳述智美更登的核心精神為「慈悲,關懷,寬容和愛」,後者,一位藏學專業畢業的大學生的反應是,嗤之以鼻。
影片避免做武斷的道德評判,也並未讓人物跳出來大聲疾呼,因為在維護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尊重和信任它的觀眾的主體性和思考能力,如同保持一個尊重的距離,去拍攝那些娓娓道來的人物。儘管如此,對傳統道德、文化的丟棄和漠視,在今日中國,幾乎隨處可見,因了藏區的地域邊緣性,及民族和宗教的獨特性,這種危機感,影片表達得含蓄克制,在觀者眼中,卻無法不被放大。在當代掠奪式的殘忍叢林中,「智美更登」這個理想化的象徵,可還有意義和感召力?而這個像徵終究是變動不居的,如何界定,如何修訂,片中不斷探尋的導演,和片外一同行路的觀眾,須自行琢磨。
《尋找智美更登》中的多重敘事,時而平行,時而交錯,時而被暫時擱置,製造輕微的懸念感。亦是不同層面、媒介和時態的線索交織。片中老闆的回憶式口頭講述(oral storytelling)的愛情故事,為過去時,並將因影像而永恆化;以影像講述的卓貝與前男友的故事,則徘徊在過去、現在與將來之間。而「智美更登」傳說所象徵的抽象的、普世的敘事,與片中老闆、卓貝及導演的個人故事(導演屢次接電話處理家事,但影片刻意隱去其對話,使之神秘化)構成不同層次。
影片關於一個小攝製組去採風,沿途所見,既有民族志影像(ethnographic films)痕跡,又有強烈的「自我映照」(self-reflexivity)意識。藏戲《智美更登》和「唐僧喇嘛」的故事出現在《靜靜的嘛呢石》和《尋找智美更登》中,使得同一導演的不同作品中有互本文的指涉。而影片不時跳切到更大景別或轉換景別,展示一個攝影機正在拍攝,導演站在一旁,不斷提醒觀者自封閉敘事中解脫出來,清醒意識這是通過另一個攝影機的眼睛的觀看,及電影的人為介入和虛構本質。
《尋找智美更登》亦有「偽紀錄片」(mocumentary)色彩,刻意模糊虛構與寫實的界限(近年華語電影中有多部此類作品,如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和鈕承澤的《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看似「偶遇」的人或物,在整個敘事結構中都是精心設計的,而拍攝的場景本身(尤其訪談和表演段落),則以連續的長鏡頭保持了紀錄片拍攝中的某些自發性和原生性。萬瑪才旦在訪談中提及《尋找智美更登》中有30%是真實素材,70%為虛構。老闆在路上講述他的愛情故事時,基本上都是一條拍就。片中演員多為非職業演員,他們身上的素樸質感,渾然天成,專業演員無法還原——自然也有弊處,萬瑪才旦多次提及,有些非職業演員因經驗不足和緊張使得拍攝不甚順利。那位施捨了妻子的「活智美更登」 嘎洛大叔被從後面拍攝,隔開距離,觀眾仍可聽出他音調的不自然,如在背誦)。無論如何,這種質感與廣袤粗獷的高原風景、及固定機位長鏡頭和大景別相得益彰。
此處的高原地貌,有些蒼黃枯槁,完全剝除《靜靜的嘛呢石》中尚存的視覺奇觀性和色彩飽和度。其一與膠片或數字介質還原色調和感光度程度不同有關,其二也是為影片立意、整體視聽風格之統一而刻意為之。攝製組主要成員為藏族人,影片在青海安多藏區拍攝。他們構築的視聽空間並非被美化、理想化和神秘化的明信片式的平面藏區,而儘量還原其日常性、普通性和立體性。他們既是局內人,深諳當地風土民俗,理解當地人生存哲學,在此環境中泰然自若;又因遠離故土多年、社會階層區分及手中的攝影機,而有局外人的探究目光和清醒態度。體現在鏡頭語言中,即親昵又疏離,即立體又平面,如此之遠,又如此之近。
這涉及到影片中的空間。車內是封閉的、侷限的行進空間,攝影機只能迫近人物,拍特寫和中近景。而老闆和女孩卓貝的影像偶爾同時出現司機的後視鏡中,暗示兩人各自的愛情故事儘管在不同時空,卻在此並置而生微妙聯繫。窗外是遠景中的廣袤荒野,隔著遙遠距離,形成對比。攝影機也不時置身荒原,遠遠注視他們乘坐的車飛馳而過;它也在某個時刻,隔著玻璃,捕捉到女孩眼角一點淚光(細節之微,很容易被不細心的觀者忽略)。在與村人交往的空間中,牆、院落、門窗等都成為切割畫面的線條,也有助構成有錯落有致多層空間(前景,後景)的深焦鏡頭,攝影機往往固定,多為全景長鏡頭,造成一種戲劇舞台感(片中的確大量出現整段的歌舞表演及小喇嘛的「才藝表演」)。在很多場合角度略高,不時跳接至一個更大景別,或另一角度的畫面,維持這一場景時間、空間、聲畫的完整性和統一性,及給觀者「與攝影機同時注視和經歷」的體驗。
影片也深諳「留白」深意,無論在敘事和取景層面:女孩始終未示的面容,導演不可聽的家事,及老闆遙望的、有他昔日戀人的高高院落。而片中多個場景的構圖中,人物在畫框邊緣,畫面中間留出一大片空白,且將立體空間作平面繪畫式呈現。尤其卓貝與前男友在學校操場見面時,中學生們課間操跳鍋莊,在畫面左邊緣形成視覺興趣點;攝製組與車在畫面右側,卓貝與前男友在畫面上端,遠遠的角落。聲軌中只有節奏歡快的音樂,觀眾繫心的人物對話全被淹沒。依照對電影語法的傳統理解,此處無一視覺和聲音主體,多重元素在爭奪觀眾的視聽注意力。而動靜之間,虛實變幻,盡在不言中。這種構圖和場面調度,突出並非縱深感,而是一種散點透視的平面感,如影片攝影師松太加所言,他們參考了一些藏族傳統畫面中的平面性美學,而非追求色彩、光影和空間透視感。
這種散點透視的平面感和「多音文化」,也體現在聲音美學中。音軌中幾乎始終播放藏族音樂,且多為有聲源音樂:來自車中的CD機,或藏戲團和「熱貢歌舞大世界」中的現場表演。音樂的音量和質感通常不隨鏡頭景別變化:鏡頭可以是大遠景,而聲音(音樂和人聲)可以是「特寫」,清晰如在耳畔;人物明明在畫面中對話,他們的聲音卻不可聞……某種程度上「非寫實」的聲音美學與高度寫實的視像美學形成有趣的對比和張力。而幾乎無處不在的畫外聲音(包括音樂、講述者老闆的畫外音等),拓展一個豐富的畫太空間,使得畫面空間如被聲音包裹——有些電影聲音研究學者會將這種具包裹感的音景喻為母體的子宮。
影片中某處細節:司機問路,問牧羊姑娘姓名,姑娘說:「若再見面就告訴你。」相信神秘力量,有緣人定再相見。卓貝還了頭巾露了真容而走,卻被片中人物和片外觀眾錯過,害得老闆感慨:「看一個美女的芳容真難啊。」卓貝也許會以畫外音對老闆和觀眾應對一句:「若再見面,就給你看我的臉。」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