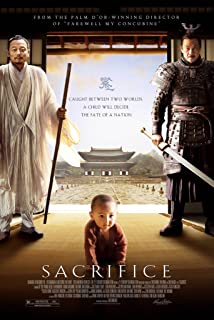2010-12-04 08:23:27
《趙氏孤兒》:悲劇與杯具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趙氏孤兒》這樣的題材,彷彿就是等待陳凱歌來拍的。陳凱歌的古典戲劇修養和電影才華,以及他深入古典所挖掘出的人性之複雜,都使他的電影在戲劇的古典式張力的同時擁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形而上的追求,也讓他本身具有了一種菁英氣質,這種氣質在中國大陸比較難能可貴,這也是他的《荊軻刺秦王》在日本備受推崇的原因,他在《刺秦》中表現出的卓越的才華讓日本人依稀遙想起電影天皇黑澤明。
所以,《趙氏孤兒》這樣經典的悲劇,這部被王國維稱為可媲美莎翁悲劇的中國古典悲劇,與陳凱歌的金風玉露一相逢,就是一段可以預想的華章。在《無極》和《梅蘭芳》的迷失之後,這是陳凱歌最有希望的一次回馬槍,拿出壓箱底的絕技,來一次華麗麗的回歸,這個回歸,更多的是陳凱歌電影范兒的回歸,都希望他像《霸王別姬》和《荊軻刺秦王》一樣,在高雅與通俗之間遊刃有餘,借世俗通俗化很高的故事外殼來一次深沉有力的自我表達。
在這部《趙氏孤兒》中,陳凱歌不願重複種種以現代方式詮釋《趙氏孤兒》的方式,比如林兆華的話劇《趙氏孤兒》。其實1980年代以來,伴隨著種種西方現代文藝思潮的湧入,大陸的社會的現代化反思,總是繞不開一個非常核心的話題:對個體存在的反思,這來源於西方文藝復興之後對個體的人文關懷,被幾千年的專制集權統治而忽略個體存在的中國文化在個體反思方面也熱衷不已,林兆華話劇版的《趙氏孤兒》便是如此。紀君祥的元雜劇《趙氏孤兒大報仇》是在元朝統治者極權下對漢唐文明中忠義精神的深切呼噢,但這個流傳數百年的經典話劇,今人看來難免頭重腳輕,趙家被屠岸賈滅門之仇何等沉重,最後趙氏孤兒長到十五歲被程嬰告知血海深仇的大仇人,立馬揮刀復仇。趙氏孤兒就是一個為了復仇而長大的工具,程嬰就是為了復仇的工具而存在的工具,前半部份的一個個血性忠義之士的捨命相救,是讓我比較感動的地方,但最後一切都如此簡單,總覺得虎頭蛇尾。所以很多現代版的《趙氏孤兒》的文藝作品比如林兆華版中,就把關注點放在了趙氏孤兒這個人物本身,他對自身存在意義的認識,他的成長與人格的形成。
陳凱歌也想探討這個悲劇復仇故事的核心,也想關注當事人的個體存在,用他的理解方式,但他選擇的核心人物是程嬰,這裡的程嬰不是趙家門客,就摒棄了元雜劇中的忠義情懷;而被歷史洪流捲入一場世仇恩怨之後,他以自己的孩子替了趙氏孤兒,接下來他要進行一場復仇。這是他本來無意承擔什麼重大責任,卻遭遇家破人亡的人生重大變故之後,產生的強烈的復仇心理,這個復仇的成本是他的整個後半生,他要用最狠的復仇「不是殺人,而是殺心」,自己帶著趙氏孤兒投大仇人屠岸賈門下,讓趙氏孤兒做屠義子,讓屠對趙氏孤兒視如己出,待趙氏孤兒長大,告訴屠岸賈他最疼愛的義子就是他當年最想殺掉的嬰兒。
其實不管是怎樣的解讀,前半部份的戲劇張力都是先天性存在的,從趙家被屠岸賈滅門到趙氏孤兒死裡逃生,這裡陳凱歌把握得不失多少水準,但不得不說的是,關鍵的戲裡范冰冰和黃曉明的表演讓緊繃的弦鬆懈了不少,戲份如同客串的張豐毅所演的公孫杵臼的表演也是馬馬虎虎,所以基本還是靠葛優和王學圻的表演撐出了前面血腥滅門戲的強大張力。提彌明等幾個忠肝義膽之士不惜以血肉之軀救主的戲,讓人對後面的精彩提高了預期。
這個時候你以為好戲剛剛開始,其實很遺憾,好戲已經到此為止了。
後面一大半,程嬰的復仇過程冗長而乏味,導演對把敘事的重心放在了程嬰身上,豈不知在故事的主線上,程嬰存在的意義還是要依附於趙氏孤兒的存在,導演對趙氏孤兒成長也做了很多鋪墊,但趙氏孤兒的成長過程中在精神上更多受屠岸賈的影響,從程嬰到趙氏孤兒再到屠岸賈,這就需要一個程嬰的堅忍和孤注一擲,一個遺孤的成長與糾結,一個權臣屠岸賈的複雜和難以捉摸,但導演偏偏就放過了屠岸賈一馬,或者放過了王學圻在後面表演上的複雜性,在後半段這個關鍵人物的塑造上太沉溺於一些小打小鬧的淺層人物關係,屠岸賈權傾朝野,手裡握著幾十條命案,又要面對一個茁壯成長的孩子,這不需要用宮廷或者政治鬥爭來襯托,但起碼得有更廣闊的格局來塑造這個人物的複雜性,怎麼可能只是一個大人物似的父親形象?到了這裡,劇情的張力已經蕩然無存,所謂的血海深仇簡直成了說說而已,所以在最後的劇情高潮的時候,由於缺乏足夠的鋪墊,實在缺乏說服力。
所以你在一場千古大血案之後,非常詫異地發現影片轉換成了一個單親家庭教育片,或者三個男人在對孩子教育問題上的分歧與糾結,是可忍,腐不可忍啊。程嬰白天和屠岸賈像夫妻,在對孩子的教育方式上分歧很大,晚上和韓厥像情人幽會,黃曉明那曖昧的眼神的笑容讓他的刀疤成了一種殘缺之美,當觀眾對前面的悲劇感慢慢淡忘了之後,導演再強迫孩子突然接受了復仇的責任,對前日還徹夜守候的義父拔刀相向,經典的悲劇已經蕩然無存,而影片本身,則成了一個大杯具。
而這個電影,在《無極》和《梅蘭芳》之後的出現,還顯示了陳凱歌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那種精神貴族架子的慢慢放下,影片的後半部份,繁瑣細微卻毫無意義的家長里短與前面的古典悲劇感是多麼不相稱,在開了一個還算華貴的開場戲之後,突然轉入了很草根的絮絮叨叨,讓我感到好像看到一個衣著華美的貴族不顧身份地蹲下,不惜衣袍掃地,只為了找自己昂貴眼鏡的鏡片,因為沒有了這鏡片,他實在看不清了。然而到最後,鏡片沒有找到,他那份尊貴也早已經斯文掃地了。其實在《無極》的時候,鏡片雖然掉了,那份尊貴感還是在的。
影片開頭的氣質其實很陳凱歌,英武超群的趙朔將軍攜美艷的夫人華蓋之下招搖過市,晉國宮廷上的堂堂氣象,是應了華麗而宏大的敘事派頭,影片的人物造型也相當漂亮,尤其是戎裝造型,屠岸賈、趙朔等人的戎裝盔甲色調和款式都精美尊貴,好久沒有在大螢幕上看到這麼漂亮的古裝戎裝造型了。人物對白雖然都很現代口語化,但陳凱歌讓演員演出了很古典莊重的感覺,而這些在後面也都慢慢越發少見了。
拼音輸入法的識別系統,偶爾之間把「悲劇」打成了「杯具」,居然流行起來,「杯具」雖然依然是悲劇之意,但總會有戲謔、調侃和某種對悲劇的無奈。而我們的精神貴族陳凱歌,是怎麼樣的輸入失誤,將一個古典的經典悲劇,擺弄成了自己的杯具呢?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