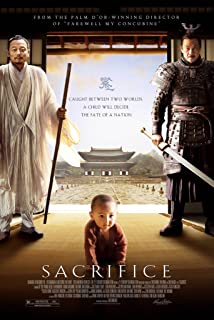2010-12-05 09:06:45
《趙氏孤兒》的不治之症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期待陳凱歌的電影也許是期待自己能夠再寫一篇影評。
這種期待的轉化無異是一種很抽象的移情。
中國電影在產業化的高歌猛進中,把馮氏「美學」的市場泡沫越吹越大,這種奇怪的騷動,讓本來優越感不強的馮小剛已經霸氣十足見誰滅誰了。私下來以為,如果拋卻票房優越感生髮的虛張聲勢,以馮小剛的自知之明,有一個人物他一定還是尊敬的,那個人就是——「凱爺」。
寫《趙氏孤兒》之前,拿馮小剛來「墊底」。其實是想藉此表達這樣一種情緒:除卻沒有脫卻文藝胎記和非主流陰影的賈樟柯,王小帥等人,中國主流電影的創作群體中,還能作為個體藝術家,來展開美學和藝術探討的,也許只剩下了兩個人,一個是陳凱歌,一個是姜文。
而相比於創造力更為優渥的姜文,陳凱歌是真正的傳統延續者,從這個角度上講,陳凱歌也真可以稱得上留在中國電影現實中,帶有傳統精神風骨的「趙氏孤兒」。
也許,有人看到這裡,會詢問我要把張藝謀的放在哪裡?這樣說吧,上一段文字里之所以強調「個體藝術家」這個詞彙,即是因為在我的眼中,張藝謀的藝術創作個體特徵,已經逐漸趨於消失,張藝謀這三個字,其實已經是一個公司,一個團隊,用黃健翔老師的經典語錄說,他已經「不是一個人」。
雖然影評界,素來把「張陳之爭」作為永恆話題,但從張藝謀混亂的創作路線就可以看出,張藝謀已經強大到除了自我什麼都不缺了;相比較而言,陳凱歌卻在多年來保留了他的恆定和文藝氣味,儘管他在創作中也必然要依賴團隊,但陳氏電影美學,還是很規矩地立在了那裡。
如果說張藝謀的全明星陣容來源於他的文化權力,馮小剛的全明星陣容來源於他的市場威力的話,那麼陳凱歌的全明星陣容,則應該是來源於對他文化魅力的尊崇。
從《趙氏孤兒》的表演中不難看出,影片中所有的演員,都處於一種很緊的狀態,連向來鬆弛的葛大爺,從肢體到語言,都讓人覺得有那麼一點僵硬;片中,最出神入化的莫過於王學圻,他那種「板著」的「文藝派」渾然天成,不僅與角色結合得好,與導演的氣息也是結合得最好的。惟一讓我覺得他演過的地方,可能王學圻本人未必同意,就是程嬰到屠府的一場戲,王學圻那一躺的駕式,雖然一點霸氣出來了,但卻逃離了屠岸賈這個人物本身,他的兇狠與不義,一直是被那身鎧甲包裹著,鬆弛的一躺,好像一下子使這個人物含混了。那種表演的情態,如果放到張豐毅身上似乎更為合適,張豐毅真是那種散著頭髮也有霸氣的演員。
全片最不上道的演員,非電視紅人海清莫屬,從氣質到表演,海清飾演的程嬰之妻牙根就是一不搭,她的眼神和氣息完全游離於影片之外,有點像影片末尾在市場上擺攤賣蘿蔔的那個群眾演員,不是一般之不對味。相比海清,范冰冰明顯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何平在電影《麥田》中已經讓她「母儀天下」了一回,這一回最多也就是一故伎重演,所以比較精緻到位,那一死的姿勢非常文藝,符合陳凱歌的審美趣味。
也就是說,從表演整體上看,《趙氏孤兒》並不是一部有什麼大問題的電影,它中規中矩,氣息暢通,演員努力而用心。
但能不能說這是一部很讓人意外的電影呢?恐怕也不能。
從視覺空間上看,這部電影是一部非常逼仄的電影,他幾乎推進於一種全內景模式中,除了程勃與屠岸賈在山野中「爛漫」的一場戲外,戰鬥的戲大約是最大的外景戲,但依然是在林子裡進行的,幾無空間感。比林子小的戲,就是在府門前和院子裡進行的,無論如何跑跳做動作,都使人的視覺感無法延宕開去。除視覺空間的逼仄之外,影片中散發出的人物心理也有清晰的逼仄意味,葛優飾演的程嬰緊緊地控制著孩子,讓他不得離開自己的視線。而且,更為讓人不安的是,程嬰和韓厥似乎總是竊竊私語,這種私語感,使一種情緒不自覺地散發了出來,這種情緒就是焦慮。這種焦慮使影片的題旨變得極為含混不清,加上程嬰反覆說培養趙氏孤兒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他復仇,而是要把成年的趙氏孤兒展示在屠岸賈面上,讓屠岸賈知道這孤兒是誰,程嬰又是誰。
弄不懂作為核心人物,他的這樣一種想法和闡述的目的是什麼?僅僅是為了經典以英雄平民化的方式「再生」?
從陳凱歌對《趙氏孤兒》的改編來看,他的確很想實現程嬰獻子的平民邏輯:把門客改成醫生,不能不說是為了隔離「知恩圖報」的層面;又給程嬰獻子塗上了一點「無奈」的邏輯,「兩害面前取其輕」——在認為自己的兒子已經出城的情況下,出賣公孫杵臼。
但這種改編,並沒實現本質上的平民化意義,最終歸於答案的還是一場對話:屠岸賈最初之所以相信他找到了真正的趙氏孤兒,恰恰是程嬰交給他的那個動作,程嬰的解釋則是,他之所以有那樣一個動作是因為看到了公孫杵臼的死。
而支持這樣一種行為的根源還是道德感召——人家公孫杵臼這麼樣就死了,我又怎麼可以不獻出自己的孩子呢?即使我不獻出,也未必意味著孩子的安全呵。這也恰恰是中國士子(門客)的慣常邏輯,即所謂「有恩不報怎相逢,見義不為非為勇」。所以,對程嬰而言,公孫杵臼的道德感召是無法置疑的;這種道德感召,成了他後來成義的源泉,這一點也是符合《趙氏孤兒》原著的精神核心的。
所以,我根本看不出《趙氏孤兒》往平民化改編的必要性所在,也看不出改編的合理性。
相反,我卻看出了,陳凱歌在影片當中散漫著的焦慮,他就像程嬰控製程勃一樣地控制著的影片和人物的走向,結果又是什麼呢,只是一種逼仄的氛圍和焦慮的感覺。
令人不解的是,陳凱歌在經營這部影片時,為何一定要強調「經典重生,大愛永恆」這個概念,難道:「平民化」是親近世俗的唯一出路?難道:「大愛永恆」可以成為討好市場,爭取票房的一個概念?
個人之見,如果要真正改編,不如就按照《哈姆雷特》的方式來,把中國士子面臨的道德絕症改成一個存在問題,不讓故事再糾葛於救還是不救,救了怎麼辦。可以完全以洋化的方式著意於復仇,藉機思考一下存在與自我的問題,思考一下TO BE OR NOT TO BE,這樣的改編,可能使劇情更通達,也許會對海外的市場推廣能夠有所幫助。
對於改編而言,要嘛激烈地走過一點,要嘛慎重的面對和闡釋傳統。透過《趙氏孤兒》的改編,能夠分明地看出陳凱歌的尷尬,想改但還拘於傳統,想傳統又有現實的焦慮。這種尷尬,恰恰誘發了影片的多義——讓人說不清這是一個通向何方的故事,也讓人搞不懂,程嬰救孤最終的價值和意義,而這也就成了《趙氏孤兒》的不治之症。
電影雖然也是用來思考的,但決不是用來過度思考的,當一個導演沒有徹底想清楚的時候,最好還是不要輕易動手。儘管誰都能夠看到,作為主流電影導演的陳凱歌是焦慮於電影現實和自我創作的現實的。
對陳凱歌而言,他對中國電影的最好貢獻,或許就應該是在人家奔向產業化的大潮時,還能堅持一個人的價值,這取決於他的堅持和努力,而不是焦慮和慌張。
當然,他也可以說他不是一個人——他可以說是他是一個半人,那半個人,當然是陳紅。
哈哈。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