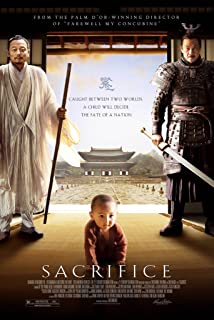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0-12-05 20:14:40
恨你恨到殺死我
復仇和愛情一樣是人類感情中最本質的東西,不用統計,地球上每天都有大量的復仇事件在發生,大致戰爭,小至孩童。因此,作為題材,復仇也成為電影中最為基本的元素,甚至可以跨越各種類型,可以這樣說-故事中的矛盾建置復仇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因為既符合邏輯,又符合人類情感,只要前因充足,渲染到位,就會極大調動起觀眾的復仇因子,期待劇情的深入發展。一句話,愛情可以不了了之,事業可以不了了之,鬼神可以不了了之,歷史可以不了了之,唯有復仇不能。
對於復仇電影,最具有代表性的大概首先是武俠片,最典型的模式就是滅門-遺孤-奇遇-練功-尋仇-決鬥-成功,概括起來就四個字:快意恩仇。總之,仇恨是以對方的瞬間死亡為終結的,在對手死亡的那一刻,仇恨消失,皆大歡喜。但是漸漸的,人們似乎已經不滿足於這種快意,電影中的尋仇方式開始變得複雜,一方面很明顯,就是可以增加情節的懸念與曲折程度,另外一方面,就是來自於人類的內心,也就是說,快意恩仇已經不再快意,已經不能解決內心的恨。
趙氏孤兒中程勃曾經問屠岸怎麼才能無敵於天下,屠岸答,當你做到無視你的敵人,同樣,怎樣才能完成復仇呢?就是你已經不再恨你的仇人。恨,是復仇的本質,是支撐這整個復仇事件的根本,恨的程度決定了復仇的方式,當見證了太多的快意恩仇之後,一招至敵似乎已經越來越不能解決恨這件事,倒好像是成全了仇敵。於是便出現了各種方式的至敵,其目的也不再侷限於對手的死亡,而更加集中到仇敵的痛苦,於是,復仇的瞬間被一再延長,幾年,十幾年,一輩子,下輩子,具體到影片中,也從以分秒,延長到整個段落,乃至全片。
不想延伸到現代人類對仇恨的認識,也不想涉及到網路暴力對仇恨的影響,只說電影本身,創意尋仇,黑色尋仇,已經獨樹一幟,比如近幾年以《老男孩》為代表的韓國復仇電影,共同點就是黑色,痛苦,折磨仇人,毀滅自己。也就是說,從仇恨建立的那一刻起,復仇者的價值觀就改變了,再沒有什麼事比復仇更有意義,再沒有什麼法律可以阻擋住復仇,在沒有什麼道理可以消釋仇恨,在沒有什麼比暴力更值得信賴。然而,當復仇事件終結的那一刻,卻在沒有什麼比成功更讓人失落,復仇者沒有了動作片裡的暢然,他們依舊痛苦,依舊恨。比如《看見惡魔》中李秉憲面對惡魔的屈服,以及復仇之後的無助,絕望地透露出一個資訊,復仇又能怎樣呢?心中的恨意不消,仇恨永存。
趙氏孤兒也是一個這樣的故事,不過這裡面還有一個更複雜的元素,借刀殺人,為了復仇,不光搭上自己,還要搭上別人。我覺得本片中最為成功之處在於,還原了程嬰的平民本質,他不是一個陰謀家,他缺少作為一名陰謀家應有的狠毒和沉穩,他甚至不是一名智者,沒辦法擺平各種年齡段的趙孤;但是他也不是一名善者,為了自己的仇恨背棄了趙家的最後囑託,把趙孤推上了復仇之路;他也絕不是一個常人,每天都要壓抑著觸手可及的投毒慾念,壓抑著對屠岸賈的仇恨,甚至要壓抑著對屠岸賈的再認識;但他又是一個常人,無法泯滅人類最本質的親情,在親情與仇恨面前無法抉擇。影片把戲劇中隱居深山的情節,改為隱居朝野,化小隱為大隱,基本上走上了創意尋仇的道路,從這一刻起,它的復仇本質改變了,不再是潛龍伏野,一朝在天的卦象,而變成了龍在天頂,欲向下落的趨勢,也就是說,這個影片整體上的氣勢是向下的,隱忍的,復仇的高潮就是整體氣勢最低的點位,高潮混入了塵土。至於韓厥的戲,我個人認為還是比較精彩的,他和程嬰漫長而詭異乃至類似於夫婦的相處,他們對於小趙孤教育問題的長期討論,平添了幾絲喜劇元素,但並沒有攪亂整個復仇劇的悲劇氛圍,反倒暗中標示了整個復仇事件的荒誕性,他們的復仇都是自私的,意氣用事的,他們玩兒的不是屠岸賈,不是小趙孤,而是他們自己。
對於本片的矛盾建置,還有一個暗線,就是仇恨與親情,或者說血統與情感的衝突,小趙孤面對三個父親,一個是素未謀面但骨血相融的生父,一個是心懷忐忑朝夕相處的養父,還有一個有殺父之仇卻情深意重的義父,他會如何選擇。我覺得影片在這個方面也是忐忑和猶豫不絕的,最終選擇了隱忍的方式,選擇了讓內心沒有仇恨的趙孤在瞬間做出抉擇,沒有內心的拷問,沒有復仇的動力,更多的可能是血統的驅使,趙盾的血在身體裡湧動,趙家的仇恨附著在遺孤的身上,最終不是程英的復仇,也不是韓厥的復仇,更不是趙孤的復仇,而演變成了整個趙氏的復仇,這個時候,場景是比較虛無的,漫長的決鬥過程中,王的身邊沒有護衛,而當屠岸賈平靜倒下的那一刻,可能只有他的心中沒有仇恨,當初他何嘗是沒有仇恨呢,但是他的仇恨在屠光趙氏的那一刻已經解決掉了,這個復仇戲裡面,心中無恨的,只有屠岸賈。他可能早就在懷疑小趙孤了,但是他已經沒有恨了,所以他也就沒有了狠,所以他註定要被復仇。他無視他的敵人,也無視他的仇人,在他看來,不過是你拿了我的東西,我拿回來,有本事的話,你再拿回去的事情,就是有借有還的人類規矩,他這麼想,他超脫了,他也完蛋了。
相對於前面的敘述,影片的結尾顯得緩慢,拖沓,沒有力度,這可能是陳凱歌的抉擇,他不願意做華麗精彩但是商業的設置,也難以讓三人同室,兩父一子的舞台劇如何的驚心動魄風起雲湧,(這個時候不知道他是不是將他的同學張藝謀在《十面埋伏》裡頭那個兩夫一妻曠野對決引以為戒)更不敢想像屠岸賈萬一打敗趙孤後該怎麼收場,畢竟決鬥這件事兒是沒有懸念的,那怎麼辦?
當然是解鈴還須繫鈴人,一切都是程嬰導演的,程導既不商業,也不藝術,而且還時常穿幫,但是他還是把這齣戲導完了,在程導倒下的那一刻,茫然的環顧四週,或許還歉疚地看了陳導一眼——程嬰只是個二流導演,只能導到這份兒了,因此沒辦法給陳導一個更給力的結局,也許,這樣的復仇本來就是不能給力的,給力的話,就不是程嬰了。給力的話,就沒有這齣戲了。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