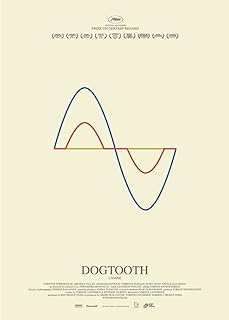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1-03-23 01:51:52
《狗牙》避重就輕的遺憾
影片開始,呈現的怪異,逐步帶你覷視窒息封閉的病態生活。三個「小朋友」學習完扭曲變異了的單詞,開始玩測試耐力的遊戲。後來他們又玩幪眼睛找媽媽,游泳池裡詐死並救生,搶飛機模型,麻醉自己看誰先醒來……溫和的玩法變得無聊了,他們就會找些激烈的,比如一刀劃開弟弟的手臂,一剪子虐殺小貓……直至最後大女兒用啞鈴敲碎自己的犬牙,血肉模糊地鑽進汽車後備箱,以行動吶喊出嚮往外面的世界,要脫離魔窟的自然意願。
講上面的劇情,你會瞠目結舌,這不是全部,還有更多無法想像的面目。一個富裕的變態家庭,一對夫妻與三個成年的孩子,在與世隔絕的鄉郊別墅生活。在父親與母親共謀的軟性恐怖統治中,孩子們像動物一樣,迫使沒有思想地吃喝拉撒。他們是犬齒之家,只有父親開車出入家門與外界接觸。其他人不得跨出家門半步,他們被灌輸外面到處都是兇猛吃人的動物,而且都在漫長隔絕社會的生活習慣中,變成了對外界一無所知的、懼怕亦無力幻想的原始「生物」。但有慾望,帶有暴戾的攻擊性,充滿好奇心,同時又缺乏自控力,沒有是非善惡的分辨力。跳出人形,可以想像,豢養的畫面。
而要維持這樣一種特殊家庭的穩定和諧,犬之首的父親自有辦法。思想上,頭領享受自幼洗腦幼仔的成功果實,並隨他們的成長繼續發展著。「殭屍」的單詞在這裡是「花朵」的意思,「電話」的意思是「椒鹽」,隨便一個來自外界的詞彙都被美化成其他詞意,必須屏蔽所有會激發孩子們思考的資訊,包裝袋上的說明一律銷毀。但小女兒可以閱讀醫學書籍,自以為醫術高明。大女兒可以群魔附身般亂舞,縱容萌芽的創造力與自我存在感。兒子無需禁慾,父親還會異常重視這些,就像重視發情期的動物,以免其危險的攻擊性。事物總有正反面,哪怕百分之九十的隔絕,依然是個露縫的蛋,那就有蒼蠅叮咬。總之,思想上的控制,應該是極端的理想化保護主義,又是尋求獸化的病態心理,本身就不安全。
生活中,他工廠的門衛女便是用錢找來的發洩工具,以防洩漏秘密,女人被戴上眼罩,定期被犬爸爸帶入這個家庭,動物似地滿足成年兒子的需求。結果女人不老實,用髮夾、髮膠、錄影帶交換,誘騙犬女為其性服務,結果被犬爸爸發現,並惡劣懲罰。之後亂倫上演,為保持家庭的徹底封閉、安全,大女兒擔當起慰安兒子的工具,整個家庭暫時回歸平靜。但非真相,隨犬爸爸的會議精神——必須接納訓練完畢的小狗(非常怯懦的小白狗),及那盤錄影帶的深刻影響,大女兒消失,像他們之前祭奠的哥哥,是死是活?又一個逃走了,而他們家的生活依然在悄無聲息的毀滅中繼續行進。
只用文字表達,足夠驚悚怪誕。但移入畫面,在電影《狗牙》中詮釋,就有了偏重唯美與雕飾的藝術氣息。有一點必須肯定,片子對細節的刻畫,相當細膩。但我又會覺得其中一些細節幾乎是可有可無的裝飾品,完全可以點到為止。甚至其影響力遮住了導演所要傳遞的沉重意義。
我看希臘電影十分有限,所以在觀看完《狗牙》之後,腦子裡一下子填滿了限量的影像,卻都是美輪美奐的珍貴古希臘裸體雕塑像,又想起那個可置換人物的笑料,是法國羅浮宮還是何地藝術博物館,老婆婆解下圍巾,用它來遮掩裸體雕塑像的私密處。笑是笑了,其實我還是不懂婆婆的舉動怎麼就成了「她一人迂腐」的糊塗,她的羞澀與否,若不干涉阻礙他人,都可視做正常,而且如此生動可愛的「思想」還會在某些地方某些人的生活中繼續。
說來,界定純潔的藝術與粗鄙的生活,不會有永恆不變的標尺,都在人的心念中,也時刻被發展的外物推動著。你有時看到的是偉大的藝術創作,你有時又會懷疑它存在的價值。我的不成熟及所教養成形的人格,一直左右我的思考方向與接受事物極限。就說電影作品,我一直鍾情於含蓄並深刻的內斂姿態,對華麗甚至冒險前衛的表象確實無興趣。
就了解一個人的思維模式與行為能力,它所能呈現出何種極致,乃至變態,希臘《狗牙》主要實驗了這樣一課題。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他不僅要成為統領全家的國王,他還要掌控妻子與孩子們的思維與行為,並信仰著一種變態的遠古犬齒獸類的生活模式。這也是一種世界觀,人生觀,至少完全影響著這一家子五口人的生活。現實中類似的可能存在,這時就要相信那句話,豐富多彩的生活,演繹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因為,特例是加工成藝術作品絕好的材料,所以可以理解用這樣一部作品參選奧斯卡外語片的意圖。坦白講,我看電影之前,對劇情毫無概念,但就是衝著希臘電影被提名的幕後文章去的。結果,比較《更好的世界》,此部落選也覺在情理之中。
正如電影故事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家庭教育方式,超越限度,便失去了令觀者各抒己見的客觀魅力,只剩下集體推倒邪惡之牆的忿氣。導演太過興奮的情緒外漏是整部劇深度被消減的癥結,歐格斯•蘭斯莫斯懂得緩中急衝的力度,也知表現變態的各種小技巧,但太過沉溺他的鏡頭,最終導致香艷過濃,能露則露,能做則做,故事又太過平緩,沒有高低起伏,回味的內涵如搖曳的燭火,漸遠只有豆大的光了。
但對犬爸爸的性格刻畫是成功的,變態的人格表現淋漓盡致,差就差一點洶湧的氣勢與力度。有兩個片段特別精彩,用錄影帶拳擊大女兒的腦袋,用錄像機狠砸門衛女的頭,那幾個動作嚇死人了。而其他人的表演也可圈可點。服務於劇情的硬件構思也夠獨特,白色服裝、簡單傢俱、空洞無物的思想,被置放進奢華的別墅,營造的不協調,的確也是渲染主題的用心之處。
始終要說電影徒留遺憾的地方在導演的拍攝手法上。如若可以澆注更多的「關心」在各種病態行為方式上,從心理層面,而非放大生理,伸拉出敘事的韌性,在犬爸的變態行徑中著墨些短淺的前因,多透露一些孩子們可能「背叛家庭」的蛛絲馬跡,以便劇情更合理,那麼電影就可加長至100多分鐘,觀後就不會有意猶未盡的淡味。可能還會冠上另一經典心理驚悚片的美名,誰知道會不會和《閃靈》一樣,讓人對這樣一個可怕的家長心有餘悸?為成長教育敲響警鐘。重視人文關懷。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