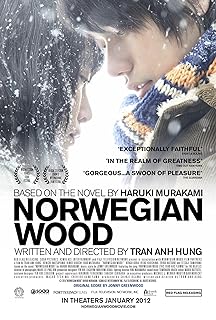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1-05-06 00:56:05
死寂 瘋亂
1 背景
看小說是零九年八九月的事,距現在逾一年半。暑假一起玩的時候,一位學哲學的朋友老在我面前咕叨《挪威的森林》怎麼好怎麼好,他怎麼喜歡怎麼喜歡。後來,在一個書攤相遇,他又說,賣這麼便宜,我買一本送給你吧……於是,我終於讀了那本小說。
一年半,不算太長。可在我,很多事情都已改變。小說裡的很多情節都變得模糊不清,也沒有重讀的必要,只是記得村上筆下那些狡黠幽默的文字,和無時不流淌著的淡淡而沉鬱的哀傷。不要看我們未到「而立、不惑、知天命」的份兒,可時代的變遷對個人生活的影響還真是很大的。前天夜裡失眠,怎麼也睡不著,直至凌晨五點。彷彿要把一輩子的事翻覆一千遍直到炒熟炒爛。看電影是昨天晚上,本來由於睡眠不足腦子昏昏沉沉,可還是看到一點多,又繼續失眠至兩點多才睡。
多半是抱著好奇才看的,早知道會對電影失望。果不其然。有人說夜裡不宜看這種電影,對睡眠有影響。管不了這許多了。
2 進入
一開始的鏡頭是兩個少年在那兒做搏擊遊戲,渡邊和木月、直子的故事。那感覺只能用兩個詞兒形容:貧瘠、寒磣。這明明白白是暴露給你電影在藝術功能上之輸於文學的地方:文字里對人物情感的直接介入、圓融通透,對於電影而言卻很為難。
電影自以為對現實有著逼真再現的優勢。但現實情境在演變為電影的時候卻要接受很大的考驗。首先,現實多是醜陋不堪的,進入電影就難免淪為扭捏造作;其次,演員的造型和外貌要接受觀眾和它自身的檢驗,二者都是很苛刻的。不苛刻不行。
兩個少年都不夠美。友情的碎片忽閃而過。於是有種感覺,村上的小說被一把剪子剪布鞋一般剪成碎片了。然後渡邊到了東京讀書,大學生活形成一種「眾人狂歡惟我自在」的動靜對比。我們覺得,手法有些太小兒科了。
3 以貌取人
一定要說到這個問題。演員的外貌關乎審美效果和觀影情緒,而且是直觀的、門面的事。總的來說,我對演員的外貌以不滿居重。當然這只是我個人感受。
木月就不說了吧。木月本該是個帥氣、略顯成熟、內在憂鬱的男孩,可電影專橫地要他與主角渡邊形成對比,於是他成了全片長相最寒磣的一個。彷彿一個外地轉來的貧困學生穿上了和大家一樣的校服,地位統一了,卻掩不住貧窘悲摧的命運,一副必然早死的暗示……既然會早死,導演就潦草地將其一筆帶過了。
直子的長相和氣質竟然帶有一種過於外露的喜感,這令我很是吃驚。圓圓的臉,雙眼皮兒,眼神無時不積著一潭無奈、歉疚。我覺得她長得像某一個演員,想不起是誰,還覺得她跟一位80後女作家有幾分相似,也不敢確定。總之,全沒在我的想像之中。我的印象里,直子是憂鬱、冷漠的化身。說得難聽點,要讓人想到幽魂倩女勉強活在陽光之下。她應該一張平板的臉頰,瘦削淡薄的身材,冷若冰霜的膚色,纖細滑膩的手指,黧黑而拉直的長髮(這點倒很符合),慢吞吞的步伐,期期艾艾、略顯遲鈍的語言表達……可電影裡的直子,卻讓我感覺她是從歡笑中長大的,圓圓的、鼓起的臉蛋,唇齒外露,急匆匆,情緒激烈。直子有憂鬱症和精神分裂的病症,這不假。只是到了荒野般的阿美寮(電影中沒有提到這個名字,就像撇開了菲茨傑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這些名字一樣),直子才表現出了她那狂野而陰鬱可怕的一面……直子死時的畫面,場面是冬日荒山陰沉、蕭條,伴著壓抑的重低音,接著露出兩條懸空的腿,我被嚇了個半死——這是我認為片中最像恐怖片的一個場面。導演還是很狠的。
渡邊是重頭戲,是男一號。大約開始沒有完整露面,我沒看清,一個小破孩的貧相。到了東京、見到直子,我才發現,這個渡邊原來是我國偶像明星粥孑輪在鄰邦日本的翻版……那髮型、臉廓、眼神、氣質等諸多地方都有50%左右的重合。不一樣的地方可能在嘴巴和鼻子,相像度將至25%。渡邊君有著濃厚的孩子氣,純真而略帶害羞。於是他的上唇尖而外翹,下唇內縮。上唇代表天真,下唇代表內斂。鼻子右半部一顆隱隱的痣,這是個無關緊要的地方。非常有意思的是渡邊的語氣和眼神。不慌不慢、慢條斯理、周轉有致,跟女孩說話的時候,斜眼暼望,顯得天真無知;行語簡潔沉穩,稍含哲理,擲地有聲,朋友們都覺得他很有意思,女孩認為他很會哄人;渡邊學著周董的樣子,不多發語,深沉為主,需要肯定時「或許如此」,需要質疑時「是嗎」,難置可否時「嗯?」,不想說話時「嗯」……就這一點講,渡邊君的表演基本合格,可以打80分。大異其趣的是最後在海邊的鬼哭狼嚎的樣子,那是悲痛欲絕的仰天悲鳴,雖說可以從小說中想像到,但表演出來還是很讓人玩味。好笑,又讓人生出一種酸楚。
綠子也很重要,演員跟我的預想也產生了40°的偏差。綠子的出場非常搞笑,一副時髦女郎的紅色裝束,肩挑長系黑包,從後面一步一娉婷地走向渡邊,我以為是同學們在餐廳演話劇。還有那副大熊貓黑片眼鏡,大得要把整張臉遮住。可憐她的身材、腦袋、臉都是那麼小巧、輕飄。嘴唇又大又厚,很不乖巧。眼睛常射斜光,總是歪著腦袋發揮自己邪惡的想像……眼睛和嘴唇的設置讓綠子帶上了混血兒的特徵。我不記得小說中是否有這樣的描寫。惜乎導演刪掉了渡邊在醫院陪護時餵黃瓜、聽老頭兒胡言的那幽默段子,更惜乎刪掉了渡邊和綠子在二樓做飯、聊天、接吻然後附近失火濃煙大作綠子聽渡邊說一起赴火死去的感人段子(哪怕這些「感人」都是很小資、輕飄飄的)。後半段,電影的戲份火力集中於直子的苦難和死,綠子被忽視了。本來小說中似乎就是如此,可我覺得導演進一步把綠子給忘掉了,既沒有把綠子那種瘋狂、活潑如一隻森林小鹿的個性發揮出來,又導致她與渡邊的感情交流和深入不夠,這對綠子多少是不公平的。以致於最後我感覺不到渡邊到底有多愛綠子……
最後說三個次要人物。永澤、初美和玲子。其實三人都是重要的。永澤是富家子弟,風流倜儻,不拘小節,思想高深,野心勃勃,看重意氣,卻跟劉玄德龜兒一樣視「女人如衣物」,負心薄倖,沒心沒肺,丟我們男兒家的臉。雖戲份不太重,但演技可打90以上。初美,我覺得要打99分,著實是個美不可言的女孩。剩下的1%留給文學的想像力。儘管有直子和綠子兩根柱子支撐,可我覺得沒人會反對,初美才是最美的,美到讓人忘記一切不潔、忘記時間流逝的地步。沒有初美和她的美,世界也不完美了。小說里,渡邊在酒後和初美坐在出租里觀察到初美的動人以及多年後渡邊在墨西哥城咖啡館看到染紅天地的晚霞想起初美那令人驚嘆的美,是令人難忘的。計程車那段,導演進行了細部的刻畫,值得稱讚,後者難度太大,不怪導演。你可以發現,渡邊幾乎和故事裡所有女人都發生過關係,唯有初美是沒沾過的。有一種力量禁止你做這種想像。說到底,是初美太美了,那雙珠寶一般(很多用此比喻的形象都是欺世盜名)的大眼珠,那種具有震懾力量的沉穩和氣質,讓周圍的一切黯然失色,繼而枯萎。至於玲子,這位大姐,也很有味道。我認為在所有演員里,玲子是最有日本風味的一個。卷尾短髮,平白額頭,蒼白膚色,一笑起來彎成一雙月牙的眼睛,平和溫藹的性情,都符合小說中的描寫。我記得玲子有一段和學生發生拉拉事件的經歷,在片中刪去是合理的,場面已經夠亂了。讓我隱約覺得可惡的,是最後玲子找到野遊歸來的渡邊,請求並最終與渡邊做愛的情節,從小說到電影,我都不太理解這種女人的心理。難道是關係至親,以致於要為密友魂魄附身之後進入對方嗎?……這一點下面還要說到。
4 阿美寮
開始說過,片子一開始很貧瘠,可後來我慢慢找到了感覺。一方面是小說的感覺回來了,另一方面是影片色調的美。本來全片都有可言之處,只是這種風格和特點在荒山休養所阿美寮表現得最為突出。影片絕口不提阿美寮這個名字,就像撇開了其他很多成份一樣,大概是為了減輕台詞的累贅,集中精力於情節。
細膩、溫和、冷艷、寧靜、幽遠。這是影片的色調特徵。
我有些不解,在我看來,阿美寮中的荒僻、詭異、寒冷都是個讓人渾身戰慄的「鬼地方」,它的美是一種純自然的美,怎麼會「適於療養和病情恢復」呢?四季變換,阿美寮的風景讓人生出嚮往,暗示著直子的病情也在變化。錯綜複雜的密林小道,滿山遍野、像魔鬼髮絲般的草場,河水清澈、冰清玉潔的河谷,大樹獨立、狂風呼嘯肆虐的荒地,雪原蒼茫、樹色幽黑的林子……這一幅幅悠遠的畫境堪比名家手筆。用我一個純潔小友的說法,渡邊和直子在那裡一次次地「幹壞事」。風景的蠻荒、蒼涼,和人物的焦慮、陰鬱甚至死亡氣息交織在一起,不知是一種悽美,還是生命渴望的張力。
影片省略了小說中平凡的生活細節,省略了直子深夜在渡邊床前裸體的美,而是無數次地重複兩人做愛前後的糾結、困境和折磨。色情、壓抑、「濕嗒嗒的」氣氛於是無可遏制地直線飆升。對比於小說,直子和渡邊此時都不夠冷靜,不夠沉穩,缺乏了思考和感受的美。直子在狂風大作的草原上失去控制,撕心裂肺地大叫,魔鬼般的長草發瘋般搖擺,讓人渾身發冷,感到生之可怕。鏡頭從黑白分明的雪色山嶺線條移到隧洞般漆黑的粗樹幹,繼而移到灰色的半空,最後出現了兩隻靜止懸空的腿腳,讓人感到死之可怖。
5 主題
這一點簡單說一下。直子說過一段話,「要我說,人應該在18歲和19歲之間循環……18歲之後是19歲,19歲之後又變回18歲。要是可能的話,那就輕鬆了……」小說中大概是有這話,我印象不深了。但聽到這兒,我才找到小說的感覺,覺得小說一直有著此類問題的思考。可電影偏偏躲著這些主題。
不知影片在對小說做「縮骨功」的時候,怎麼苗條到了這個地步,人物豐富的情感不見了,大量細節得不到體現。全部的情節糾結於一個主題。
簡言之,各種人物的性關係混亂不堪。無論渡邊在哪裡、跟誰說話,總離不開「睡覺」「做」這個事情。他們的語言交流,總是在「你跟他(她)誰過沒有」「為什麼沒有睡過」「睡過幾次」「跟你做」「幫你釋放」「濕與不濕」一類的話語之間徘徊,重複得要融化了一樣。玲子和渡邊做愛,又是出幹什麼樣的心理呢?留給你去猜吧……
一貫思竟邪焉、很不純潔的綠子,懷著喪父之慟打電話給渡邊,大哀欲絕地問渡邊「你會帶我去看黃片嗎?」(回答:會的)然後「看最黃最黃的那種嗎?」(回答:我儘量找找看)……黃色的思想都要被淚水浸泡得浮腫了,不知到底要鬧哪樣……這就是這個唯一的主題在片中的氣派,讓人哭笑不得。這就很讓人懷疑導演的純潔動機。不在於小說原作寫了什麼,而在於電影裡表現了什麼。
6 結尾
對於結尾,我認為是電影最失敗的地方。沒等我看到眉目,情節已經過去了,草率的表演也讓小說本該有的意境大打折扣。
容我摘錄小說最後一段。迷失歸來的渡邊覺得自己還是要活下去,於是終於想起了綠子,想要見她,打電話過去。傷透了心的綠子問「你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哪裡?
我拿著聽筒揚起臉,飛快地環視電話亭四週。我現在哪裡?我不知道這裡是哪裡,全然摸不著頭腦。這裡究竟是哪裡?目力所及,無不是不知走去哪裡的無數男男女女。我在哪裡也不是的場所的正中央,不斷地呼喚著綠子。
電影對結尾渡邊這種環顧世界、如身處荒原般茫然無措的無在感和對現世實在的渴盼熟視無睹,一句台詞之後戛然切斷,繼而是兩句很扯的關於生死的思辨話語。如此粗劣,功力很是欠修煉。
開頭說到我那位學哲學的朋友。在我看來,他是個很有思想、較有深度和行動力的人,對應故事中各色人物,他在性格上更像永澤。然而,即將畢業,他卻並不如意。某日,我接到他父親電話,說該友在家裡情緒低落,意氣消沉……我為我的朋友感到不滿。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