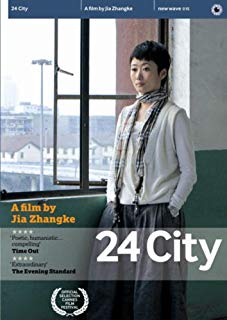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1-12-25 04:06:37
「二十四城芙蓉花,錦官自昔稱繁華」
《二十四城記》雖然是帶有戲劇虛構成份的電影,卻以紀錄片的寫實風格再現了成發集團於上世紀50年代至二十一世紀的興衰變遷。其間,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受訪對象紛紛訴說自身與成發集團的往事,由個體至社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成都在近半個世紀中的現代化變遷,今昔對比間,時空的滄桑感立顯,真可謂「二十四城芙蓉花,錦官自昔稱繁華」。
成發集團的生命歷程是依附於中國的社會大背景的,每個不同的年代都有其特有的時代烙印。50年代,韓戰爆發,以及出於鞏固新生政權的需要,420廠於成都誕生。作為軍事工業的重鎮,瀋陽的一些軍工廠紛紛南遷成都,影片中,侯麗君、郝大麗等人便是背井離鄉從瀋陽遷往成都的工人典型。那時的420,作為國防部署的一部份而直屬於國家,接受軍事化管理,體制色彩濃厚。80、90年代,成發集團在其發展過程中,漸漸完成了從國企到外企的轉變,適應了經濟制度的嬗變與市場的發展。二十一世紀,成發被雨潤收購,躋身房地產行業,隱沒於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二十四城的芙蓉花開了,錦官原有的繁華就此謝幕。
開頭是一段成發領導冠冕堂皇的致辭,座中的工人們,穿著工人階級特有的藍色制服,默默接受下崗的「宣判」。工人橫跨老中青三代,既有元老級的老師傅,又有紮根成都的知青,又有頂替而來的工人子女,或許他們曾為了420傾其所有,或許他們當年被禁錮於體制中失去了原本不該失去的東西,但現在,他們必須得下崗。破敗傾頹的工廠,被拆卸下來的集團商標,成發在社會結構的變動中被隨之解構,而她所有的配置,包括工人們,都將隨之四散。
「整個造飛機的工廠像一個巨大的眼球,而勞動是它最深的部份。」然而,工人階級的地位在不同的年代不盡相同。50、60年代,工人階級是社會生產的重要力量,堪稱中流砥柱。420的老鉗工們,懂得如何最大限度地磨好一塊材料,他們珍惜國家的資源,因而,國有工業的輝煌都是在他們的勤謹與珍惜中鑄就的。當時,工人們可以享受社會福利的優待,正如郝大麗所言,除了每月58元的工資,420的工人可額外享受5元的保密費,在自然災害期間,工人們還能拿到肉票。或許,在當時,工人是無產階級中的「貴族」。但在80年代後,在生產現代化進程中,工人的地位逐漸式微。片中的人物之一孫衛東,因為工人階級的尷尬地位,而與女友分道揚鑣。而八零後的娜娜,也在工了解體後成為跑單幫打工族的一員,顛沛流離。但工人社會地位的下降並不意味著工人精神境界的墮落,昔日的「標準件」、「廠花」小花,在「剩女」的窘境中,仍能不失原色:「我就算不是『標準件』,也不是『報廢件』,我有自己的『標準尺寸』。」
郝大麗是體制的受害者,最終被時代拋之腦後,被徹底遺忘了。作為從瀋陽內遷的工人之一,郝大麗背井離鄉,與親人們生死兩茫茫。在南遷途中,郝大麗永遠丟失了一雙兒女。然而,森嚴的體制沒能給她追回兒女的希望,「當時工廠是軍事化管理,一舉一動都關乎國家的安全,汽笛就是命令,我們必須得走。」郝大麗的悲痛或許是個體的極限,但對於當時整個社會而言,或許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不足以被量化。所以,郝大麗是體制下的犧牲品,她失去了個人的幸福,僅僅是因為國家的某項「規定」,她作為個體的人生幸福被忽視了。
汽笛有多重隱喻。它是一種權力、體制的象徵,也是話語權的象徵。在六十年代,郝大麗等瀋陽工人南遷重慶,完全是體制安排的結果,工人在就業上完全是國家分配,毫無自主權,雖然這樣的制度操作有其必然性,但卻完全置個體的利益於不顧。同時,它也是一種不乏政治意味的話語權: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因而,個人的幸福是可以被置之度外的。郝大麗就是這樣一個不得不屈從於社會主流話語權的犧牲品。她的社會角色在那一刻完全起衝突了:一邊是本應完全服從組織安排的軍工內部人員,一邊是母親是人妻。她既面臨著硬性的職責,又擔負著為人母的責任,但在當時特殊的社會背景下,她只能無力地屈服於國家冰冷的制度,放棄了尋找一雙兒女的機會。在政治掌握主要話語權的六十年代社會,這樣的個人悲劇不勝枚舉。文革悲劇尤甚。社會是先於個人的存在,個體難以超越社會而存在,因而社會對於個體的影響與制約可見一斑。因此,「我們開始明白在某一社會中,一代代的人的個人生活;他生活在自己的生活歷程中,而這個又存在於某個歷史序列中。因為他正在生活這一事實,他就對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演進作出了貢獻,無論這個貢獻是多麼微不足道,甚至連他自己也是在社會和歷史的推進作用下塑造出來的。」我想,米爾斯這個頗具功能主義思想的論述,是不是能夠概括個體之於社會看似渺小又偉大的一生呢?
然而,老年的郝大麗在孤獨中還是被時代遺忘了。她在廠里組成工人家庭,她見證了420在建國之初一步一腳印的輝煌,她有一種歸屬感,依附於國家的歸屬感。但是,那個走計劃經濟路線、以階級鬥爭為主線的國家在改革開放後漸漸轉型,生產方式的現代化使得工人的地位邊緣化,國企變成外企,當她驚異於21世紀的成發女職員上班化妝時,那個素顏的純真年代早已遠去,所剩無幾。郝大麗是時代的遺物,她無法調試這樣的脫節,她只能孤獨地坐在電視機前,看追溯抗戰年代的老電影,靠回憶來支撐自己的價值觀。可以說,她已經一無所有,只有悲苦的回憶。郝大麗的痛,是一代人的痛。或許九零後的我無力批判60年代的體制,但個體的悲哀,或許還是能想像的。魯迅說:「那些遠方的人,都與我有關。」社會需要人文關懷。六十年代的人們,經歷了政治集權乃至文革的衝擊,社會處於文化精神的荒漠狀態,他們的精神世界也是荒蕪而枯槁的,因而,我們不難理解文革時期文藝作品之寥寥,也不難理解文革後除了反思文革的「傷痕文學」就別無其他。社會的文化結構被破壞了,而郝大麗這一代人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但是最後她的遭遇只能隱於歷史的長河中,來不及被同情就被遺忘了。這是一種對於個體的忽視、人文的缺失,令人唏噓。
廠花小花很出彩。知青總是一群有隱痛的人。小花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被迫離鄉,紮根異鄉,儘管是一名樸素的工人,但作為一個講究精緻的上海女子,小花堅持:「螺獅殼裡做道場」,追求生活的層次與格調。小花的故事或許有些典型,因為時代的種種原因,錯失了終生幸福,但讓人感動的是,人到中年的小花寧願單身也不願違心地給富佬當孩子的後媽。小花的堅持與獨立,讓我嗅到了一絲女性主義的味道,她追求的,不僅是物質、心理上的自立與平等,同時也向社會追求一種價值肯定,哪怕是最落魄時。
「僅你消逝的一面,已足以讓我榮耀一生。」儘管城市與個體都已新陳代謝,所幸我們還有回憶與記錄。時代的洪流滾滾向前,有些被沖走了,有些被留了下來,我們依舊感激那些留下來的聲音。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