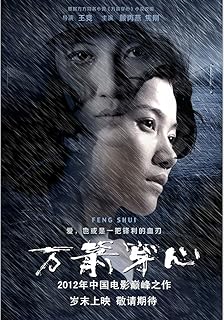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2-11-24 00:54:42
影片解讀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馬學武 – 每個人都有他的影子
馬學武真可謂是「冷暴力不合作」運動的集大成者。他的不合作是徹底和廣泛的,體現在:
• 他用各種藉口性冷淡,拒絕行房(影片開頭的場景)(這和偷情時的急不可耐和淫聲蕩漾形成極強烈的對比)
• 非語言行為上的不合作:他在家時成天神情木訥,行動遲緩,目無焦點,魂不守舍(這和他與同事談笑的眉飛色舞形成極強烈的對比)
• 肢體語言上的不合作:拒絕與李寶莉碰杯(這是影片的主題性畫面,後來在給兒子高考慶功的飯桌上再次出現這個畫面,這回拒絕與李寶莉碰杯的是兒子,但冥冥中好像馬學武借屍還魂)。對於李寶莉的卑躬屈膝,刻意迎奉,用轉身脫襪和關門來抵抗和拒絕。
• 拒絕言語與意圖的交流:體現在接母親來家裡住這件事上,馬學武僅僅稍作象徵性地表示,便如他偶爾施捨給李寶莉的幾下抽動一樣,很快就偃旗息鼓。其實他還真沒有同李寶莉交流和表達自己意圖的意願,就如他說的,房子是我的,要接老娘住,你甭管。即便是死,他也頑固地不留給李寶莉一個字。
• 完全拒絕情感的交流:例如對於李寶莉的情緒爆發,既不安慰也不面質,僅在躲在洗手間捏緊拳頭,做象徵性地反抗和發洩。(可能歷來如此)
• 馬學武的絕招應該是一種長期慢性且非常微妙的不合作:例如對於李寶莉與搬運工人錙銖必較,對孩子的粗燥管教,他均暗渡陳倉地懷柔和輕描淡寫地破壞,並藉此很輕易地佔據道德高地,博取同情好感。
相比李寶莉他確實屬於一個更有文化的階層。但他那富餘的文化和智力僅僅足以讓他一次次地逃離現實,耽於幻想。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對於生命怠惰的人。他把對於生命的種種失望轉為無處發洩的壓抑,泛化為一種缺乏行動意志的抑鬱和幾近絕望。面對生活的失望和不如意,不順心,面對著受本身文化水平和生活環境限制的李寶莉的種種缺點和不足,他也許沒有一刻想到自己可以試著介入,試著改變。恰恰相反,他的唯一救命稻草就是精神上的逃離和情感上的隔膜。他好像是生活的局外人,邊緣化的妄想者。促使他逃離現實的驅力如此之大,足可以使他把所有的情感,慾望,心力,正面意義和理想化均賦予他藉以逃離的對象。例如:
• 當李寶莉守在家中,想用溫柔和熱忱,甚至搬出孩子做救兵試圖挽回婚姻的時候,他毫不在意地選擇繼續找藉口加班,並和同事大肆吃喝,談笑風生,得意忘形(可以想見其他晚歸的夜晚)。
• 當李寶莉試圖進一步努力把他拴在身邊的時候,他「升級」了他的逃離,「事先通知」地與同事開房。
• 當李寶莉試圖利用東窗事發的道德羞恥感來進一步「罩著他」的時候,他又搬來救兵,讓老娘與他們合住,也好繼續避免直接面對李寶莉的壓迫。
• 當李寶莉發現了他的意圖,並產生激烈言語衝突後,他又再一次選擇逃離,試圖從情人那裡獲得想像中慰籍,並維持一種曖昧,以便繼續他精神和情感的逃離。可縱他苦情西施,痴話連篇,無奈別人卻早已齣戲,神情泰然,過(吃)得蠻好。他終於發現當他賦予了每次逃離太多的理想化和美好時, 如此的一相情願恰恰別人無法負載,而終究要自己承受失重失落的。
• 當他得知自己下崗時,終於覺得無路可逃了。因為下崗會逼迫他回家,喪失一切逃離的藉口。下崗會讓他在李寶莉面前更加抬不起頭,毫無翻身希望。而他唯一的情感出口也如雪景融化後的泥濘,一片狼藉,不堪回首。於是,他寧願懦弱地死也要逃離他不想面對的現實。在這裡,死是容易的,而生恰恰是艱難的。想像是容易的,而實際常常令人不堪。
人就是這樣,當我們學會想像和做夢後,一旦遭遇挫折和傷害,很多時候就如馬學武一樣活在自己的想像里,用理想化的曖昧代替直面現實。用各種積極的奔忙,來閉鎖禁錮自己的人生,卻不期然成了自己生活的破壞者和對他人冷暴力的施予者。每個人身上都有馬學武的影子,只是生活不是電影,它不會把你逼到走投無路,只會讓你在沉默中漸漸迷失,漸漸萎靡。
救貓咪 - 影片的移情工具
所謂「救貓咪」場景是指:當我們遇見主人公時,他必需要做一些讓我們喜歡上他的事情。通過救貓咪場景,我們完成了對於主人公的移情,從此開始關心她的命運,想他所想,急他所急,漸漸被影片牢牢地吸引。從某種程度上,建建和何嫂子都是李寶莉的貓咪。何嫂子和建建都先後是她關心和照顧的對象。從中可以反映出,李寶莉作為草根,對於其他底層勞動人民有著一種發自內心,自然流露的同情,善意。就像襪子店老闆對她冷嘲熱諷中透露出的為她擔心。但李寶莉與眾不同之處在與她的同情善意會轉化為主動關心和照顧的行動,且不計利害。
在影片的前半部,每當情節出現她暴烈的脾氣和不近情理的苛責後,會立即插入一個救貓咪的場景。維持觀眾對於李寶莉的移情。第一次救貓咪是對於何嫂子生意的照顧,甚至擋風遮雨。第二次救貓咪是得知建建被抓時,流露的對於建建安危福禍的關心和擔心(這時候的表情是微皺眉頭)。而且,這些救貓咪的場景在影片後半部不斷髮展。李寶莉擔心建建釋放後的出路,擔心他重操舊業,擔心打架鬥毆的是他,每次都如此輕蹙雙眉。李寶莉甚至還關心他收帳是否吃虧:只換了個破麵包車,關心他住得是否寒酸,關心他喝醉酒掉到溝里。李寶莉救貓咪之心從不改其衷或輕易受挫,而投入金錢和情感投入的代價也越來越大。一個人做一次好事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這樣的救貓咪次情節對於激發觀眾的移情,有著累加和疊加的效果。影片這樣安排是非常巧妙的。從社會心理學來看,對於一個人初期印象較差,隨著逐漸的了解,印象轉好,這樣的對比和反差對於人的心理衝擊力是最大的,勝過一直印象很好。於是,觀眾移情的程度就不斷增強,直到頂點。相比何嫂子,李寶莉甚至顯得更能吃苦,更會做扁擔生意。但何嫂子的性格比較平淡,很難進一步反襯李寶莉的性格。何嫂子的惟一敘事功能就是調侃了陰盛陽衰(這在影片中和生活中無疑都是事實)。於是,在何嫂子次情節結束(在一次忍受婆婆逼迫和揶揄的,代價重大的救貓咪行動中達到高潮)後,建建的次情節便漸入高潮。
建建 – 一個自我擊敗的人,李寶莉的一面鏡子
建建正如他自己所說是一個嘴賤的人。想必他的真情曾遇到過持久的傷害,在他內心深處產生了恐懼和巨大的羞恥感。於是,每當他要表示善意時,或者產生與人接近的願望時,那種對於傷害的回憶和羞恥感就條件反射般地湧到心頭。從而,他發展了一套自我擊敗的人生策略:既然多情總被無情傷,那麼在你還沒有傷害我之前,我就先發制人,先無情地攻擊你,這樣我就可以避免被傷害:
• 出獄回來遇到李寶莉的主動關心,他明明有些觸動,卻說,怎麼怕我嗎?
• 邀請李寶莉去看他的貨運站,本來很熱情,他非要加上一句,你又不能給我帶來生意,你個扁擔。
• 在誘姦李寶莉後,他明明想和她約會,卻莫名其妙發揮了一大段:現在的人都很隨便,做完了跟沒事一樣。
• 李寶莉去探望他,幫他收拾屋子,他明明感激,卻推託說,我又沒有請鐘點工。
• 李寶莉弄傷了他,去賠錢道歉。他試圖表示不想談錢,不想見外,卻說成我睡了你也沒有吃虧,你怎麼倒貼我錢。
• 當他從李寶莉的委屈爆發中意識到她的真情流露時,他內心應該有所感動,卻明確冷冷地說本來就沒有當真,不要裝得很有情。
• 當然,在影片的最後,他終於第一次說出了主動關心的話(有什麼打算),自我表露的話(我就是嘴賤),毫不猶豫擔當的話(老子不怕),再沒有加上一句什麼。
其實建建活脫就像李寶莉的一面鏡子:他們的父母可能由於生活的苦難和重擔忽略了他們,可能因為本身性格和脾氣乃至文化素養的侷限對他們的情感需求置之不理,或者甚至對他們施加了言語乃至肢體的暴力。於是,他們生活在一種強大的不安全感中。他們是如此地需要愛,渴望愛,想表達愛,卻因為生命早期種種的共情挫敗和巨大羞恥感,演出成了一種怒氣和攻擊欲。他們沒有掌握愛的語言。他們粗暴地對待別人,也許恰恰是因為他們曾經被如此地粗暴對待。記得在搬家夫妻衝突中,李寶莉惡狠狠地罵馬學武:生得賤。也許她也被這樣責罵過。
李寶莉- 少有人能做到的堅韌,剛強和容忍
對於李寶莉而言,早年共情失敗的影響是巨大的。她真的缺乏共情的能力,即為別人設身處地設想的能力。李寶莉只能生活在她自己的現實框架和習慣思維裡面,無法哪怕一點點地跳脫出來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她說了勞心的事情她不行,她做能做到最勞心的事情,就是以己度人:
• 她也許生在一個錙銖必較,睚眥必報的環境裡,這既培養了她能為不多的報酬任勞任怨的態度,卻又帶給她為蠅頭小利斤斤計較的小市民思維定勢。她怎麼也不能共情搬運工人的辛苦,卻只能以己度人,反感他們不如自己任勞任怨,貨真價實,價格公道,錢貨兩清,更反感他們就地起價,懶惰不負責還貪她家小便宜。
• 她能感受到丈夫從當初跪地發誓對她好,到不合作冷暴力的變化,而自己心意似乎不變,為此憤懣委屈不已。但她卻感受不到自己優勢意識和強勢態度給丈夫帶來的委屈,受挫和不斷逃離。所以她強烈反對小景的警告。
• 對於丈夫百般拒絕房事或者敷衍了事,是因為夥計不給力或者第二天要搬家等藉口,她都木知木覺地相信,直到她發現丈夫和情人發生姦情時的急迫慷慨,春聲蕩漾,對比後方才覺悟深深的失落和自尊的貶抑。
• 她顧及兒子,沒有去抓姦在床,希望通過第三方外力把偷情的丈夫給輕易奪回來。卻沒能設想這麼做可能給丈夫帶來的事業和感情上的傷害。
• 她好不容易通過外力和自己的「寬大」把丈夫服服貼貼地抓到身邊頤指氣使,不料丈夫搬出老娘來橫插一槓。她氣急敗壞,怒火中燒,惡言相向,冷嘲熱諷,卻無法設想這麼做給丈夫和婆婆帶來的嚴重傷害。
• 她只知道拼命給孩子創造好的條件,把人生的一半奉獻給了孩子,卻體會不到自己的惡言厲吼,粗暴對待,缺乏共情的關心和缺乏陪伴,給孩子帶來的恐懼和疏離,以及丈夫,婆婆的態度對於兒子的負面影響。
• 當她知道丈夫自殺後,她只認為丈夫是受不了下崗的刺激自殺的。所以,她又以己度人,說自己下崗了,不還活得好好的。她想不清白,看不起丈夫的懦弱,更不能理解丈夫對她一言不發,甚至覺得丈夫有點對不起她。
反過來,曾經飽受損害和侮辱的李寶莉,對於人情冷漠,甚至是粗暴對待,卻有著深厚的容忍力和超強的耐受度。對於丈夫拒絕敬酒,李寶莉自我調侃說,今天高興不和你計較。對於婆婆一次次的言語相逼,李寶莉每次都忍了,默默無言。也許冷漠的環境讓她習慣了,她從不認為自己不值得接受這些委屈。相反,對於早年愛的缺失,她恰恰希望不惜一切代價來換取這份愛,為此她寧願扮演一個犧牲者和照顧者的角色而甘之如飴,矢志不渝。
正因為她無法共情,影片前半部馬學武要求離婚,偷情,自殺成為了她人生的三個突如其來,莫名其妙,毫無抵抗,衝擊巨大的大災難。但是,與馬學武不同,李寶莉決不逃避,打倒了再爬起來,勇敢面對。她有著底層勞動人民特有的堅韌和剛強,以及強大的意志力。影片的前半部在激勵事件(馬學武提出離婚)後,由她強大的意志力貫穿。馬學武提出離婚,她痛哭過就去找小景出主意,在小景的勸告下,用不斷升級的各種辦法把馬學武拴在身邊。例如從苦苦守候,好生伺候,好言相侍,利用兒子,到主動出擊,跟蹤伏擊,運用公檢法,給婆婆下馬威。很顯然,她根本不是馬學武的對手。發現馬學武偷情時,她痛苦得萬箭穿心。但很快就能爬起來,揩乾眼淚,拾掇自己,並用巧計獲得電話號碼。丈夫死了,沒有給她留下一個字。她卻一滴眼淚沒有掉。雖不明所以,卻毫不為迷信所迫,馬上勵志撐起一片天。試問這在當代人裡面有多少能夠做到。底層勞動人民需要辛苦地勞作方能果腹,通過這些生命的歷練,他們的血液里骨骼里都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努力來爭取生命的權力和尊嚴(這在李寶莉和小景的對話裡可以看出,李寶莉對於用體力掙錢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踏實,自在和自信)。同時,被活生生的殘酷現實逼迫著追逐著的他們,每分鐘都活在現實里,紮在泥土中,沒有時間和空間來奢侈地做馬學武式的幻想,馬學武式的逃避。例如被丈夫以死拋棄後,她第一時間就檢查存款。生活的苦難和艱辛給了她一種不認輸,不信命,不放棄的性格。影片的後半部也被她的強大的意志力支持,「要撐起這個家,不能讓它散了」,一切為了兒子(顯然她的百般討好也似乎遇到一堵無形的牆壁)。她的堅持和勇敢,卻每每能夠讓她渡過生命的種種苦難,仍然充滿勇氣,依然心地善良,情真意切,不改初衷。她高揚了人性的光輝,萬丈光榮。
可是,一切都走向了她願望的反面。馬學武沒有拴住,不留一字,永遠離開,卻久久陰魂不散。萬沒有想到她一往情深,含辛茹苦培養的兒子,會那麼決絕地背叛,要和她一刀兩斷。她還是不服不屈。可是,居然這兩件事非但有關聯,而且都直接歸咎於她。恍如晴天霹靂,她的整個世界,以及她所信賴,依賴,為之奮鬥的價值(拴住丈夫,為了兒子)瞬間崩塌了。眾叛親離,她失去了和這個世界的所有情感聯繫和寄託。她拼命地逃離這種天崩地裂,黑白顛倒的現實,來到了江邊,走投無路,莫知所往。可是,逃無可逃,一群慶生的孩子又把她硬生生拉回到了現實。這時,曾經坑了她的生活,醍醐灌頂似的教會了她共情,她似乎明白了馬學武當初的走投無路情歸何處,以及來到江邊時的淒悽惶惶,她終於也意識到了孩子的惶恐和疏離毀壞了他童年的快樂。
許多人在生命的早期都會不期然遭遇一些情感的挫折和傷害。當他們能夠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們就變成了一往無前的鬥士,一定要爭一個勝負得失,用來補償從前的缺失。那些爭名逐利,蠅營狗苟,那些狼奔豕突,好強鬥勇,那些不甘掙扎,貪心不足就是為了證明一件事:我是好的,我是值得的。李寶莉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梅花香自苦寒來,最終她學會了和解,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她意識到,那些拼命爭取的高低短長,那戲武斷評判的高貴貧賤和那些斤斤計較的強妄態度,恰恰傷害和扭曲了人生,恰恰侷限並喪失了自我。於是,她終於學會了放棄爭輸贏,並接受人生和自己的不完美。這些不完美,就像收留她的建建那樣有過去,有缺陷,有反覆。人生,或者就像建建的破車那樣吼得響,開得慢,常常會熄火,還得要自己下來推一把,方能收拾精神,重新上路。這是李寶莉的了悟,也是李寶莉的救贖。
婆婆 – 影片場景情感價值的調節功能
• 影片場景的動力在與對於觀眾而言的情感價值的變化。而對觀眾而言情感價值的變化,取決於觀眾對於主人公的移情,即對主人公自覺和不自覺願望的理解和關心。而婆婆是影片情感價值的調節器。在影片的前半部,由於李寶莉的需求是奪回丈夫。婆婆成了她實現願望的重大阻礙,觀眾的移情尚在李寶莉這邊。但是,李寶莉的強勢,蠻不講理對比婆婆的委曲求全,可憐和被逼出走,婆婆成了弱者。觀眾的同情心總是偏向相對的弱者。於是觀眾的同情中心開始偏向婆婆而非李寶莉。可畢竟影片同情的中心需要回到李寶莉身上,下半部影片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來轉移同情的中心。
• 第一個場景:李寶莉開家長會:她那勞工身份和粗線條性格與現場的很不協調,婆婆又發不讓她來的牢騷。第二個場景,李寶莉回到家裡,低聲下氣地求兒子同她說話。這裡充分體現了愛使人渺小這句話。這時,兒子的莫名呵斥,婆婆又助威地數落她沒文化。於是,李寶莉和兒子,婆婆,以及週遭環境的關係顛倒了,李寶莉成了徹底的弱者,好讓觀眾改變同情的中心。接著,影片馬上用兩個場景來間接歌頌李寶莉。一個是小景和兒子談,母親有多不容易了。一個是老師斥責學生,扁擔的兒子年年考第一、
• 於是我們重新開始同情李寶莉,我們了解她的願望是儘可能創造好的生活條件,幫助兒子讀書,並且贍養婆婆。我們也了解李寶莉一個不自覺的願望,即消弭與家人的隔閡,重新獲得情感的慰藉和找回愛。 但每每這個不自覺的慾望,都遭遇了婆婆的打擊。她說給孩子買點好的,婆婆說這個還用你說。她關心孩子學習,婆婆說她沒文化。她問婆婆借錢,婆婆藉機逼她把房子過戶。她照顧孩子高考,婆婆說她礙事趕她走。最後婆婆生病還間接造成了她和兒子的誤會,以及孩子和建建的衝突。
• 這些段落里,婆婆和建建的作用是類似的,即讓觀眾坐情感價值的過山車。每每李寶莉在與孩子/婆婆的關係上似乎取得了一點進展,有所融洽,情感價值從負到正,婆婆馬上澆一桶冷水,情感價值轉而從正到負。每每李寶莉和建建的關係上似乎取得了一點進展,李寶莉長期缺失的對愛的渴望有所復甦,情感價值從負到正,建建又嘴賤破壞殆盡,價值從負到正。
• 婆婆最後開始理解和同情李寶莉,並為她的遭遇惋惜。這裡,婆婆的角色起到了反襯的功能。如前所述,當一個人通過了解,把對別人的負面印象漸漸轉向正面的時候,是最令人信服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婆婆的轉變反襯了李寶莉人性之美如何水滴石穿,撼動人心。
小景 – 影片的敘事功能
• 小景在影片中主要承擔是敘事功能。她一出現,就引發了李寶莉的痛苦流涕,無助無措 。這和李寶莉前一個場景裡面的強勢和控制欲呈現出鮮明的對比。頓時讓我們對李寶莉改觀,從強到弱的反差和對比,讓觀眾開始建立移情。在李寶莉發現丈夫出軌後,萬箭穿心地痛苦不能自己時,這種移情進一步增加。 當然,觀眾本身的道德價值觀就多半不支持出軌。
• 李寶莉每次遭遇變故後,小景都要來出謀劃策,順便感慨一番。對於情節既有推動,又有一種意義上的概括和昇華。小景給李寶莉出的第一個妙計,把老公拴住,直接導致影片上半部份的動力和故事脊椎。小景給李寶莉揭示萬箭穿心的秘密,李寶莉不信命,發誓要撐起家,直接導致影片下半部的動力和故事脊椎。
• 上半部里,小景上門進行調解時,和李寶莉的對話,點出了李寶莉的身世,也間接解釋了李寶莉婚姻不合的原因,對於影片的人物塑造,情節動力起到了關鍵性的揭示作用,可以說是一月照萬川。
兒子 – 撐起影片後半部的負面力量
• 許多人詬病兒子的角色過於臉譜化,單一化。這裡不免要多塗幾筆。在小景上門調解的同一個場景里,兒子也表明了明確偏向父親,討厭母親的態度,為後面的情節進行了伏筆和鋪墊。
• 在後面的影片中,對於兒子的態度,進行了不厭其煩的反覆展示,鋪墊,並有了一個長達5分鐘的閃回,用來渲染最終的母子衝突,就是要建立兒子反叛態度的合理性。
• 孩子害怕並疏遠易怒暴躁的母親,和爸爸親是正常的狀況。青春期的孩子易衝動,母親長期不在身邊,聽由自己印象,想像,和奶奶的灌輸,產生憎恨和背叛,其思維不成熟,歸因偏頗單一,也是正常,無可厚非的。
馬學武真可謂是「冷暴力不合作」運動的集大成者。他的不合作是徹底和廣泛的,體現在:
• 他用各種藉口性冷淡,拒絕行房(影片開頭的場景)(這和偷情時的急不可耐和淫聲蕩漾形成極強烈的對比)
• 非語言行為上的不合作:他在家時成天神情木訥,行動遲緩,目無焦點,魂不守舍(這和他與同事談笑的眉飛色舞形成極強烈的對比)
• 肢體語言上的不合作:拒絕與李寶莉碰杯(這是影片的主題性畫面,後來在給兒子高考慶功的飯桌上再次出現這個畫面,這回拒絕與李寶莉碰杯的是兒子,但冥冥中好像馬學武借屍還魂)。對於李寶莉的卑躬屈膝,刻意迎奉,用轉身脫襪和關門來抵抗和拒絕。
• 拒絕言語與意圖的交流:體現在接母親來家裡住這件事上,馬學武僅僅稍作象徵性地表示,便如他偶爾施捨給李寶莉的幾下抽動一樣,很快就偃旗息鼓。其實他還真沒有同李寶莉交流和表達自己意圖的意願,就如他說的,房子是我的,要接老娘住,你甭管。即便是死,他也頑固地不留給李寶莉一個字。
• 完全拒絕情感的交流:例如對於李寶莉的情緒爆發,既不安慰也不面質,僅在躲在洗手間捏緊拳頭,做象徵性地反抗和發洩。(可能歷來如此)
• 馬學武的絕招應該是一種長期慢性且非常微妙的不合作:例如對於李寶莉與搬運工人錙銖必較,對孩子的粗燥管教,他均暗渡陳倉地懷柔和輕描淡寫地破壞,並藉此很輕易地佔據道德高地,博取同情好感。
相比李寶莉他確實屬於一個更有文化的階層。但他那富餘的文化和智力僅僅足以讓他一次次地逃離現實,耽於幻想。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對於生命怠惰的人。他把對於生命的種種失望轉為無處發洩的壓抑,泛化為一種缺乏行動意志的抑鬱和幾近絕望。面對生活的失望和不如意,不順心,面對著受本身文化水平和生活環境限制的李寶莉的種種缺點和不足,他也許沒有一刻想到自己可以試著介入,試著改變。恰恰相反,他的唯一救命稻草就是精神上的逃離和情感上的隔膜。他好像是生活的局外人,邊緣化的妄想者。促使他逃離現實的驅力如此之大,足可以使他把所有的情感,慾望,心力,正面意義和理想化均賦予他藉以逃離的對象。例如:
• 當李寶莉守在家中,想用溫柔和熱忱,甚至搬出孩子做救兵試圖挽回婚姻的時候,他毫不在意地選擇繼續找藉口加班,並和同事大肆吃喝,談笑風生,得意忘形(可以想見其他晚歸的夜晚)。
• 當李寶莉試圖進一步努力把他拴在身邊的時候,他「升級」了他的逃離,「事先通知」地與同事開房。
• 當李寶莉試圖利用東窗事發的道德羞恥感來進一步「罩著他」的時候,他又搬來救兵,讓老娘與他們合住,也好繼續避免直接面對李寶莉的壓迫。
• 當李寶莉發現了他的意圖,並產生激烈言語衝突後,他又再一次選擇逃離,試圖從情人那裡獲得想像中慰籍,並維持一種曖昧,以便繼續他精神和情感的逃離。可縱他苦情西施,痴話連篇,無奈別人卻早已齣戲,神情泰然,過(吃)得蠻好。他終於發現當他賦予了每次逃離太多的理想化和美好時, 如此的一相情願恰恰別人無法負載,而終究要自己承受失重失落的。
• 當他得知自己下崗時,終於覺得無路可逃了。因為下崗會逼迫他回家,喪失一切逃離的藉口。下崗會讓他在李寶莉面前更加抬不起頭,毫無翻身希望。而他唯一的情感出口也如雪景融化後的泥濘,一片狼藉,不堪回首。於是,他寧願懦弱地死也要逃離他不想面對的現實。在這裡,死是容易的,而生恰恰是艱難的。想像是容易的,而實際常常令人不堪。
人就是這樣,當我們學會想像和做夢後,一旦遭遇挫折和傷害,很多時候就如馬學武一樣活在自己的想像里,用理想化的曖昧代替直面現實。用各種積極的奔忙,來閉鎖禁錮自己的人生,卻不期然成了自己生活的破壞者和對他人冷暴力的施予者。每個人身上都有馬學武的影子,只是生活不是電影,它不會把你逼到走投無路,只會讓你在沉默中漸漸迷失,漸漸萎靡。
救貓咪 - 影片的移情工具
所謂「救貓咪」場景是指:當我們遇見主人公時,他必需要做一些讓我們喜歡上他的事情。通過救貓咪場景,我們完成了對於主人公的移情,從此開始關心她的命運,想他所想,急他所急,漸漸被影片牢牢地吸引。從某種程度上,建建和何嫂子都是李寶莉的貓咪。何嫂子和建建都先後是她關心和照顧的對象。從中可以反映出,李寶莉作為草根,對於其他底層勞動人民有著一種發自內心,自然流露的同情,善意。就像襪子店老闆對她冷嘲熱諷中透露出的為她擔心。但李寶莉與眾不同之處在與她的同情善意會轉化為主動關心和照顧的行動,且不計利害。
在影片的前半部,每當情節出現她暴烈的脾氣和不近情理的苛責後,會立即插入一個救貓咪的場景。維持觀眾對於李寶莉的移情。第一次救貓咪是對於何嫂子生意的照顧,甚至擋風遮雨。第二次救貓咪是得知建建被抓時,流露的對於建建安危福禍的關心和擔心(這時候的表情是微皺眉頭)。而且,這些救貓咪的場景在影片後半部不斷髮展。李寶莉擔心建建釋放後的出路,擔心他重操舊業,擔心打架鬥毆的是他,每次都如此輕蹙雙眉。李寶莉甚至還關心他收帳是否吃虧:只換了個破麵包車,關心他住得是否寒酸,關心他喝醉酒掉到溝里。李寶莉救貓咪之心從不改其衷或輕易受挫,而投入金錢和情感投入的代價也越來越大。一個人做一次好事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這樣的救貓咪次情節對於激發觀眾的移情,有著累加和疊加的效果。影片這樣安排是非常巧妙的。從社會心理學來看,對於一個人初期印象較差,隨著逐漸的了解,印象轉好,這樣的對比和反差對於人的心理衝擊力是最大的,勝過一直印象很好。於是,觀眾移情的程度就不斷增強,直到頂點。相比何嫂子,李寶莉甚至顯得更能吃苦,更會做扁擔生意。但何嫂子的性格比較平淡,很難進一步反襯李寶莉的性格。何嫂子的惟一敘事功能就是調侃了陰盛陽衰(這在影片中和生活中無疑都是事實)。於是,在何嫂子次情節結束(在一次忍受婆婆逼迫和揶揄的,代價重大的救貓咪行動中達到高潮)後,建建的次情節便漸入高潮。
建建 – 一個自我擊敗的人,李寶莉的一面鏡子
建建正如他自己所說是一個嘴賤的人。想必他的真情曾遇到過持久的傷害,在他內心深處產生了恐懼和巨大的羞恥感。於是,每當他要表示善意時,或者產生與人接近的願望時,那種對於傷害的回憶和羞恥感就條件反射般地湧到心頭。從而,他發展了一套自我擊敗的人生策略:既然多情總被無情傷,那麼在你還沒有傷害我之前,我就先發制人,先無情地攻擊你,這樣我就可以避免被傷害:
• 出獄回來遇到李寶莉的主動關心,他明明有些觸動,卻說,怎麼怕我嗎?
• 邀請李寶莉去看他的貨運站,本來很熱情,他非要加上一句,你又不能給我帶來生意,你個扁擔。
• 在誘姦李寶莉後,他明明想和她約會,卻莫名其妙發揮了一大段:現在的人都很隨便,做完了跟沒事一樣。
• 李寶莉去探望他,幫他收拾屋子,他明明感激,卻推託說,我又沒有請鐘點工。
• 李寶莉弄傷了他,去賠錢道歉。他試圖表示不想談錢,不想見外,卻說成我睡了你也沒有吃虧,你怎麼倒貼我錢。
• 當他從李寶莉的委屈爆發中意識到她的真情流露時,他內心應該有所感動,卻明確冷冷地說本來就沒有當真,不要裝得很有情。
• 當然,在影片的最後,他終於第一次說出了主動關心的話(有什麼打算),自我表露的話(我就是嘴賤),毫不猶豫擔當的話(老子不怕),再沒有加上一句什麼。
其實建建活脫就像李寶莉的一面鏡子:他們的父母可能由於生活的苦難和重擔忽略了他們,可能因為本身性格和脾氣乃至文化素養的侷限對他們的情感需求置之不理,或者甚至對他們施加了言語乃至肢體的暴力。於是,他們生活在一種強大的不安全感中。他們是如此地需要愛,渴望愛,想表達愛,卻因為生命早期種種的共情挫敗和巨大羞恥感,演出成了一種怒氣和攻擊欲。他們沒有掌握愛的語言。他們粗暴地對待別人,也許恰恰是因為他們曾經被如此地粗暴對待。記得在搬家夫妻衝突中,李寶莉惡狠狠地罵馬學武:生得賤。也許她也被這樣責罵過。
李寶莉- 少有人能做到的堅韌,剛強和容忍
對於李寶莉而言,早年共情失敗的影響是巨大的。她真的缺乏共情的能力,即為別人設身處地設想的能力。李寶莉只能生活在她自己的現實框架和習慣思維裡面,無法哪怕一點點地跳脫出來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她說了勞心的事情她不行,她做能做到最勞心的事情,就是以己度人:
• 她也許生在一個錙銖必較,睚眥必報的環境裡,這既培養了她能為不多的報酬任勞任怨的態度,卻又帶給她為蠅頭小利斤斤計較的小市民思維定勢。她怎麼也不能共情搬運工人的辛苦,卻只能以己度人,反感他們不如自己任勞任怨,貨真價實,價格公道,錢貨兩清,更反感他們就地起價,懶惰不負責還貪她家小便宜。
• 她能感受到丈夫從當初跪地發誓對她好,到不合作冷暴力的變化,而自己心意似乎不變,為此憤懣委屈不已。但她卻感受不到自己優勢意識和強勢態度給丈夫帶來的委屈,受挫和不斷逃離。所以她強烈反對小景的警告。
• 對於丈夫百般拒絕房事或者敷衍了事,是因為夥計不給力或者第二天要搬家等藉口,她都木知木覺地相信,直到她發現丈夫和情人發生姦情時的急迫慷慨,春聲蕩漾,對比後方才覺悟深深的失落和自尊的貶抑。
• 她顧及兒子,沒有去抓姦在床,希望通過第三方外力把偷情的丈夫給輕易奪回來。卻沒能設想這麼做可能給丈夫帶來的事業和感情上的傷害。
• 她好不容易通過外力和自己的「寬大」把丈夫服服貼貼地抓到身邊頤指氣使,不料丈夫搬出老娘來橫插一槓。她氣急敗壞,怒火中燒,惡言相向,冷嘲熱諷,卻無法設想這麼做給丈夫和婆婆帶來的嚴重傷害。
• 她只知道拼命給孩子創造好的條件,把人生的一半奉獻給了孩子,卻體會不到自己的惡言厲吼,粗暴對待,缺乏共情的關心和缺乏陪伴,給孩子帶來的恐懼和疏離,以及丈夫,婆婆的態度對於兒子的負面影響。
• 當她知道丈夫自殺後,她只認為丈夫是受不了下崗的刺激自殺的。所以,她又以己度人,說自己下崗了,不還活得好好的。她想不清白,看不起丈夫的懦弱,更不能理解丈夫對她一言不發,甚至覺得丈夫有點對不起她。
反過來,曾經飽受損害和侮辱的李寶莉,對於人情冷漠,甚至是粗暴對待,卻有著深厚的容忍力和超強的耐受度。對於丈夫拒絕敬酒,李寶莉自我調侃說,今天高興不和你計較。對於婆婆一次次的言語相逼,李寶莉每次都忍了,默默無言。也許冷漠的環境讓她習慣了,她從不認為自己不值得接受這些委屈。相反,對於早年愛的缺失,她恰恰希望不惜一切代價來換取這份愛,為此她寧願扮演一個犧牲者和照顧者的角色而甘之如飴,矢志不渝。
正因為她無法共情,影片前半部馬學武要求離婚,偷情,自殺成為了她人生的三個突如其來,莫名其妙,毫無抵抗,衝擊巨大的大災難。但是,與馬學武不同,李寶莉決不逃避,打倒了再爬起來,勇敢面對。她有著底層勞動人民特有的堅韌和剛強,以及強大的意志力。影片的前半部在激勵事件(馬學武提出離婚)後,由她強大的意志力貫穿。馬學武提出離婚,她痛哭過就去找小景出主意,在小景的勸告下,用不斷升級的各種辦法把馬學武拴在身邊。例如從苦苦守候,好生伺候,好言相侍,利用兒子,到主動出擊,跟蹤伏擊,運用公檢法,給婆婆下馬威。很顯然,她根本不是馬學武的對手。發現馬學武偷情時,她痛苦得萬箭穿心。但很快就能爬起來,揩乾眼淚,拾掇自己,並用巧計獲得電話號碼。丈夫死了,沒有給她留下一個字。她卻一滴眼淚沒有掉。雖不明所以,卻毫不為迷信所迫,馬上勵志撐起一片天。試問這在當代人裡面有多少能夠做到。底層勞動人民需要辛苦地勞作方能果腹,通過這些生命的歷練,他們的血液里骨骼里都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努力來爭取生命的權力和尊嚴(這在李寶莉和小景的對話裡可以看出,李寶莉對於用體力掙錢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踏實,自在和自信)。同時,被活生生的殘酷現實逼迫著追逐著的他們,每分鐘都活在現實里,紮在泥土中,沒有時間和空間來奢侈地做馬學武式的幻想,馬學武式的逃避。例如被丈夫以死拋棄後,她第一時間就檢查存款。生活的苦難和艱辛給了她一種不認輸,不信命,不放棄的性格。影片的後半部也被她的強大的意志力支持,「要撐起這個家,不能讓它散了」,一切為了兒子(顯然她的百般討好也似乎遇到一堵無形的牆壁)。她的堅持和勇敢,卻每每能夠讓她渡過生命的種種苦難,仍然充滿勇氣,依然心地善良,情真意切,不改初衷。她高揚了人性的光輝,萬丈光榮。
可是,一切都走向了她願望的反面。馬學武沒有拴住,不留一字,永遠離開,卻久久陰魂不散。萬沒有想到她一往情深,含辛茹苦培養的兒子,會那麼決絕地背叛,要和她一刀兩斷。她還是不服不屈。可是,居然這兩件事非但有關聯,而且都直接歸咎於她。恍如晴天霹靂,她的整個世界,以及她所信賴,依賴,為之奮鬥的價值(拴住丈夫,為了兒子)瞬間崩塌了。眾叛親離,她失去了和這個世界的所有情感聯繫和寄託。她拼命地逃離這種天崩地裂,黑白顛倒的現實,來到了江邊,走投無路,莫知所往。可是,逃無可逃,一群慶生的孩子又把她硬生生拉回到了現實。這時,曾經坑了她的生活,醍醐灌頂似的教會了她共情,她似乎明白了馬學武當初的走投無路情歸何處,以及來到江邊時的淒悽惶惶,她終於也意識到了孩子的惶恐和疏離毀壞了他童年的快樂。
許多人在生命的早期都會不期然遭遇一些情感的挫折和傷害。當他們能夠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們就變成了一往無前的鬥士,一定要爭一個勝負得失,用來補償從前的缺失。那些爭名逐利,蠅營狗苟,那些狼奔豕突,好強鬥勇,那些不甘掙扎,貪心不足就是為了證明一件事:我是好的,我是值得的。李寶莉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梅花香自苦寒來,最終她學會了和解,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她意識到,那些拼命爭取的高低短長,那戲武斷評判的高貴貧賤和那些斤斤計較的強妄態度,恰恰傷害和扭曲了人生,恰恰侷限並喪失了自我。於是,她終於學會了放棄爭輸贏,並接受人生和自己的不完美。這些不完美,就像收留她的建建那樣有過去,有缺陷,有反覆。人生,或者就像建建的破車那樣吼得響,開得慢,常常會熄火,還得要自己下來推一把,方能收拾精神,重新上路。這是李寶莉的了悟,也是李寶莉的救贖。
婆婆 – 影片場景情感價值的調節功能
• 影片場景的動力在與對於觀眾而言的情感價值的變化。而對觀眾而言情感價值的變化,取決於觀眾對於主人公的移情,即對主人公自覺和不自覺願望的理解和關心。而婆婆是影片情感價值的調節器。在影片的前半部,由於李寶莉的需求是奪回丈夫。婆婆成了她實現願望的重大阻礙,觀眾的移情尚在李寶莉這邊。但是,李寶莉的強勢,蠻不講理對比婆婆的委曲求全,可憐和被逼出走,婆婆成了弱者。觀眾的同情心總是偏向相對的弱者。於是觀眾的同情中心開始偏向婆婆而非李寶莉。可畢竟影片同情的中心需要回到李寶莉身上,下半部影片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來轉移同情的中心。
• 第一個場景:李寶莉開家長會:她那勞工身份和粗線條性格與現場的很不協調,婆婆又發不讓她來的牢騷。第二個場景,李寶莉回到家裡,低聲下氣地求兒子同她說話。這裡充分體現了愛使人渺小這句話。這時,兒子的莫名呵斥,婆婆又助威地數落她沒文化。於是,李寶莉和兒子,婆婆,以及週遭環境的關係顛倒了,李寶莉成了徹底的弱者,好讓觀眾改變同情的中心。接著,影片馬上用兩個場景來間接歌頌李寶莉。一個是小景和兒子談,母親有多不容易了。一個是老師斥責學生,扁擔的兒子年年考第一、
• 於是我們重新開始同情李寶莉,我們了解她的願望是儘可能創造好的生活條件,幫助兒子讀書,並且贍養婆婆。我們也了解李寶莉一個不自覺的願望,即消弭與家人的隔閡,重新獲得情感的慰藉和找回愛。 但每每這個不自覺的慾望,都遭遇了婆婆的打擊。她說給孩子買點好的,婆婆說這個還用你說。她關心孩子學習,婆婆說她沒文化。她問婆婆借錢,婆婆藉機逼她把房子過戶。她照顧孩子高考,婆婆說她礙事趕她走。最後婆婆生病還間接造成了她和兒子的誤會,以及孩子和建建的衝突。
• 這些段落里,婆婆和建建的作用是類似的,即讓觀眾坐情感價值的過山車。每每李寶莉在與孩子/婆婆的關係上似乎取得了一點進展,有所融洽,情感價值從負到正,婆婆馬上澆一桶冷水,情感價值轉而從正到負。每每李寶莉和建建的關係上似乎取得了一點進展,李寶莉長期缺失的對愛的渴望有所復甦,情感價值從負到正,建建又嘴賤破壞殆盡,價值從負到正。
• 婆婆最後開始理解和同情李寶莉,並為她的遭遇惋惜。這裡,婆婆的角色起到了反襯的功能。如前所述,當一個人通過了解,把對別人的負面印象漸漸轉向正面的時候,是最令人信服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婆婆的轉變反襯了李寶莉人性之美如何水滴石穿,撼動人心。
小景 – 影片的敘事功能
• 小景在影片中主要承擔是敘事功能。她一出現,就引發了李寶莉的痛苦流涕,無助無措 。這和李寶莉前一個場景裡面的強勢和控制欲呈現出鮮明的對比。頓時讓我們對李寶莉改觀,從強到弱的反差和對比,讓觀眾開始建立移情。在李寶莉發現丈夫出軌後,萬箭穿心地痛苦不能自己時,這種移情進一步增加。 當然,觀眾本身的道德價值觀就多半不支持出軌。
• 李寶莉每次遭遇變故後,小景都要來出謀劃策,順便感慨一番。對於情節既有推動,又有一種意義上的概括和昇華。小景給李寶莉出的第一個妙計,把老公拴住,直接導致影片上半部份的動力和故事脊椎。小景給李寶莉揭示萬箭穿心的秘密,李寶莉不信命,發誓要撐起家,直接導致影片下半部的動力和故事脊椎。
• 上半部里,小景上門進行調解時,和李寶莉的對話,點出了李寶莉的身世,也間接解釋了李寶莉婚姻不合的原因,對於影片的人物塑造,情節動力起到了關鍵性的揭示作用,可以說是一月照萬川。
兒子 – 撐起影片後半部的負面力量
• 許多人詬病兒子的角色過於臉譜化,單一化。這裡不免要多塗幾筆。在小景上門調解的同一個場景里,兒子也表明了明確偏向父親,討厭母親的態度,為後面的情節進行了伏筆和鋪墊。
• 在後面的影片中,對於兒子的態度,進行了不厭其煩的反覆展示,鋪墊,並有了一個長達5分鐘的閃回,用來渲染最終的母子衝突,就是要建立兒子反叛態度的合理性。
• 孩子害怕並疏遠易怒暴躁的母親,和爸爸親是正常的狀況。青春期的孩子易衝動,母親長期不在身邊,聽由自己印象,想像,和奶奶的灌輸,產生憎恨和背叛,其思維不成熟,歸因偏頗單一,也是正常,無可厚非的。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