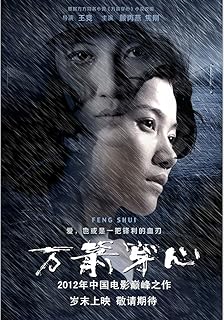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2-11-25 01:18:20
生活邏輯重壓下的底層
這不算是個影評,只是個小說結合電影文本的內容分析,或者只是篇讀後感般的議論文。
文本對比:
看電影前突擊讀完了原作,湖北作協主席方方的六萬一千多字、寫於2007年的中篇小說,兩到三個小時能讀完。文本對比如下:
馬學武:小說中描寫為大專學歷,原為技術員,然後當上了廠辦主任,電影中萬小景在李寶莉家吃完飯聊天時的情節:萬小景說李不該總說馬是鄉下人,都是一家人了嘛。這台詞間接介紹了馬學武的「鳳凰男」身份。原著中說到有廠長是他的同學,有意要提拔他,於是走入行政崗。因為偷情時間被曝光,被貶稱為技術員,後來因為此事名聲不好,成為工廠下崗首先被裁掉的人。小說中的馬學武也很軟弱,但並不似電影裡刻畫成那樣。
馬學武父母:小說中敘述為鄂西某市的中學老師,退休後房子被拆,聽家鄉馬學武表哥的意見,來到武漢投靠兒子。片中只安排出現了馬母一人,其實老兩口一直都有戲份,且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後來孩子在武漢工作掙錢了以後,在武昌的湖邊買了別墅給二老住,為了湊買別墅的首付,小寶(馬文昭)讓李寶莉離開,要賣掉房子湊錢。小說中馬家二老和李寶莉的矛盾很尖銳,但電影做了溫和處理。
李寶莉:小說中交代了是下崗職工,下崗後到漢正街一個賣襪子的老闆處打工,小學學歷。因為長得好看很多人追求,她看中了馬學武的學歷高,人長得也不錯,在馬學武追求下和他結婚。結婚前閨蜜方小景介紹自己的「乾哥哥」建建給李寶莉,但李寶莉看不上,小說開頭李萬二人開玩笑時李說:「就要找個學歷高的人,將來生的孩子也聰明,能沾上光。」小說中的李寶莉八面玲瓏,特別會說話能幹活,在漢正街的特別有號召力,有點《生活秀》裡吉慶街「一姐」來雙揚的意思,電影中將李寶莉刻畫地更加憨直和良善。
李寶莉父母和妹妹:這在電影中徹底被省略了,小說中交代了李家是武漢人,李寶莉父親原來是碼頭的,因為工傷內退,在巷口擺了個自行車攤;李母是個性格很強的人,因為自己貧下中農的身份,在文革時當過領導,改革開放後成為普通退休工人,卻是個很硬氣很能幹的人,李寶莉的性格大部份跟了她母親。小說中對李家貧寒的生活在開始就有描寫,後來李寶莉當扁擔時為了給孩子湊大學學費,幾次賣血被家母發現,後來沒辦法李寶莉去找家母借錢供孩子讀書,但發現父親已經是癌症晚期,於是沒有張口,李夫後來去世。李家另一個人物是李寶莉的妹妹,上了中專/職高,當了白領,小說開頭就出現了一次,其中交代她對自己的學歷有優越感,比較懶惰,衣服都是李寶莉幫著洗過一回。
萬小景:李寶莉的髮小,讀過高中,小說剛開頭就介紹了李萬二人的學歷。嫁了一個大款,大款在外面有很多女人,方小景和丈夫的感情名存實亡,只負責要錢花錢,李寶莉最最忠實和可依賴的朋友。
小寶(馬文昭):小說中記載他從小就很怕媽媽,因為媽媽總在訓斥爸爸,由於爸爸有文化,作為學生的他自然和爸爸更親近一些,後來馬學武跳江之後,他完全倒向爺爺奶奶一邊和李寶莉做對,三個馬家人欺負李寶莉,他以高分放棄去北大清華而報考了武大,他說因為怕李寶莉對爺爺奶奶不好,後來其工作後賺到錢,還在正月過年時去看了看外婆,李寶莉的媽媽,但是對李寶莉依然無情。
和馬學武偷情者:小說中寫成廠里打字員,電影裡設定為工會人員。眾所周知國企的工會是個閒差,管福利管活動,本身就不忙,認識廠里所有人,這樣也為兩人的姦情提供點邏輯合理性。
扁擔何嫂子:小說中沒有何嫂子兒子受傷李寶莉借錢的情節。
建建:從李寶莉結婚前就喜歡她,後來多了監獄,出來以後他母親得病,為了治療替某人蹲了10年監獄換來50萬給他母親治病,出獄後開了一個酒吧,沒有電影裡刻畫的那樣黑社會或者地痞流氓受保護費的情節,小說裡的他很文雅,從始至終都只是在表達對李寶莉的愛戀,到影片結尾也沒有上床或者後來李寶莉搬出來後和他在一起的情節。
相對小說中非常尖銳、讓人讀了以後揪心的矛盾來說,電影做了較為柔和的處理:馬家人(二老加上小寶)對李寶莉的百般刁難,冷落和漠視,集中體現在李寶莉為了何嫂子和地痞打架,腿被砍傷,養病時馬家老太生病,李寶莉不顧自己的傷勢去陪夜看護,自己反倒病情加重住院,但馬家人對此毫不領情。另一處為:李寶莉為了給孩子湊大學學費,不得已多次賣血,被萬小景發現不對勁,知情後萬小景盛怒之下罵了馬家二老,馬家的態度稍有緩和,主動把養老金給李寶莉當作孩子學費。
小說中的一個關鍵背景:李家父母,在影片中未出現。李父的匆匆出場和李母的硬氣、大氣和洞察世事,很多有道理的話都是馬母說出來的,如:她認為生活就憑自己的硬氣,無論物質條件如何,自己首先要硬氣。馬學武走後,她告訴李寶莉今後全憑一個「忍」字,凡事都是忍。後來李父彌留之際說自己最大的福分就是娶了李母為妻,李家的悲情戲份也比較有看頭。李父去世後,李母對李寶莉說:「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沒道理,而且每個人的道理都不同。當年我當革委會主任時,我覺得有道理,大家覺得沒道理,現在我生活這樣,我覺得沒道理,但別人覺得有道理。」小說和電影的中文名字叫《萬箭穿心》,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小說開頭部份,分到新房子的李寶莉高興地帶自己的父母在樓上看江景,結果李父說出了這句「萬箭穿心」的風水問題。小說中李寶莉因為這個說法而在做家務時生過氣。電影中此言則是安排給了萬小景,馬學武走後李寶莉和萬小景坐輪渡時萬小景說的。
階級
影片中時常會出現一個鏡頭:房屋密集的居民樓,看上去特別像居住條件緊張的香港特有的「屋村」,這就是李寶莉「萬箭穿心」的新房所在地。這套房是馬學武廠里分配給他的,是典型的工人階級居住區:空間擁擠、建築物色調和樣貌高度整齊劃一。另一個常見的鏡頭是漢口的一個大全景,層層疊疊的樓房和最遠處的長江、大橋,似有王安憶《長恨歌》小說開頭寫景的韻味。這兩個鏡頭在影片中多次出現,雜亂、層疊、密集,色調陰鬱,這實際上在預示這是一個關於底層人的故事。他們辛苦在城市謀生活,時代變動面前往往成為最脆弱的一部份。
電影的時代背景也鋪陳得清楚:香港武俠電視劇、漢正街上90年代的流行歌,人們的穿著方式,把故事發生的時間置於90年代,這剛好是李寶莉下崗後賣襪子、後來馬學武被下崗的大背景:90年代國企改革的下崗潮。馬學武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典型的社會主義大工廠、上下班時的自行車流、鐵路道口旁工人們吃著熱乾麵等著過去,他是工廠的普通技術員,在市場經濟之前是國家的主流入群,而他的工作和學歷,也在小說中有所提及,都是一個作為社會底層的小市民李寶莉所看中的。但李寶莉是武漢本地人,對馬學武這樣來自小地方的「鳳凰男」,她無疑在出身或城市的歸屬感上更有優越性,萬小景在電影裡對李寶莉的批評:「你早做麼事去了?他出軌之前你就要把他牢牢抓住,你之前對他不好才導致他今天這樣,你總是喊人家『鄉下人、鄉下人』,都是一家人了,說這個搞麼事?」
馬學武無論在小說中還是電影裡都被刻畫成一個高度軟弱、唯李寶莉命是從的妻管嚴。除卻李寶莉遺傳了李母的硬朗霸氣、馬學武文弱這些性格因素之外,社會原因是一個重要方面。李寶莉是武漢本地人,長得又好看,而且下崗之前也是工人階級,這些都對鳳凰男馬學武極有吸引力,而這現象背後的城鄉差距問題,直到20年後的今天,依然在人們的發展和婚戀問題上有不少的影響。從結婚到搬入新房,馬學武在性格霸氣的李寶莉面前忍了很多年,但在搬家後工人們說的一句「被這樣的女人罩著,你有再大的成就也是……」激化了馬學武心中的屈辱,當天晚上,他提出離婚。
離婚的問題實際上是兩人相對位置變化的表徵:此時的馬學武受領導的器重,已經由技術員升為廠辦主任,進入領導層,他的前景是光明的,社會階層的躍升讓他有了更多資源和更多選擇,恰恰外遇也就發生在此時,外遇實際上是馬學武社會階層上升帶來的紅利;此時的李寶莉則成為社會底層,早年下崗、小學文化程度的她只能去漢正街幫著賣賣襪子,在夫妻雙方的博弈的相對關係當中,李寶莉全面處於下風。李寶莉對此巨變應該並無深刻認識,在家中依舊對馬學武吆五喝六,這讓馬學武離婚的心思實際上越來越成熟。影片開頭馬學武對李寶莉求歡的排斥完全是這種問題在生活中的反映。
「萬箭穿心」這一話語的實際承載物毫無疑問是房子。新的房子是李寶莉在小說開篇歡天喜地的原由,也是此後劇情上演的舞台。90年代開始的住房商品化過程,本身就是中國全面進入市場化時代的最重要一方面,房子是人們參與市場競爭的資源,更是任何一個人在市場經濟的主舞台——「城市」當中安身立命的身份象徵。在用慣了「有臭味的公共廁所、共同的下水管道」的小市民李寶莉心目中,新房子和美好新生活是緊密勾連載一起的,因為房子是馬學武給這個家庭和自己的饋贈,李寶莉決心好好待馬學武(小說中開篇就有提及);同時,馬父馬母不請自來的行為,在李寶莉眼中實際上是局外人對自己美好新生活的粗暴瓜分,因此她對馬父馬母的排斥,實際上她對自己想像中美好生活的捍衛——但這種美好生活終究只是想像,更要命的是夫妻對未來的想像不同:馬學武厭倦了對自己呼來喝去的糟糠之妻,想要借自己事業的上升來送舊迎新,即便偷情後身敗名裂,他依然會去和偷情女子見面,可見他對李寶莉從內心的徹底決裂;李寶莉則希望在新屋帶來的物質改善當中繼續自己已經習慣了的、和馬學武以前的生活和溝通方式——夫妻同床而異夢,離婚或者決裂成為必然選擇。
李寶莉因為自身文化程度低,在和家庭其他兩個成員(小寶和馬學武)的互動中處於邊緣化境地。馬學武一直輔導小寶學習,小寶也親見母親對夫妻的種種呵斥,小寶自然和父親更親,而馬學武和李寶莉因為生活空間和階層慢慢拉開差距,所思所想除了家庭這方天地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交集。馬學武走後,李寶莉由於忙於生計更不能融入小寶的生活,因此隔閡日深。
除卻李寶莉自身,她背後「娘家人」也是她參與社會博弈的自身資源。正如小說中所描寫的,李家實際上是城市低層,他們住在使用公共水龍頭、公共廁所的街區,因傷內退的父親在巷口修自行車,因為時代轉變、原本在文革時期叱吒風雲的李母則成為新時代菜市場買魚的小商販,李寶莉的妹妹是個小白領,內心虛榮,看不上家人的做派。後來李父去世,家中更拿不出錢給小寶上大學,這一切都將李家定位在90年代社會激變當中地位下行的人群中,李寶莉也是這個下行人群中的一員,邊緣和弱勢的不言而喻。李家社會地位下行另一個表現即:萬小景在得知李寶莉為了謀生活而當了「扁擔」,氣憤的說:「你怎麼能幹那種下等人的事情。」的確如此,萬小景和李寶莉是髮小,都是之前的小市民,在他們眼中,「扁擔」這個活計是最低賤的體力活和下苦的差事——但李寶莉確實當了「扁擔」,李父也靜靜地去世了,這就是曾經的小市民在殘酷社會分層中下行成為下層階級的現實。
作為李寶莉「娘家人」的萬小景實際上是給李寶莉從物質到精神各方面支持最多的人。她的生活可謂是「感情不幸錢包幸」,大款老公和她之間已經沒有感情可言,老公在外面養著N個奶,萬的老公是個生意人,他實際上是市場經濟中的贏家,對性資源的充分佔有,只是其諸多勝利中的一方面。影片中還有個場景能和此呼應:李寶莉去給何嫂子錢,到了何嫂子住在扁擔專用的地方,這個地方原來是建建出租的,就在李寶莉和建建交談時,畫外音是叫床聲,鏡頭一轉,另一個屋裡的男扁擔們正在擠在一起看A片,社會底層的人們因為經濟上的潰敗,性資源極度缺乏,無法擁有正當的性權利,只能通過這樣意淫的方式解決,這無疑和萬小景老公是最好的對比:生活的對比,更是階層的對比。
這是一個關於女人的悲劇,更是一個訴說階級問題的文本。離婚,不僅是馬學武擺脫李寶莉「欺負」的唯一途徑,更昭示了社會地位逐漸上行的馬學武準備和李寶莉及李家日漸下行的社會階層決裂的意願。這實際上是大時代社會激變、階層劃分這樣殘酷現實的一個顯影:小家庭中的變動,反映的是社會大格局的變化。離婚所表徵的社會激變,是馬學武的悲劇和李寶莉此後痛苦人生的開端,更是這出人間悲劇的真正原因。馬學武因為被舉報嫖娼,前途幻滅,後來還因此而被下崗,曾經一切美好的東西化為烏有,他內心最為認同和看中的階層上升的途徑被堵塞,事業的失敗使得自己去擺脫這樣一個已經深深厭惡的家庭的可能性幾近為零,絕望中,他選擇自殺。一個男人,可能他最為珍視的東西未必是家庭,而是成就感,這不同於女人,和馬學武偷情的同廠女職工並未自殺就說明了這一點,她可以苟活,但馬學武卻接受不了,因為這種苟活會讓李寶莉對自己更加頤指氣使,卻又不同意與自己離婚,讓自己進入無期徒刑——而這間接證明了,男人的生活的全部意義,更依附於社會當中的相對地位、階級及其帶來的社會認同感。
性別
上段陳述中男女生活重心不同的說法,在女權主義者眼中可能是性別政治不正確的表現,但毫無疑問,《萬箭穿心》這小說還是電影的中心情節,其實是一個關於女人的悲劇故事。貫穿全片的主要人物毫無例外都是女人,李寶莉、萬小景(建建的角色在小說中從未單獨出現,完全是在萬小景、萬小景+李寶莉的場景中才會出現)、李母(這個重要角色是一個大時代轉變的簡介,在電影中並未表現)馬家的代表馬母(小說中始終和馬母同時出現的馬父在影片中刪掉,而作為馬家人的小寶,實際上只是一個馬學武靈魂附體的人,是一個小「馬學武」,體現的是馬學武+馬家二老的想法)、乃至作為女「扁擔」代表的何嫂子(小說中的何嫂子遠比電影中霸氣),都是這個文本的性別特徵。
如果這個故事的其他元素不變,而只是性別特徵改換以後會怎樣?在此做一個大膽的假設:工廠技術員馬學武因為事業平庸,自己為人又唯唯諾諾令人生厭,妻子離開(或絕望跳江或面臨誘惑拋棄家庭遠走高飛),他又不幸工傷致殘,下崗大潮中被國家無情拋棄,父母老家的房子被拆過來投靠(這是小說中的情節),他身無長物只好淪為漢正街的「扁擔」,一個人含辛茹苦供小寶成為高考狀元(期間小說中的賣血等情節不變),但小寶因為母親的離開十多年來一直和馬學武齟齬不斷,最終還是不原諒父親,於是馬學武成為一個佝僂蒼老、在漢正街上賣命的老「扁擔」……
這個故事怎樣?主人公仍舊是一樣的慘,但整個故事的悲劇性卻大打折扣,被李寶莉的故事的悲劇性甩出十幾條街。如果主人公是個男的,那麼這個故事多少會讓人讀出一點勵志的味道,反而成為「守得雲開見月明」的有點正面意涵的故事。作為男性的悲劇人物,這樣的「男扁擔」馬學武能慘得過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嗎?能慘得過余華筆下的福貴嗎?顯然不能。就算對故事進一步做改動,突出悲劇性:小寶不學好,成了少年犯,馬父馬母年老無錢治病孤獨地客死都市,馬學武為了解決生理需求去嫖娼結果染上了性病,身體崩壞,扁擔也幹不了了,於是在絕望和精神錯亂中死去……慘是夠慘,但這不同於悲劇性。悲劇不光是慘,還要能激發人的惻隱之心、同情心乃至悲天憫人的情懷——這方面,女性為主角天然能激發出人們的這種感受,這是被社會角色所規定了的男女的根本不同。
在影片的影視語言當中,同是扁擔,男扁擔很少以悲情和苦痛的表情示人,他們大多抽菸開玩笑,臉上多少有點賣力氣人的暢快和大條。底層男性們心情低落或者面臨困境時,打罵老婆,喝頓大酒、和朋友們哭得稀里嘩啦,大罵社會或者和別人打一架,都多少能紓解心頭的不快;在生活方面,他們可以底層人的無賴姿態隨便調戲女性,就像阿Q的行為,他們可以看A片(A片完全是男性視角,主要受眾亦是男性),或者乾脆去嫖娼、隨意支配自己的身體……男性在社會當中的憤懣和失望是有諸多出口的,他們也擁有更多的機會,他們抗打擊程度更強;女性恰恰相反,同樣底層的女性,並不能通過男性的方式發洩不快,她們解決生理壓抑的手法也不能像男性那樣隨意和方便,她們無法打罵老公和孩子,無法像男性一樣對社會施以惡意。如果說底層人承擔著這個社會最苦痛和最悲慘的境遇,那麼底層中的女性,無疑是最具悲劇性的群體,正如同孔乙己似乎永遠比不上祥林嫂更悲劇。
本片的英文名字叫「fengshui」,即「風水」,「萬箭穿心」也取自風水理論。但實際上,無論在小說里還是電影中,「萬箭穿心」的情節出現都不超過兩次,而且李寶莉對此還並不服氣,她偏認為是「金光萬丈」。李寶莉不信風水,但她信命。她偶爾會說自己的命格不好,她跟小景借錢時說「每個人都是來世上還債的,借的越多下輩子就還人家越多」之類的宿命論的話,當李寶莉無法面對和無法解釋自己的生活的窘境時,只能拿著這種說法來搪塞。風水本事堪輿之學,將居住和建築問題和人生運到的宏觀事務聯繫起來,這無疑是中國人對生命的一種認識,而且我也不懷疑製片方不願用《一個女人的悲劇》之類的大俗話或者「萬箭穿心」根本無法用英文翻譯的初衷,他們用了「fengshui」這樣一個外國人看來充滿東方神秘主義意蘊的詞語,因為其很難解釋,所以無法辯駁——當中國人遇到一些無法解釋和處理的問題時,會用「命」「緣」「運」等等本身就沒有確切含義的概念來加以解釋,一個「fengshui」,就概括了李寶莉的悲劇,這似乎是在說:李寶莉的悲劇是無法解釋的,她對自己的命運無從把握,因為這一切都是「fengshui」這樣的宏大因素在起作用。
看畢方方的《萬箭穿心》,我想起另一個武漢作家池莉的中篇《生活秀》,兩篇同由武漢女作家寫出的漢味故事,反映的也都是90年代中國市場進程和拜金潮席捲下的大時代裡的小人物人物故事。《生活秀》裡的來雙揚風華絕代、精明強幹,她生意紅火、巧妙地爭回房產、擺平家裡的糾紛,但她在卓雄州身上渴望實現的感情救贖卻最終破滅,是一個從詩意救贖的可能到殘酷的生活邏輯重壓之下詩意無奈消解的過程,但這不是悲劇,只是多元生活中本身的一種可能性;《萬箭穿心》實則是一個女人的悲劇,這個女人從頭到尾都沒有綻放過、炫目過,她在底層社會終其一生,她眼裡現實的生活邏輯是第一位的,她對更好生活過於急切的熱望讓她粗暴地表達自己,她並沒有溫柔地對待丈夫和孩子,為了維持正常的生活邏輯不影響小寶考學,小說中她始終也不敢接受建建的愛。如果說來雙揚除了後來未遂的感情之外,真的在市井的世界吉慶街里活出了女人的精彩,相比之下李寶莉殊為可悲,她有底層人的粗獷大條、生活所迫斤斤計較,「美」在她的身上實際是缺席的,這讓丈夫遠離他——在愛情(馬學武要離婚、出軌、自殺)和家庭(小寶和他斷絕關係、馬父馬母對他形同陌路)徹底拋棄她之後,她真的一無所有。這實際上也反證了我之前提到的現象和觀點:馬學武自殺但偷情女未自殺,她雖然從此從工廠消失,但她並未因此失去家庭或重組了家庭。社會賦予兩性較為固化的角色讓家庭成了女性生活的極大支柱,來雙揚沒有愛情和一個不完全的家庭,這是她內心永遠無法紓解和渴望被救贖的,好在她有出眾的外貌、能力和生意支撐著她;沒有這些特點的李寶莉在被家庭邊緣化之後,悲劇性油然而生。
愛情和婚姻
李寶莉是個美女,小說中交代了她年輕的時候不乏追求者,即便她後來當了「扁擔」,因為打架受傷後休養了一段時間也恢復了美貌。她的美貌是她年輕時期最大的資本,加上她潑辣爽利的性格,大氣能幹(電影中沒有很好地表現出這點,是個遺憾),她也算是個拿得出手的「草莽巾幗」。她小學畢業,很小的時候就跟著母親賣魚賣菜,後來當了一段短暫時間的工人之後下崗去賣襪子,因此李寶莉生活的核心就是「現實的生活邏輯」,草根出身讓她將現實利益擺在第一位,發小萬小景當年介紹自己的「乾哥哥」建建給他認識,建建也算是條好漢,不缺女孩子,但他獨獨看上了李寶莉,後來出獄開了酒吧也一直在追求她——但李寶莉年輕時拒絕建建的原因很簡單,他學歷低,沒好工作。小說中清除交代了她接受馬學武追求的動因:「找個學歷高的,將來生個伢也聰明,好好學習考好大學當大官,讓我享清福。」這就是草根李寶莉的婚戀觀:現實計算是個主要方面。
愛情和婚姻從來都是有所關聯的兩碼事,愛情更多屬於感覺層面,來時山呼海嘯,去時瞬間全無;而婚姻是現實的生活邏輯的產物,充滿了算計和考量。萬小景和大款老公有婚姻關係,但這種婚姻的主要內容就是老公自己在外邊搞外遇,為了維持家庭和自己財產不被分割而不斷給小景錢花,小景和老公之間是沒有愛情可言的。馬學武和廠裡的打字員(影片中設定為工會人員)之間是兩情相悅的,兩個人都有家庭,但在90年代內陸城市還不是很開放的社會風氣里,能出去偷情,則無疑是愛情的表現,但殘酷的生活邏輯是不能讓他們走到一起重組家庭的;出獄後獨資經營酒吧的建建始終對李寶莉不死心,處處提供幫助,這種愛情李寶莉心知肚明而且心嚮往之,即便在萬小景極力促成之下,小說中他倆也始終沒有走向婚姻。愛情或許是個奢侈品,像巧克力,婚姻是個必需品,像麵包。在凡夫俗子的生活里,只所以必須選擇婚姻生活,完全是現實的生活邏輯的產物,因為兩人世界的婚姻生活能保證自己活的更好的機率更大:穩定的家庭會提供穩定的生活、為穩定的發展提供支持。當初馬學武和李寶莉走到一起,一方面是馬學武看中李寶莉是武漢人,而且長得好看,這對「鳳凰男」很有殺傷力;而李寶莉看中馬學武學歷高,有不錯的工作,將來能保障自己的生活。在婚姻中的現實問題面前,李寶莉和馬學武衝突不斷,這實際上已經在衝擊兩人的婚姻共識,尤其是李寶莉地位下行,全部生活重心和希望壓在馬學武身上時,馬學武的背叛終於讓李寶莉做出報警的嚴重舉動。旁觀者清,萬小景對此非常明了,因此她會說「你瘋了?!」她很清楚李寶莉在生活上對馬學武的高度依附性,而報警的真相一旦被馬學武知曉可能會讓李寶莉失去所有。
作為「新寫實主義」的文本,其所反映的背景為90年代武漢底層人生活的情景,其實在當下中也有現實意義。愛情和婚姻問題在今天這個時代的話題性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在現實的生活邏輯和商業化浪潮之下,「寧願坐在寶馬里哭,也不願坐在自行車后座上笑」的言論、「乾爹」、小三、援交包養、離婚率提高等現象的出現,《非誠勿擾》這樣的相親節目、各種相親網站和活動的風行,婚戀話題史無前例地成為一個社會議題乃至社會問題出現在這個時代。在此前社會相對簡單的年代,婚戀問題相對容易地開啟,即便有很現實的利益考量,但也會很快選擇進入婚姻,而後相對穩定和順利地變成那時人們單純生活的一部份,而這種單純性在現今社會中似乎成為一種傳說——如今的婚戀問題無限複雜,而這種複雜性也催生了整個婚戀產業的繁榮,從相親交友到婚慶再到婚姻矛盾調解和心理諮詢,婚戀問題本身成了一個產業,把人們生活中的一部份剝離出來加以商業化運作,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實質,這種社會裡,我們每個人都有成為問題的可能。
《萬箭穿心》講的是一個底層女人的悲劇,一個從階級到性別都在現實的生活邏輯重壓下的悲劇。說房子的風水不好,實際上並無多大意義,因為這房子裡出了高考狀元,能直接上北大清華;說房子的風水完全無關,那麼這個故事就無從講起,李寶莉的悲劇就從住上這新房子開始。最終李寶莉離開了這讓她充滿痛苦和艱辛的房子,這房子曾經是美好生活的開始,她的離開又開啟了另一端新生活,她的生活會好起來嗎?小說和電影都沒說,或許這就跟「風水」這個詞一樣,「道可道非常道」般不可說;或許就跟底層小人物拿這個時代沒辦法一樣,說了也白說。
文本對比:
看電影前突擊讀完了原作,湖北作協主席方方的六萬一千多字、寫於2007年的中篇小說,兩到三個小時能讀完。文本對比如下:
馬學武:小說中描寫為大專學歷,原為技術員,然後當上了廠辦主任,電影中萬小景在李寶莉家吃完飯聊天時的情節:萬小景說李不該總說馬是鄉下人,都是一家人了嘛。這台詞間接介紹了馬學武的「鳳凰男」身份。原著中說到有廠長是他的同學,有意要提拔他,於是走入行政崗。因為偷情時間被曝光,被貶稱為技術員,後來因為此事名聲不好,成為工廠下崗首先被裁掉的人。小說中的馬學武也很軟弱,但並不似電影裡刻畫成那樣。
馬學武父母:小說中敘述為鄂西某市的中學老師,退休後房子被拆,聽家鄉馬學武表哥的意見,來到武漢投靠兒子。片中只安排出現了馬母一人,其實老兩口一直都有戲份,且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後來孩子在武漢工作掙錢了以後,在武昌的湖邊買了別墅給二老住,為了湊買別墅的首付,小寶(馬文昭)讓李寶莉離開,要賣掉房子湊錢。小說中馬家二老和李寶莉的矛盾很尖銳,但電影做了溫和處理。
李寶莉:小說中交代了是下崗職工,下崗後到漢正街一個賣襪子的老闆處打工,小學學歷。因為長得好看很多人追求,她看中了馬學武的學歷高,人長得也不錯,在馬學武追求下和他結婚。結婚前閨蜜方小景介紹自己的「乾哥哥」建建給李寶莉,但李寶莉看不上,小說開頭李萬二人開玩笑時李說:「就要找個學歷高的人,將來生的孩子也聰明,能沾上光。」小說中的李寶莉八面玲瓏,特別會說話能幹活,在漢正街的特別有號召力,有點《生活秀》裡吉慶街「一姐」來雙揚的意思,電影中將李寶莉刻畫地更加憨直和良善。
李寶莉父母和妹妹:這在電影中徹底被省略了,小說中交代了李家是武漢人,李寶莉父親原來是碼頭的,因為工傷內退,在巷口擺了個自行車攤;李母是個性格很強的人,因為自己貧下中農的身份,在文革時當過領導,改革開放後成為普通退休工人,卻是個很硬氣很能幹的人,李寶莉的性格大部份跟了她母親。小說中對李家貧寒的生活在開始就有描寫,後來李寶莉當扁擔時為了給孩子湊大學學費,幾次賣血被家母發現,後來沒辦法李寶莉去找家母借錢供孩子讀書,但發現父親已經是癌症晚期,於是沒有張口,李夫後來去世。李家另一個人物是李寶莉的妹妹,上了中專/職高,當了白領,小說開頭就出現了一次,其中交代她對自己的學歷有優越感,比較懶惰,衣服都是李寶莉幫著洗過一回。
萬小景:李寶莉的髮小,讀過高中,小說剛開頭就介紹了李萬二人的學歷。嫁了一個大款,大款在外面有很多女人,方小景和丈夫的感情名存實亡,只負責要錢花錢,李寶莉最最忠實和可依賴的朋友。
小寶(馬文昭):小說中記載他從小就很怕媽媽,因為媽媽總在訓斥爸爸,由於爸爸有文化,作為學生的他自然和爸爸更親近一些,後來馬學武跳江之後,他完全倒向爺爺奶奶一邊和李寶莉做對,三個馬家人欺負李寶莉,他以高分放棄去北大清華而報考了武大,他說因為怕李寶莉對爺爺奶奶不好,後來其工作後賺到錢,還在正月過年時去看了看外婆,李寶莉的媽媽,但是對李寶莉依然無情。
和馬學武偷情者:小說中寫成廠里打字員,電影裡設定為工會人員。眾所周知國企的工會是個閒差,管福利管活動,本身就不忙,認識廠里所有人,這樣也為兩人的姦情提供點邏輯合理性。
扁擔何嫂子:小說中沒有何嫂子兒子受傷李寶莉借錢的情節。
建建:從李寶莉結婚前就喜歡她,後來多了監獄,出來以後他母親得病,為了治療替某人蹲了10年監獄換來50萬給他母親治病,出獄後開了一個酒吧,沒有電影裡刻畫的那樣黑社會或者地痞流氓受保護費的情節,小說裡的他很文雅,從始至終都只是在表達對李寶莉的愛戀,到影片結尾也沒有上床或者後來李寶莉搬出來後和他在一起的情節。
相對小說中非常尖銳、讓人讀了以後揪心的矛盾來說,電影做了較為柔和的處理:馬家人(二老加上小寶)對李寶莉的百般刁難,冷落和漠視,集中體現在李寶莉為了何嫂子和地痞打架,腿被砍傷,養病時馬家老太生病,李寶莉不顧自己的傷勢去陪夜看護,自己反倒病情加重住院,但馬家人對此毫不領情。另一處為:李寶莉為了給孩子湊大學學費,不得已多次賣血,被萬小景發現不對勁,知情後萬小景盛怒之下罵了馬家二老,馬家的態度稍有緩和,主動把養老金給李寶莉當作孩子學費。
小說中的一個關鍵背景:李家父母,在影片中未出現。李父的匆匆出場和李母的硬氣、大氣和洞察世事,很多有道理的話都是馬母說出來的,如:她認為生活就憑自己的硬氣,無論物質條件如何,自己首先要硬氣。馬學武走後,她告訴李寶莉今後全憑一個「忍」字,凡事都是忍。後來李父彌留之際說自己最大的福分就是娶了李母為妻,李家的悲情戲份也比較有看頭。李父去世後,李母對李寶莉說:「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沒道理,而且每個人的道理都不同。當年我當革委會主任時,我覺得有道理,大家覺得沒道理,現在我生活這樣,我覺得沒道理,但別人覺得有道理。」小說和電影的中文名字叫《萬箭穿心》,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小說開頭部份,分到新房子的李寶莉高興地帶自己的父母在樓上看江景,結果李父說出了這句「萬箭穿心」的風水問題。小說中李寶莉因為這個說法而在做家務時生過氣。電影中此言則是安排給了萬小景,馬學武走後李寶莉和萬小景坐輪渡時萬小景說的。
階級
影片中時常會出現一個鏡頭:房屋密集的居民樓,看上去特別像居住條件緊張的香港特有的「屋村」,這就是李寶莉「萬箭穿心」的新房所在地。這套房是馬學武廠里分配給他的,是典型的工人階級居住區:空間擁擠、建築物色調和樣貌高度整齊劃一。另一個常見的鏡頭是漢口的一個大全景,層層疊疊的樓房和最遠處的長江、大橋,似有王安憶《長恨歌》小說開頭寫景的韻味。這兩個鏡頭在影片中多次出現,雜亂、層疊、密集,色調陰鬱,這實際上在預示這是一個關於底層人的故事。他們辛苦在城市謀生活,時代變動面前往往成為最脆弱的一部份。
電影的時代背景也鋪陳得清楚:香港武俠電視劇、漢正街上90年代的流行歌,人們的穿著方式,把故事發生的時間置於90年代,這剛好是李寶莉下崗後賣襪子、後來馬學武被下崗的大背景:90年代國企改革的下崗潮。馬學武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典型的社會主義大工廠、上下班時的自行車流、鐵路道口旁工人們吃著熱乾麵等著過去,他是工廠的普通技術員,在市場經濟之前是國家的主流入群,而他的工作和學歷,也在小說中有所提及,都是一個作為社會底層的小市民李寶莉所看中的。但李寶莉是武漢本地人,對馬學武這樣來自小地方的「鳳凰男」,她無疑在出身或城市的歸屬感上更有優越性,萬小景在電影裡對李寶莉的批評:「你早做麼事去了?他出軌之前你就要把他牢牢抓住,你之前對他不好才導致他今天這樣,你總是喊人家『鄉下人、鄉下人』,都是一家人了,說這個搞麼事?」
馬學武無論在小說中還是電影裡都被刻畫成一個高度軟弱、唯李寶莉命是從的妻管嚴。除卻李寶莉遺傳了李母的硬朗霸氣、馬學武文弱這些性格因素之外,社會原因是一個重要方面。李寶莉是武漢本地人,長得又好看,而且下崗之前也是工人階級,這些都對鳳凰男馬學武極有吸引力,而這現象背後的城鄉差距問題,直到20年後的今天,依然在人們的發展和婚戀問題上有不少的影響。從結婚到搬入新房,馬學武在性格霸氣的李寶莉面前忍了很多年,但在搬家後工人們說的一句「被這樣的女人罩著,你有再大的成就也是……」激化了馬學武心中的屈辱,當天晚上,他提出離婚。
離婚的問題實際上是兩人相對位置變化的表徵:此時的馬學武受領導的器重,已經由技術員升為廠辦主任,進入領導層,他的前景是光明的,社會階層的躍升讓他有了更多資源和更多選擇,恰恰外遇也就發生在此時,外遇實際上是馬學武社會階層上升帶來的紅利;此時的李寶莉則成為社會底層,早年下崗、小學文化程度的她只能去漢正街幫著賣賣襪子,在夫妻雙方的博弈的相對關係當中,李寶莉全面處於下風。李寶莉對此巨變應該並無深刻認識,在家中依舊對馬學武吆五喝六,這讓馬學武離婚的心思實際上越來越成熟。影片開頭馬學武對李寶莉求歡的排斥完全是這種問題在生活中的反映。
「萬箭穿心」這一話語的實際承載物毫無疑問是房子。新的房子是李寶莉在小說開篇歡天喜地的原由,也是此後劇情上演的舞台。90年代開始的住房商品化過程,本身就是中國全面進入市場化時代的最重要一方面,房子是人們參與市場競爭的資源,更是任何一個人在市場經濟的主舞台——「城市」當中安身立命的身份象徵。在用慣了「有臭味的公共廁所、共同的下水管道」的小市民李寶莉心目中,新房子和美好新生活是緊密勾連載一起的,因為房子是馬學武給這個家庭和自己的饋贈,李寶莉決心好好待馬學武(小說中開篇就有提及);同時,馬父馬母不請自來的行為,在李寶莉眼中實際上是局外人對自己美好新生活的粗暴瓜分,因此她對馬父馬母的排斥,實際上她對自己想像中美好生活的捍衛——但這種美好生活終究只是想像,更要命的是夫妻對未來的想像不同:馬學武厭倦了對自己呼來喝去的糟糠之妻,想要借自己事業的上升來送舊迎新,即便偷情後身敗名裂,他依然會去和偷情女子見面,可見他對李寶莉從內心的徹底決裂;李寶莉則希望在新屋帶來的物質改善當中繼續自己已經習慣了的、和馬學武以前的生活和溝通方式——夫妻同床而異夢,離婚或者決裂成為必然選擇。
李寶莉因為自身文化程度低,在和家庭其他兩個成員(小寶和馬學武)的互動中處於邊緣化境地。馬學武一直輔導小寶學習,小寶也親見母親對夫妻的種種呵斥,小寶自然和父親更親,而馬學武和李寶莉因為生活空間和階層慢慢拉開差距,所思所想除了家庭這方天地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交集。馬學武走後,李寶莉由於忙於生計更不能融入小寶的生活,因此隔閡日深。
除卻李寶莉自身,她背後「娘家人」也是她參與社會博弈的自身資源。正如小說中所描寫的,李家實際上是城市低層,他們住在使用公共水龍頭、公共廁所的街區,因傷內退的父親在巷口修自行車,因為時代轉變、原本在文革時期叱吒風雲的李母則成為新時代菜市場買魚的小商販,李寶莉的妹妹是個小白領,內心虛榮,看不上家人的做派。後來李父去世,家中更拿不出錢給小寶上大學,這一切都將李家定位在90年代社會激變當中地位下行的人群中,李寶莉也是這個下行人群中的一員,邊緣和弱勢的不言而喻。李家社會地位下行另一個表現即:萬小景在得知李寶莉為了謀生活而當了「扁擔」,氣憤的說:「你怎麼能幹那種下等人的事情。」的確如此,萬小景和李寶莉是髮小,都是之前的小市民,在他們眼中,「扁擔」這個活計是最低賤的體力活和下苦的差事——但李寶莉確實當了「扁擔」,李父也靜靜地去世了,這就是曾經的小市民在殘酷社會分層中下行成為下層階級的現實。
作為李寶莉「娘家人」的萬小景實際上是給李寶莉從物質到精神各方面支持最多的人。她的生活可謂是「感情不幸錢包幸」,大款老公和她之間已經沒有感情可言,老公在外面養著N個奶,萬的老公是個生意人,他實際上是市場經濟中的贏家,對性資源的充分佔有,只是其諸多勝利中的一方面。影片中還有個場景能和此呼應:李寶莉去給何嫂子錢,到了何嫂子住在扁擔專用的地方,這個地方原來是建建出租的,就在李寶莉和建建交談時,畫外音是叫床聲,鏡頭一轉,另一個屋裡的男扁擔們正在擠在一起看A片,社會底層的人們因為經濟上的潰敗,性資源極度缺乏,無法擁有正當的性權利,只能通過這樣意淫的方式解決,這無疑和萬小景老公是最好的對比:生活的對比,更是階層的對比。
這是一個關於女人的悲劇,更是一個訴說階級問題的文本。離婚,不僅是馬學武擺脫李寶莉「欺負」的唯一途徑,更昭示了社會地位逐漸上行的馬學武準備和李寶莉及李家日漸下行的社會階層決裂的意願。這實際上是大時代社會激變、階層劃分這樣殘酷現實的一個顯影:小家庭中的變動,反映的是社會大格局的變化。離婚所表徵的社會激變,是馬學武的悲劇和李寶莉此後痛苦人生的開端,更是這出人間悲劇的真正原因。馬學武因為被舉報嫖娼,前途幻滅,後來還因此而被下崗,曾經一切美好的東西化為烏有,他內心最為認同和看中的階層上升的途徑被堵塞,事業的失敗使得自己去擺脫這樣一個已經深深厭惡的家庭的可能性幾近為零,絕望中,他選擇自殺。一個男人,可能他最為珍視的東西未必是家庭,而是成就感,這不同於女人,和馬學武偷情的同廠女職工並未自殺就說明了這一點,她可以苟活,但馬學武卻接受不了,因為這種苟活會讓李寶莉對自己更加頤指氣使,卻又不同意與自己離婚,讓自己進入無期徒刑——而這間接證明了,男人的生活的全部意義,更依附於社會當中的相對地位、階級及其帶來的社會認同感。
性別
上段陳述中男女生活重心不同的說法,在女權主義者眼中可能是性別政治不正確的表現,但毫無疑問,《萬箭穿心》這小說還是電影的中心情節,其實是一個關於女人的悲劇故事。貫穿全片的主要人物毫無例外都是女人,李寶莉、萬小景(建建的角色在小說中從未單獨出現,完全是在萬小景、萬小景+李寶莉的場景中才會出現)、李母(這個重要角色是一個大時代轉變的簡介,在電影中並未表現)馬家的代表馬母(小說中始終和馬母同時出現的馬父在影片中刪掉,而作為馬家人的小寶,實際上只是一個馬學武靈魂附體的人,是一個小「馬學武」,體現的是馬學武+馬家二老的想法)、乃至作為女「扁擔」代表的何嫂子(小說中的何嫂子遠比電影中霸氣),都是這個文本的性別特徵。
如果這個故事的其他元素不變,而只是性別特徵改換以後會怎樣?在此做一個大膽的假設:工廠技術員馬學武因為事業平庸,自己為人又唯唯諾諾令人生厭,妻子離開(或絕望跳江或面臨誘惑拋棄家庭遠走高飛),他又不幸工傷致殘,下崗大潮中被國家無情拋棄,父母老家的房子被拆過來投靠(這是小說中的情節),他身無長物只好淪為漢正街的「扁擔」,一個人含辛茹苦供小寶成為高考狀元(期間小說中的賣血等情節不變),但小寶因為母親的離開十多年來一直和馬學武齟齬不斷,最終還是不原諒父親,於是馬學武成為一個佝僂蒼老、在漢正街上賣命的老「扁擔」……
這個故事怎樣?主人公仍舊是一樣的慘,但整個故事的悲劇性卻大打折扣,被李寶莉的故事的悲劇性甩出十幾條街。如果主人公是個男的,那麼這個故事多少會讓人讀出一點勵志的味道,反而成為「守得雲開見月明」的有點正面意涵的故事。作為男性的悲劇人物,這樣的「男扁擔」馬學武能慘得過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嗎?能慘得過余華筆下的福貴嗎?顯然不能。就算對故事進一步做改動,突出悲劇性:小寶不學好,成了少年犯,馬父馬母年老無錢治病孤獨地客死都市,馬學武為了解決生理需求去嫖娼結果染上了性病,身體崩壞,扁擔也幹不了了,於是在絕望和精神錯亂中死去……慘是夠慘,但這不同於悲劇性。悲劇不光是慘,還要能激發人的惻隱之心、同情心乃至悲天憫人的情懷——這方面,女性為主角天然能激發出人們的這種感受,這是被社會角色所規定了的男女的根本不同。
在影片的影視語言當中,同是扁擔,男扁擔很少以悲情和苦痛的表情示人,他們大多抽菸開玩笑,臉上多少有點賣力氣人的暢快和大條。底層男性們心情低落或者面臨困境時,打罵老婆,喝頓大酒、和朋友們哭得稀里嘩啦,大罵社會或者和別人打一架,都多少能紓解心頭的不快;在生活方面,他們可以底層人的無賴姿態隨便調戲女性,就像阿Q的行為,他們可以看A片(A片完全是男性視角,主要受眾亦是男性),或者乾脆去嫖娼、隨意支配自己的身體……男性在社會當中的憤懣和失望是有諸多出口的,他們也擁有更多的機會,他們抗打擊程度更強;女性恰恰相反,同樣底層的女性,並不能通過男性的方式發洩不快,她們解決生理壓抑的手法也不能像男性那樣隨意和方便,她們無法打罵老公和孩子,無法像男性一樣對社會施以惡意。如果說底層人承擔著這個社會最苦痛和最悲慘的境遇,那麼底層中的女性,無疑是最具悲劇性的群體,正如同孔乙己似乎永遠比不上祥林嫂更悲劇。
本片的英文名字叫「fengshui」,即「風水」,「萬箭穿心」也取自風水理論。但實際上,無論在小說里還是電影中,「萬箭穿心」的情節出現都不超過兩次,而且李寶莉對此還並不服氣,她偏認為是「金光萬丈」。李寶莉不信風水,但她信命。她偶爾會說自己的命格不好,她跟小景借錢時說「每個人都是來世上還債的,借的越多下輩子就還人家越多」之類的宿命論的話,當李寶莉無法面對和無法解釋自己的生活的窘境時,只能拿著這種說法來搪塞。風水本事堪輿之學,將居住和建築問題和人生運到的宏觀事務聯繫起來,這無疑是中國人對生命的一種認識,而且我也不懷疑製片方不願用《一個女人的悲劇》之類的大俗話或者「萬箭穿心」根本無法用英文翻譯的初衷,他們用了「fengshui」這樣一個外國人看來充滿東方神秘主義意蘊的詞語,因為其很難解釋,所以無法辯駁——當中國人遇到一些無法解釋和處理的問題時,會用「命」「緣」「運」等等本身就沒有確切含義的概念來加以解釋,一個「fengshui」,就概括了李寶莉的悲劇,這似乎是在說:李寶莉的悲劇是無法解釋的,她對自己的命運無從把握,因為這一切都是「fengshui」這樣的宏大因素在起作用。
看畢方方的《萬箭穿心》,我想起另一個武漢作家池莉的中篇《生活秀》,兩篇同由武漢女作家寫出的漢味故事,反映的也都是90年代中國市場進程和拜金潮席捲下的大時代裡的小人物人物故事。《生活秀》裡的來雙揚風華絕代、精明強幹,她生意紅火、巧妙地爭回房產、擺平家裡的糾紛,但她在卓雄州身上渴望實現的感情救贖卻最終破滅,是一個從詩意救贖的可能到殘酷的生活邏輯重壓之下詩意無奈消解的過程,但這不是悲劇,只是多元生活中本身的一種可能性;《萬箭穿心》實則是一個女人的悲劇,這個女人從頭到尾都沒有綻放過、炫目過,她在底層社會終其一生,她眼裡現實的生活邏輯是第一位的,她對更好生活過於急切的熱望讓她粗暴地表達自己,她並沒有溫柔地對待丈夫和孩子,為了維持正常的生活邏輯不影響小寶考學,小說中她始終也不敢接受建建的愛。如果說來雙揚除了後來未遂的感情之外,真的在市井的世界吉慶街里活出了女人的精彩,相比之下李寶莉殊為可悲,她有底層人的粗獷大條、生活所迫斤斤計較,「美」在她的身上實際是缺席的,這讓丈夫遠離他——在愛情(馬學武要離婚、出軌、自殺)和家庭(小寶和他斷絕關係、馬父馬母對他形同陌路)徹底拋棄她之後,她真的一無所有。這實際上也反證了我之前提到的現象和觀點:馬學武自殺但偷情女未自殺,她雖然從此從工廠消失,但她並未因此失去家庭或重組了家庭。社會賦予兩性較為固化的角色讓家庭成了女性生活的極大支柱,來雙揚沒有愛情和一個不完全的家庭,這是她內心永遠無法紓解和渴望被救贖的,好在她有出眾的外貌、能力和生意支撐著她;沒有這些特點的李寶莉在被家庭邊緣化之後,悲劇性油然而生。
愛情和婚姻
李寶莉是個美女,小說中交代了她年輕的時候不乏追求者,即便她後來當了「扁擔」,因為打架受傷後休養了一段時間也恢復了美貌。她的美貌是她年輕時期最大的資本,加上她潑辣爽利的性格,大氣能幹(電影中沒有很好地表現出這點,是個遺憾),她也算是個拿得出手的「草莽巾幗」。她小學畢業,很小的時候就跟著母親賣魚賣菜,後來當了一段短暫時間的工人之後下崗去賣襪子,因此李寶莉生活的核心就是「現實的生活邏輯」,草根出身讓她將現實利益擺在第一位,發小萬小景當年介紹自己的「乾哥哥」建建給他認識,建建也算是條好漢,不缺女孩子,但他獨獨看上了李寶莉,後來出獄開了酒吧也一直在追求她——但李寶莉年輕時拒絕建建的原因很簡單,他學歷低,沒好工作。小說中清除交代了她接受馬學武追求的動因:「找個學歷高的,將來生個伢也聰明,好好學習考好大學當大官,讓我享清福。」這就是草根李寶莉的婚戀觀:現實計算是個主要方面。
愛情和婚姻從來都是有所關聯的兩碼事,愛情更多屬於感覺層面,來時山呼海嘯,去時瞬間全無;而婚姻是現實的生活邏輯的產物,充滿了算計和考量。萬小景和大款老公有婚姻關係,但這種婚姻的主要內容就是老公自己在外邊搞外遇,為了維持家庭和自己財產不被分割而不斷給小景錢花,小景和老公之間是沒有愛情可言的。馬學武和廠裡的打字員(影片中設定為工會人員)之間是兩情相悅的,兩個人都有家庭,但在90年代內陸城市還不是很開放的社會風氣里,能出去偷情,則無疑是愛情的表現,但殘酷的生活邏輯是不能讓他們走到一起重組家庭的;出獄後獨資經營酒吧的建建始終對李寶莉不死心,處處提供幫助,這種愛情李寶莉心知肚明而且心嚮往之,即便在萬小景極力促成之下,小說中他倆也始終沒有走向婚姻。愛情或許是個奢侈品,像巧克力,婚姻是個必需品,像麵包。在凡夫俗子的生活里,只所以必須選擇婚姻生活,完全是現實的生活邏輯的產物,因為兩人世界的婚姻生活能保證自己活的更好的機率更大:穩定的家庭會提供穩定的生活、為穩定的發展提供支持。當初馬學武和李寶莉走到一起,一方面是馬學武看中李寶莉是武漢人,而且長得好看,這對「鳳凰男」很有殺傷力;而李寶莉看中馬學武學歷高,有不錯的工作,將來能保障自己的生活。在婚姻中的現實問題面前,李寶莉和馬學武衝突不斷,這實際上已經在衝擊兩人的婚姻共識,尤其是李寶莉地位下行,全部生活重心和希望壓在馬學武身上時,馬學武的背叛終於讓李寶莉做出報警的嚴重舉動。旁觀者清,萬小景對此非常明了,因此她會說「你瘋了?!」她很清楚李寶莉在生活上對馬學武的高度依附性,而報警的真相一旦被馬學武知曉可能會讓李寶莉失去所有。
作為「新寫實主義」的文本,其所反映的背景為90年代武漢底層人生活的情景,其實在當下中也有現實意義。愛情和婚姻問題在今天這個時代的話題性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在現實的生活邏輯和商業化浪潮之下,「寧願坐在寶馬里哭,也不願坐在自行車后座上笑」的言論、「乾爹」、小三、援交包養、離婚率提高等現象的出現,《非誠勿擾》這樣的相親節目、各種相親網站和活動的風行,婚戀話題史無前例地成為一個社會議題乃至社會問題出現在這個時代。在此前社會相對簡單的年代,婚戀問題相對容易地開啟,即便有很現實的利益考量,但也會很快選擇進入婚姻,而後相對穩定和順利地變成那時人們單純生活的一部份,而這種單純性在現今社會中似乎成為一種傳說——如今的婚戀問題無限複雜,而這種複雜性也催生了整個婚戀產業的繁榮,從相親交友到婚慶再到婚姻矛盾調解和心理諮詢,婚戀問題本身成了一個產業,把人們生活中的一部份剝離出來加以商業化運作,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實質,這種社會裡,我們每個人都有成為問題的可能。
《萬箭穿心》講的是一個底層女人的悲劇,一個從階級到性別都在現實的生活邏輯重壓下的悲劇。說房子的風水不好,實際上並無多大意義,因為這房子裡出了高考狀元,能直接上北大清華;說房子的風水完全無關,那麼這個故事就無從講起,李寶莉的悲劇就從住上這新房子開始。最終李寶莉離開了這讓她充滿痛苦和艱辛的房子,這房子曾經是美好生活的開始,她的離開又開啟了另一端新生活,她的生活會好起來嗎?小說和電影都沒說,或許這就跟「風水」這個詞一樣,「道可道非常道」般不可說;或許就跟底層小人物拿這個時代沒辦法一樣,說了也白說。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