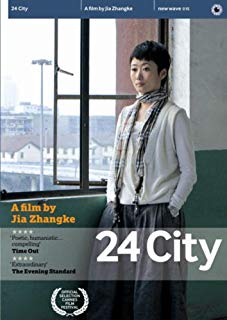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3-09-26 22:11:25
告別
「僅你消逝的一面,已是足以讓我榮耀一生。」
這就是所謂的好導演。他不急,讓畫面緩緩流過,流過每個旁觀者內心最柔軟的一小塊地方,然後再走。
賈樟柯就是這樣的導演。
大二吧,曾經一股腦看過他的小武、尹瑞娟等等的故事,一股腦接受了任逍遙、站台的洗禮。灰色的山西小城,黯淡的青春,許多隱隱作痛的歲月痕跡,全部融成一塊濃得化不開重得往下沉的東西,哽在喉間。然而也僅僅如此。到了三峽好人、東,越發有點不懂了,想情節也想不起來多少,只是記得那幾張海報,和看這些東西的某間教室。
然而二十四城記不同。忘了為啥忽然想起下了來,於是糾結在Masaccio的畫作分析文章途中看了。足夠現實,足夠藝術。像牯嶺街,看了就讓人隱隱地受不了。好像Number 23裡面金凱瑞的太太說:好的書就好像是作者偷去了讀者內心最隱秘的一小部份——好的電影也同理。
一個國有軍工廠被房地產公司買了地,工廠搬遷到郊區。一個聲音(莫非就是賈麼)訪問幾個真的員工,然後有幾個演員再來演幾個員工或者員工家屬。這樣一串故事。
開頭廠里開大會工人唱《歌唱祖國》,一下子就想起1984。然後是東北來的老工人、妻子病在床上訥訥的老師傅、公車上苦苦的下崗工人,一段段地讓淚湧出來。到了呂麗萍出來倒顯的突兀,陳沖提到自己的時候滿是美人遲暮的蕭索,趙濤變得好漂亮了,最後她那麼風蕭蕭地看著這個滿是高樓的城。
Bosch的畫裡,城市竟在地獄的所在,想想令人傷感。
說一點「大詞」吧,所謂單位制的崩塌,人們和傳統、和上一輩、和自己的告別,究竟要以如何的方式進行?
許多人靜靜地站著,讓畫面定格。他們的眼裡,不該是空洞的。他們說,人有事做,老的慢一點。
「整個造飛機的工廠是一個巨大的眼球,勞動是其中最深的部份。」還有「怪奴何事備傷神,半為憐春半惱春」,還有本文最前面的一句話。導演彷彿還是念著舊的啊。「二十四城芙蓉花,錦官自古稱繁華」,最古的名字,又成了最新的。
一字不多,滴水不漏,過去就那麼過去了。卻總是想起那一句: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