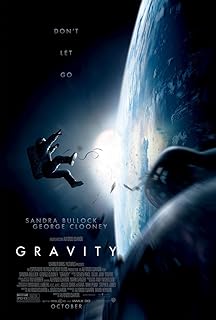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3-10-04 14:54:25
電影前路上,這已不僅是「高概念」那麼簡單
通常,在電影開始後的20個鏡頭以內,我們便能夠大致對自己將要看到的影片節奏樣式有了一個大致的心理模型。在開場12-15分鐘第一場戲基本結束後,有經驗的電影發燒友便能嗅出故事所使用的發展策略甚至能夠預測故事的結局走向。當今的觀眾,早就不是被《火車進站》嚇得四下逃竄的「觀影幼兒」了。現在的觀眾都是monster,不僅口味不是一般的重,而且各個身經百戰,一般畫面和噱頭也就僅夠他們摳腳一笑罷了。而我,也是帶著這樣的信心隻身來到影院準備嘲笑那個把《哈3》拍成翔的導演的新作。
在出發前去電影院之前,我瞟了一眼預告片。很明顯,「高概念」嘛。很少有預告片敢放這麼長且連續的細節鏡頭,且完全沒有「劇情」的概念和線索在預告片中。「the Look, the Hook, and the Book」——大不了就是美麗的太空,藍色的星球;為了回家,辛苦波折;穩紮穩打,開端發展高潮結尾規規矩矩的劇情推進,且最後一定要成事兒。(事實上確是這樣。片子情節簡單到,想要不劇透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個字兒不說。按who/where/what表述劇情就是——「太空人,在太空,要回地球」的故事,連why都不用給。沒了。)
可當《gravity》的一個鏡頭出現時,我就立刻停止聒噪了(也許是因為有人故意讓我們以此記起庫布里克曾給我們留下的太空夢魘)——我們如衛星般,處於萬里之上無氧氣無生命的無垠宇宙空間凝望著自己賴以生存的這個美麗的藍色星球——我不禁心下「wow」——想必在太空站上進行太空漫步的太空人有如此所睹也必然由此所思所wow吧——果然,鏡頭前景進入了美貌大叔太空人喬治克魯尼凝望地球的臉。在藍色星球的映襯下,也許這會是克魯尼大叔所有片子裡把他拍的最美的一個鏡頭。因為他要代表全體觀眾開啟摺扇凝視太空之門。
我們都是沒有上過太空的人(排除那零星幾個),如果你非要說你看著畫面中的日落極光、地球上的山川海洋,太空的深遠無垠,以一顆流星的視角卻什麼感覺都沒有,那你就ZB了。管你BBC紀錄片看過幾百套,面對超大屏超逼真近在眼前的「幻景」,你的生理本能就是雞凍。3D,IMAX之類是未來電影導向,這是有原因的。
雖然我知道光看景就獵奇得很有感覺也不能代表這是個好片子講了好故事,但靜心細想,這種獨處萬里太空之中艱險求生的影片,如果不是在此情境中,你還會看嗎?這此的劇情雖然是放在太空,但其實和傳統的荒島求生,密室求生…如出一轍。奇觀。和噱頭。沒人做的比它更明晰和徹底了。
影片劇情的推進和發展其實沒什麼好說的。跟一般的逃生電影無疑,困難,困難,一個接一個「差一點就搞定了」,甚至它的劇情設計比其他片子還要牽強一些,bug還要更多一些。(因為……以我shallow的太空知識也覺得,憑誰在太空如果遇上飛船失事,也是一百個死定了吧喂!導演,你和你兒子這麼敢想敢幹,我有那麼一瞬間,突然為之勇氣很感動!)
電影不僅是夢境,還是神話。那麼神話嘛,製造神奇之人驚奇之事才是負責任的態度。並沒有什麼太過苛責的。如果你在觀影是沒有因為邏輯bug影響你屏息凝神,那麼這些bug其實便不成立。(商業電影好像沒有負責流芳百世這個選項。但若導演不只追求商業電影的幾把刷子,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
當桑德拉·布洛克從湖裡爬到岸邊,突然得到的gravity使她一站之下竟然沒有爬起來。這麼個輕輕地一個「爬不起來」,勝過多少大片裡男女主人公相互抱著在夕陽里啃來啃去。雖然其本質其實也相當於此,只不過主人公是「人類」與「地球母親」。
因此,《gravity》並不是沒有情感。這種情感,是一種最基本最原始,我們幾乎都不能自覺的情感。是大部份的作者提起它都不知道該從何下筆,卻一下筆又汪洋千里。(讓我想起《老人與海》裡的Diego。)它是生命對生命的依戀,是地球人對地球,我們對母體的依戀。存在之於存在的意義。男女之愛,母子之愛,友情,道義,都讓位於這最基礎的情感。
通片導演都沒有講什麼「生有多麼好,死有多可怕」這類的說教,連大帥哥克魯尼的從容赴死消逝夜空中也美好平靜得跟詩一樣。布洛克本也想學了他的樣子從容赴死,但死前的迴光返照讓她涅槃了。這麼一涅槃,什麼都有了。(不得不說,此片的價值觀,是把《駭客帝國》的主導價值狠狠抽了個底兒朝天的嘴巴子。現在明白為什麼駭客帝國里自由人要一個勁兒的往地底下鑽了。從高處往下看,看到的都是「母體」的偉大正確溫暖異常啊。)
活在地球上,污濁的一切已經讓人不想再活,如何才能跳出來給自己一個活下去的理由呢?到夜空中去吧。面對著這樣一個水靈靈,充滿生機,獨一無二的藍色球體……你還有恨嗎?不到太空中去,你知道地球母親對你有多「親」嗎?gravity,一個你可能從生下來到死去都沒有想過要為得到它而拼死掙扎的東西。在太空中,你可明白了?你「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
電影是夢境。是神話。還是寓言。它愈是簡單,可被解讀的空間就越大。
(有木有人覺得「神zu」的外殼跟美國的一比在片中看起來有點像玩具;俄羅斯的衛星內部起火灰飛煙滅那是一瞬間的事兒,跟前蘇聯一樣;美國太空人被漢語戲弄,最後還借雞生蛋的情節,為毛讓我一下覺得美國人對外債這個事兒那麼耿耿於懷呢,感覺好萊塢對有關中國的一切都懷著非常「複雜」和「糾結」的態度欲拒還迎心猿意馬啊……)
* * * * * * * * * * * * * * * *
我的點,其實要說不是該片的視效有多牛逼,編劇路子對不對,有多狗血,故事背後有什麼思考空間……而是我們的所謂「肉體經驗」,如何從新成為了觀影的主導,成為了引誘觀眾繃在影院座椅上呼吸緊張的主因。
而大呼「神片」的觀眾,應該也是因為這個道理吧。
「老子閱片無數,身經百戰,居然在看你這個diao片子的時候大氣都不敢出,全神貫注坐了90分鐘!你很牛b,你神!」其實這感覺與「火車進站」時觀眾亂竄是一個道理。他們當時也是這麼讚嘆電影是個神奇的玩意兒的!
(而討厭它的人,則更多是因為他們厭惡自己的情緒或心理活動被如此邏輯簡單的劇情攪擾的挫敗感吧,要感謝他們「寧死不屈的理智」。)
這樣看,此片倒像是電影原教旨主義的進步。笑
* * * * * * * * * * * * * * * *
bo的電影資料館放完《gravity》還要放1920年的《佐羅的面具》,本想看的(在國外,看默片最省力有木有!!),結果凍得堅持不了便走了。邊走邊感慨,歷史果然是在不斷畫圈……所謂螺旋上升。總會到達一個原點上方的位置,與原點心心相映~
當100多年前電影發明時的「名片」《火車進站》把觀眾嚇得四下逃竄的時候,讓他們震撼的原因不就是因為他們相信了電影的「逼真」,而被代入了影片的時空,進行了真實的心理反應。而今天,當觀眾們瞪視著宇宙的夜空和蔚藍的星球,當片中太空人因為氧氣不足而憋氣時,所有的觀眾也如昨日初生的「電影觀眾」般與他們一同憋悶,在他們摘下面罩呼吸時與他們一起大喘氣。而片中被影評人和觀眾吐槽太簡單太生硬的劇情,多次出現的「最後一秒營救」,1%的氧氣,「一線」之牽,諸如此類狗血老三套…為什麼它需要如此多的老一套劇情構造?
其實這就是一部如1920年的《佐羅的面具》,如1915年《一個國家的誕生》一樣不需要語言和複雜心理活動表達的影片。「GRAVITY」是什麼?是佐羅手裡的劍,是「國家的誕生」。而《佐羅的面具》和《一個國家的誕生》其實還比這個片子複雜得多,它們有太多大義凌然和潛台詞在其間。它其實更像1905年的《義犬救主記》,或者1902年《月球旅行記》的結尾——從月球逃生重返地球,總共就五個鏡頭。而《gravity》就是最簡單,最原始的求生劇情。返璞歸真。就這麼簡單,簡單到娘胎里!
電影史走了一百多年……突然體會到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猶如突然聽到「愛你始終如一」般感動。
原來電影學院老師在電影史、電影理論課上叨叨的——電影最本質的的「物質復原與再現」功能,那些打亂你心理節奏的老套橋段,那種騙得了別人騙不了自己的身臨其境的肉體經驗——其實一直沒有遠去,一直在支撐著電影的進步。
電影理論的先導和教父巴贊一定想不到,電影行至今日,電影「現實」的定義已經被打破了。比「現實」更加「清晰」的反而是那些虛構的「非現實」,而我們的「凝視」本身也已經從本質上改變了意義。按照巴讚的說法,我們已經很難講《GRAVITY》是一部相信畫面的導演所拍,還是相信真實。面對一個能讓你看到你所想的一切,一切瘋狂畫面的電影技術,蒙太奇的定義也許也該被改寫了。如果蒙太奇是為了製造節奏和戲劇性,那麼觀眾在一個鏡頭內震驚於看到自己「夢境」或幻境的這種戲劇性,又叫什麼?(我懵在這裡了。前路慢慢,老師,我們該不該放膽去想?而不是copy?)不管相信真實還是相信畫面,《gravity》至少在二者結合的路上生出了新枝。
不要拿什麼3D IMAX的《環太平洋》《阿凡達》來跟這個片子比較,那些是科幻片,是虛構和完全虛構。這個片子的基石,是非常現實的。因而此片才顯得特別,值得我打這麼多字。它是個純粹「夢境」,卻又現實到適合每個地球人設身處地的自我投射。(別告訴我你看阿凡達時也幻想自己變成藍色,看環太平洋時也幻想自己站在機器人兒里跳舞啊。情感認同和心理投射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後者能讓你產生某種「間接」的「肉體經驗」。)《GRAVITY》所基於的角度是,當每個地球人凝望夜空時的幻想。那是在我們八歲左右,我們剛學會思考,有一天曾問父母:地球的外面是什麼樣子?從地球的外面看地球是什麼樣子?
這部片子的出現,說明世界電影發展的排頭兵——「好萊塢」,已經在更深的理念上探索「新電影」的突破與創新。這種創新是將傳統好萊塢電影的萬用靈藥和新技術下大大被延伸的視覺可能性相結合的一次嘗試。
在理解了這一層之後,再細想,覺得其實這部片子在劇作上可以做的更精巧,可以放入的內涵其實可以更多。至少如果庫布里克還活著,讓他接手這個idea,一定比阿方索拍得更有力更令人回味無窮。但作為一個商業片,阿方索·卡隆和製作方已經在導向未來電影的先路上踏上了屬於自己的腳印(what a lucky boy!)。
通向未來電影模型的一步步,有無窮可能,重要的是我們要靠我們自己的想像力和idea去一步步實踐。
(回家的公交車上,看著歐洲街道上拎酒瓶子的各色trash,努力把淚忍回去——回想到國產電影的思維和現狀,除了尼瑪炒就是抄——感覺自己和這些trash無異。現實的差距帶來的壓力,有時真的讓人挺難過。很害怕,有生之年來不及做到……如此……酣暢)
@喬酒
謝絕轉載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