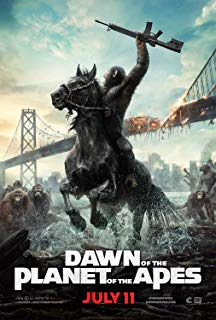2014-09-03 03:34:09
戰爭早已開始,哪怕在和平的時候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戰爭乃萬物之父,萬物之王。他讓有些成神,有些成人。有些拘役,有些自由」——赫拉克利特(B53)
倘若我們相信演化論,人類就是從猿猴變來的。對這個假說嗤之以鼻的人,往往覺得,人那麼了不起,祖宗怎麼可能是看上去丑且笨的猿猴?可災難之後,沒了電源的人群只能在恐慌中展現弱小,燃起火把的猿群卻依然在自己的家園裡從容地生息繁衍。
有些人因為「猿流感」摧毀了人類文明而對猿猴充滿了憎恨,它們的出現只能喚起消滅它們的念頭,比如那位水利工程師;有些猿面對人類便只能感覺到復仇的衝動,要殺死這一個、那一個,要殺了全部人類,比如猴群裡的科巴。
「原來我們這麼相似」。影片結束於更大的戰爭將要爆發之前,猴群之王凱撒和它的人類朋友馬爾康姆互道保重。但他們知道,他們的友誼對於人猿之間幾乎命定的敵對來說,不過是不可理喻的螳臂當車——「其實戰爭早已開始」,哪怕在和平的時候。
一、讓我們生活在各自的家園裡
人類用猿猴做試驗,不慎引發猿流感。只有少數對猿流感免疫的人活了下來,聚集在舊金山。但能源即將耗盡,惟一的解決辦法,是遠山裡的一個可以用來發電的水壩。倘若不利用這個水壩發電,不僅人類從前的生活方式無以維繫,他們還不能發出信號,以和別處倖存的人類獲得聯繫。
但人類幾乎滅絕之後,猿猴部落已經生息在了那裡。水壩座落的山谷是它們的家園。人類曾把它們關在實驗室裡百般折磨,他們憎恨人類。
猴群的領袖是一只會說話的猴子,他叫「凱撒」,他是被一個善良的人養大的。他允許馬爾康姆等幾個人進入水壩工作。他明白人類軍火的威力,也明白倘若不允許,人類將立即向猴群宣戰,無數猴子將死於槍炮。
但他的手下,另一隻猿猴科巴,反對凱撒的妥協。他的理由是:猴群應該抓住這個時機,趁人類脆弱的時候進行復仇。而且,人類獲取能源之後,將變得更加不可戰勝,那時猴群可就慘了。
顯然,兩派都有道理。這一仗總是要打的,不過是或早或晚的區別。這是一個窘境,或早或晚,總要有無數猴子死於槍火。就像人類文明內部:資源在那兒,就那麼多,要嘛歸你,要嘛歸我。爭執始終都在。所謂和平,不過是面對彼此的威懾力而不得不按兵不動。我不打你,因為我不想被你打死。和平,是暫時不爆發的火山。
想不被毀滅,只能增加自身獲勝的籌碼。文明之間是這樣,個人之間也未嘗不是這樣。因此,「之間」,是充滿了張力的地帶,它逼迫個體在自身之中不斷地超越自身。
二、寬恕的歸寬恕,復仇的歸復仇
暫時和人類合作,還是趁機攻打人類?這是凱撒和科巴之間的分歧。科巴仇恨人類——甚至之前一天,他和兒子巡視時,偶然撞見的人類(尋找水壩的人)還開槍把兒子打傷了。因此,科已對凱撒的決定咬牙切齒。而凱撒說:「你只從人類那兒學到了仇恨。」
仇恨可以長久地充滿一個人,就像愛。愛和仇恨都讓人獲得力量。但被愛佔據的人是柔和的、包容的,他的力綿延而活潑。仇恨帶來的力則是硬的,僵硬如一根鐵棒,它是死,它不容商量,它具有死亡的絕對性。比如,滿腔仇恨要為帕特克里斯復仇的阿喀琉斯,他如死神般戰無不勝,而他的勝利的終點,正是自己的死亡。
科已從人類的軍火庫偷來機槍,暗中向凱撒射擊。他以為凱撒死了,猴群以為是人類乾的。他號令大家攻打人類,為凱撒報仇。猴群攻佔了人類的高塔,忠於凱撒的人都被他關進了鐵籠子。
科巴命令一隻猿猴殺死俘獲的人,猿猴不從,因為它記得凱撒說過的,仁慈。科巴把那隻記得仁慈的猿猴扔下高塔——電影《鋼琴師》里有個鏡頭,納粹把一個猶太人直接從樓上扔了下去。
而凱撒被馬爾康姆夫婦救活,他爬上高塔,向科巴要回權力。一對一的肉搏中,科已將要掉下深淵,凱撒伸出手,拉住了科巴的手。這時,科巴倒想起了凱撒平時常說的:「猿猴不殺猿猴」。凱撒平靜地說:猿猴不殺猿猴。可你不配做(不是)猿猴。
凱撒鬆開手,讓科巴墜落下去——理智讓人能夠分清,誰是應該被寬恕的,誰是應該被報復的。正如不加思索地報復一切,不過是出於狹隘和魯莽,不加辨析地寬恕所有,更多只是婦人之仁罷了,帶來的將是更多無辜生靈的傷害乃至毀滅。正義,即讓他擁有屬於他的。被寬恕,不屬於科巴。屬於他的,他最終得到了。
三、對抗與和解,辨異與合同
蘇格拉底說,倘若你以為不是以「理想國」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城邦算是「一個」城邦,你就太天真了。那些城邦永遠是兩個,至少兩個:富人和窮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他們之間彼此對立、衝突,很容易因為內部的衝突而造成城邦的瓦解——外力或許只需一根稻草。
人猿之戰便正是如此。人類分成兩派,馬爾康姆為首的親猿派和德里弗斯為首的殺猿派,在影片尾聲,他們的對立升級為馬爾康姆拿著機槍威脅德里弗斯,讓他不要炸塔樓,給凱撒一點時間,收回科巴發動的佔領。但德里弗斯認為這不可理喻。他自殺性地拉了引爆線,認為自己是在拯救人類。
如前所述,猿猴也是分成兩派,他們之間,同樣是你死我活的對抗。人群和猴群,還真沒那麼大的不同。都有善意的,也有惡意的;有教條的,也有能夠睜開眼睛看,看事物究竟如何在面前呈現自身的——這個電影講的其實就是兩個人群或兩個國家的故事。
這部電影最觸動我的地方,是敵對雙方能夠在對抗性張力之中,仍然在不經意間向對方流露出善意。比如那隻剛出生不久的小猴,跳到薩拉的肩上,好奇地打量那些新鮮的物事,薩拉和亞歷山大的目光從驚愕逐漸變得慈愛。放下了人與人(猿)之間的算計和戒備,純粹的自然,便得以湧現。
就像整部《伊利亞特》,我只愛最後一捲。特洛伊國王普里亞冒死去阿喀琉斯的帳篷里,請求他允許自己帶回兒子赫克托的屍體。無論帶著怎樣的仇恨,阿喀琉斯和普里亞短暫和解了,他們共進晚餐的時候,向對方溫和地微笑——儘管他們知道,戰爭並沒有結束。
我不喜歡無差異的東西。因為智慧首先便存在於分辨差異,哪怕孕育於智慧的看似博愛的情懷,也並非不明差異,而是有足夠的洞察力,讓他得以抵達差異背後的根基處的共同或共通之源。我也不喜歡因為弱小而無力反擊的原諒,這不過是自欺的說辭罷了。只有強大者才有能力原諒——在早已開始的戰爭中,那個不攻擊,卻永不被擊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