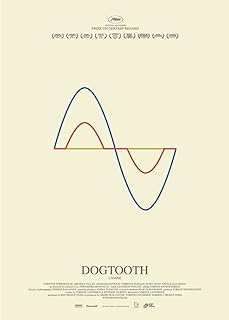2015-11-18 22:42:02
是極權,還是伊甸園——禁果被摘下以前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一 . 詞語
大海(sea)的意思是木扶手皮椅;高速公路(highway)的意思是強風;遠足(excursion)是一種非常耐用的材料;獵槍(shotgun)是一種漂亮的白色小鳥……
這不是一段詩歌,而是一盤教學錄音帶。正在學習中的是年輕的姐弟三人。廁所牆上潔白的瓷磚使畫面顯得異常乾淨、整潔。希臘導演歐格斯·蘭斯莫斯善於運用有技巧的鏡頭語言,《犬齒》整部影片呈現出一種精緻、平和、優雅、古典式的意境。
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在他的著作《哈扎爾辭典》中寫道:「耶和華創造世界用的是動詞而不是名詞。」動詞是邏輯,是法律,是規則,是一切創造。而行為本身必先於被創造的世界而存在。名詞的使命在於同人名相對應,指稱各種事物,方便進行歸類和整理。動詞是源自上帝的,而名詞是屬於人的,它不穩定、不精確、可疑,並且短暫。
在《犬齒》中,孩子們被父母囚禁在家的圍欄里,他們所認識和理解的一切事物都依賴於父母的詮釋。世界是危險的,為了避免自己的家庭陷入險境,他們不惜將整個外部世界與自己的孩子隔絕。而恰恰是為了迴避解釋那個被隔絕的世界,父母篡改了一些詞語的名稱,或者重新定義它。比如,「電話」的意思是調料瓶,「賤貨」是一盞大燈,「殭屍」是一朵小小的黃花,而女人的陰部則被稱為「鍵盤」。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名詞的脆弱和模糊,一旦它脫離了它所依賴的客觀系統存在,它就徹底變成了虛幻,變成了夢境。當電影中的小兒子蹲在草地上興奮地向母親大喊「媽媽,我發現了兩個殭屍!」的時候,我感覺到的並不是荒謬,而是純真。如果我們笑了,大概是出於恐懼,因為這差錯不過是另一種可能存在的無比客觀的真實。
因此,在這部電影中,家庭中的所有人都是沒有名字的。他們的名字從未被說出,而只以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稱呼來代替。唯一出現的人物名字便是克里斯蒂娜。父親把這個女人邀請到家裡,與自己的兒子性交。這女人的名字也許可以作為一種象徵,聯繫著那個由意義被限定的龐大的名詞系統所構成的外部世界。
女孩發明了一個遊戲,而當被問到這個遊戲叫什麼名字時,女孩持續沉默了許久,然後說:「不知道。」命名權掌握在父母手裡,這當然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集權主義。每一次父親外出購物回家,都要在大門外將所有商品的標籤統統撕掉,他不希望孩子對事物的認識取決於外面那個世界的定義。他可以自己去定義。「威脅到我們的那個動物是一隻『貓』,世上最危險的動物,他吃肉,特別吃小孩肉,用爪子將受害者撕傷以後,他就用鋒利的牙齒,將受害者的臉和整個身體狼吞虎嚥地吃掉。」
二 .遊戲
很久以前,在上帝建造的伊甸園裡,亞當和夏娃在怎樣地生活?秩序已經建立,神的規則非常完美,一切應有盡有。在秩序被破壞以前,烏托邦存在過。那是一個由規則建立和統治的沒有善惡之別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人的生活由基本的物質元素和遊戲組成,因為在遊戲中不要求主體意識(比如道德)的參與,只需要規則。
影片中這個家庭就類似於這樣一個烏托邦,遊戲成為三個年輕人生活的主要內容。他們自己創造遊戲,那是些最原始的遊戲,擁有極為簡單明確的規則。比如忍耐力遊戲,三個人同時把手指伸進熱水裡,誰堅持的時間最長誰就算贏;醫生和病人的遊戲,兩個女孩玩兒過了火,同時吸入麻醉劑,誰第一個醒來就是勝利者;溺水急救遊戲,一個人沉入水中,模擬溺水者,兩人在旁邊觀看等待,等他的身體漂浮起來,便將他救上岸,用按壓胸口、人工呼吸的方式使他甦醒……對於遊戲的認真程度,他們與我們社會中那些最小的孩子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旦嚴肅地對待這些遊戲,遊戲便成為一件嚴肅的事情,成為他們模仿和接近彼此,並不脫離這個世界的方法。
當影片中的小女兒認真地坐在那裡,一邊用剪刀剪斷芭比娃娃的腳掌,一邊模擬手中的玩偶發出刺耳的尖叫,那不應當被理解為出於一種壓抑。那是每一個對世界尚未有足夠經歷的兒童都可能會進行的遊戲。乾淨柔和的畫面,教學錄音帶用一種平直無表情的語調持續地發出聲音,女孩不斷讓自己進入玩偶疼痛的世界裡。這看起來就像一個巫術。值得思考的反而是另一個問題,為何成人的世界會拒絕再次進行這種遊戲?
從天上掉落的飛機,在影片中非常具有超現實的意味。飛機的掉落,是父母在孩子的世界中刻意製造的偶然,就像一個奇蹟。父親悄悄地把魚放入游泳池的水中。他不僅創造秩序,他還創造神奇。
競爭也是必要的,這是遊戲之所以吸引人投入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有時候,父親會為他們組織這種競爭性的比賽,例如潛水,看誰在水中堅持的時間最長。父親的競爭遊戲是有獎勵的,那些花花綠綠的貼紙,成為孩子們受到認可、讚揚和鼓舞的勝利的象徵。父親會統計每個人得到貼紙的數量,得數最多的人將贏得晚間家庭娛樂活動的選擇權。
在家庭晚餐之前,,他們對於自己的著裝重視得不合常理。晚餐需要盛裝出席,每個孩子都認真挑選著合適的衣服,並且樂在其中。這何嘗不是另一個遊戲。父親是智慧的,通過將遊戲變得嚴肅而神聖,他使孩子們在這個封閉的家庭圍欄中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一切。
三 . 狗
狗這種動物,以及它標誌性的身體姿態、動作(例如舔舐)、聲音,在這部影片中究竟隱喻著什麼?是一種蟄伏於人身體深處,置於權利之下所發散出來的奴性?還是為了體現一種缺乏理性和想像力的交流方式最終淪落為動物性的生理本能?也許兩者都有,但卻並不全面。
父親去看望那隻被自己送到馴養場訓練的狗「雷克斯」。在辦公室裡,訓練場的負責人向父親做出解釋:「訓狗,就像捏陶泥,我們的工作就是將他塑造成形。……它需要我們大量的工作,耐心和關心。……我們在這兒,制定出狗應該具有的行為。」這番話可以理解為「狗的教育方法」。那麼,對人的教育方法呢?
若用「強權」或者「極權」之類的字眼來對影片中的事實進行描述是不恰當的,因為任何行為教育都包含著施加權力和意圖塑造的目的。塑造一條狗和塑造一個人,本質上並無多大區別。也許區別僅僅在於方法。用一種強硬的、軍事化的方法,或是用一種溫和的、引導性的方法。顯然,父親所選擇的是前者。所以當那個負責人反覆詢問「你明白嗎?」的時候,父親面無表情卻無比爽利地答道:「明白。」
他當然明白,因為他正是這樣做的。這種方法看起來冷酷、專制、沒有人情味,但是同樣需要付出「大量的工作,耐心和關心」。這付出如果不一定是出於愛,至少也是出於責任感。在作為整個家庭的主導的父親身上,對於自己家庭領地的捍衛,對家人的極端的保護,就凝聚在這看似過份的責任感之中。而這恰好是我所要補充的,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都認同並讚揚,但在這部影片中卻被忽略的狗的另一個特徵——守護、捍衛與忠誠。
那個被虛構的、生活在圍欄之外的「哥哥」死去了,父親說,他死於一隻貓的攻擊。家庭成員顯示出了無可置疑的團結。「親愛的哥哥,我從沒想到事情會錯成這樣。我希望你能在我的捍衛下活下來,但危險真的太多了……」
於是,孩子們被教會以狗的姿態趴在地上,學會了犬吠,用以對付家庭隨時可能面臨的危險的入侵。他們學會了服務,並且取悅他人(兒子為父親畫眉毛,女兒為父親剪指甲,以及像動物一樣互相舔舐),這些特性都可以從狗的身上找到。而「犬齒」,作為狗身上最鋒利和堅固的武器,用來隱喻父親捍衛自己家庭的決心。只有當犬齒脫落了,孩子才被允許駕駛汽車離開家。而只有等那顆脫落的犬齒再長出來,他們才能學習駕駛。
四 . 性
女人克里斯蒂娜的到來,的確給這個家庭帶來了影響。為了讓兒子擁有必須的性生活,父親將這個女人從外面帶回家。這是一個嘗試,更是冒險。雖然已經做了許多防範,卻依然徒勞。
性,在這個家庭中,帶有一種「必行之事」的意味。它不包含任何激情與幻想,不包含情感,也不包含任何道德內容。它只是兩個身體自然的結合,實現兩性被創造之初所意味著的結合的必要或可能。性在這個家庭規則系統之中,沒有被賦予過多可被探索和關注的空間。因此,父親和母親之間的性,兒子與女人之間的性,看上去都只是毫無意趣的身體活動,乾澀、荒蕪,卻並不骯髒,也不混亂,更像是一種將身體本能正常秩序化的結果。
然而,女人克里斯蒂娜帶來了她的慾望。這慾望來歷不明,似乎從一個撩人的繁花似錦的公園兀自涉入一片荒涼場地,看上去尷尬而突兀。克里斯蒂娜要求女孩舔她的下體,條件是以發卡作為交換。為了得到發卡,女孩同意了。但克里斯蒂娜的慾望對她來說什麼都不是,她沒有從她身上理解到慾望,她只理解了交易。
於是,舔舐成為女孩們學會的交易手段,開始在家庭成員之間進行。大女兒又用這種方法從克里斯蒂娜那裡換來了她想要的錄影帶。(這個女孩從一開始就對外界抱有好奇心,從她對克里斯蒂娜行為的注視,以及後來對克里斯蒂娜要求舔舐的交易行為進行的拙劣的模仿都可以看出。)從錄影帶中,她認識了布魯斯(應該是Bruce Lee李小龍),並且開始產生意圖衝破家庭的禁錮。這一切都成為父親的嘗試最終失敗的證據,導致父親最後只好選擇一種看似極端非理的方法,讓自己的兒子與自己的女兒性交,以維繫家庭的安全與完滿。
然而,影片中的亂倫畫面,並沒有散發出罪惡的氣息。對於大女兒來說,那更像是一種服務,在這個家庭本來就超越現實的秩序之下成為合理。這使我想起羅伯·格里耶的文學作品《情感小說》,整部作品由亂倫、戀童、性虐等內容拼湊而成,而作家的文字氣質與這部影片的氣質何其相像。羅伯·格里耶在介紹他這部作品時的描述也許同樣可以作為觀看這部電影時可使用的一個角度。他說:「這篇敘述文字是某一種成人童話,這讓它有很多次機會超越真實性的律法。然而寫作它時對準確性有著精心考量,讓它能與最嚴謹的現實主義相似,於是超越適度的律法。它斷然是關於別的東西的。另一種適度和另一種真實性。」
五 . 愛
與性所佔據的微弱、沉悶而僵硬的空間相比,愛的存在,支撐和印證著這個家庭延續的合理性。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信任,長久的陪伴和依賴,以及對那個不存在的死去的「哥哥」的悲切悼念,都體現著這一點。
在晚餐後「聽爺爺唱歌」的娛樂環節中,家庭的快樂到達了高潮。當然,父親唸出的歌詞是被篡改過的:「爸爸愛我們,媽媽愛我們,我們愛他們嗎?愛,我們愛他們……」孩子們滿懷喜悅地聽著,眉眼間幾乎洋溢著感動。最後,一家人隨著音樂歡樂地跳起舞來。
這也許很容易提醒人們回想起一些歷史時期,整個社會陷入的集體狂熱。這種狂熱產生於某種已被猛烈批判過的危險的意識形態。然而當這種愛和熱情浮現、湧動於一個平常的家庭之中,我們便有了太充足的理由去原諒它。
如果說這部影片包含著批判,我更願意將其理解為是針對現有的家庭組織,而不是某種龐大的政治理想。我們現在能看到的絕大部份家庭,不是正處於同樣的境地嗎?何況導演並沒有過多地進行批判,只是採取了一種較為極端的方法將其呈現。而但凡是將整部影片的內涵引至那個不可觸碰的歷史陰影或那種危險意識形態的評論,或許是被自己的思維引導著落入了一個並不存在的陷阱,而迴避了我們真正身處其中的微縮的、更加飽滿而浮動著危險的現實。這也是這部電影不同於其他更多反烏托邦類影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這部影片裡沒有真正被傷害的角色,只有觀眾對於傷害的想像。
亞當和夏娃被塑造出來,安置在伊甸園裡,但他們被要求不能去吃智慧樹的果子,這是上帝所設置的界限,也是神的權力的體現。當然,這相當於將人所有可能擁有的自由置之於不顧。但如果人類的痛苦和人世的黑暗最終將追溯至偷食禁果所獲得的本不該有的智慧,那麼最初上帝對人所實施的權力的控制便可以被理解為無比的「善」(即是「愛」)。然而人違背了秩序,使這愛落了空。如果我們真的要去控訴和指責影片中的父親,又何必千百年來滿懷鄉愁地、像個迷失的孩子一樣苦苦呼喚那個逝去的伊甸園呢?
在一場「最後的晚餐」式的宴會過後,在一場滿懷絕望和躁動的、不知疲倦的、著魔般的舞蹈過後,為了獲得離家的資格,大女兒最終用鎯頭敲碎了自己的犬齒。這是一次自殘式的自我救贖。而這自殘的行為究竟對這個女孩來說意味著什麼?脫離父母的愛與保護,脫離家庭秩序的約束究竟意味著什麼?「自殘」在這裡提示著,打破秩序之後她將面臨的傷害,或許不僅僅是打碎一顆犬齒那麼簡單。
因此,當電影最後的畫面定格在女孩藏身的汽車後備箱時,沒有人,沒有一個觀眾能夠為她指出,通往自由的道路究竟應該怎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