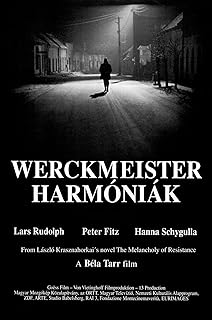電影訊息
鯨魚馬戲團--Werckmeister harmoniak
編劇: Laszlo Krasznahorkai
演員: Lars Rudolph Peter Fitzpatrick 漢娜席古拉 Janos Derzsi
鲸鱼马戏团/残缺的和声/和睦相处
導演: 貝拉塔爾 Agnes Hranitzky編劇: Laszlo Krasznahorkai
演員: Lars Rudolph Peter Fitzpatrick 漢娜席古拉 Janos Derzsi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6-04-01 08:00:36
用長鏡頭完爆蒙太奇——簡析《鯨魚馬戲團》中的導演手法
第一次看《鯨魚馬戲團》是在電腦上,兩年半以前還是一個剛開始學看電影的小白,什麼都不懂,只是感性地對他的長鏡頭產生了一種迷戀,這種迷戀跟在侯孝賢、安哲等人身上引發的化學反應完全不同。今天再次在北電大螢幕上看,看的是膠片,眼睛像被甩了糨糊一刻也不想離開螢幕。貝拉·塔爾的長鏡頭本身富有極大張力,這種張力概括來講由三個因素構成:精確的場面調度、主導的運動鏡頭、反覆變奏的音樂。
如果要問貝拉塔爾的場面調度有何特色,我想大概可以用精確和唯美來形容,幾乎每一幀截圖都可以用來做屏保。在整部片子中有600多名非專業群眾演員,他們的走位和表演都紋絲不亂得讓人震驚,這在醫院暴亂和廣場兩場戲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在第一個鏡頭中,群眾開始表現日全食之舞瘋狂地旋轉,男主混在他們中間指揮著他們,像是一群醉鬼中唯一一個藝術家,是最格格不入的孤獨的一個。黑白色彩的表現和燈光的運用也是他場面調度中的重要部份。當第一個鏡頭男主示範完真人日全食後,第二個鏡頭是男主在空蕩蕩的馬路上走過一盞燈,燈光越變越窄最後變成了一條細線,是對日全食的隱喻,極其富有美感。當男主第二次趁著夜色偷偷溜進貨櫃看鯨魚,全黑之中有一束光照在鯨魚令人同情的眼睛上,而後來男主偷聽馬戲團負責人和「王子」的談話時,也有一束光準確地照在他的眼睛上,鯨魚和男主形成了隱喻上的關聯。當然關聯不止這一處,39個有限的蒙太奇中至少有兩處都在強調這種對應關係。貝拉塔爾極其重視黑與白之間的對比,在醫院暴亂這場戲中,在漆黑色調的醫院一系列打砸搶燒之後,暴民們拉開了浴室白色的簾子,一個渾身乾癟的老頭站在浴缸里垂著雙手和無法勃起的陰莖,整個底色是全白的,極其刺目和耀眼讓人無法適應,就像是看到了天堂裡的耶穌而耶穌如今已經成為了一個無助的老頭子。
主導的運動鏡頭大概是貝拉塔爾長鏡頭最大的特色了。平均時長3分鐘的鏡頭可以平穩地遊走在人物之間,穿梭過一個又一個空間,環繞、旋轉、變焦,不停地挑選我們視覺的停留點。記得戴爺在分析《人類之子》時說過,這部電影里長鏡頭中的場面調度和運動鏡頭的戲劇性已經完全可以和蒙太奇媲美,那麼貝拉塔爾這部《鯨魚馬戲團》中長鏡頭抓人的現場感和緊張感則完全可以完爆好萊塢。話說我一直好奇貝拉塔爾的運動鏡頭都是怎麼拍的,上一秒是平穩的不規則運鏡像是用斯坦尼康,下一秒是紋絲不動的固定鏡頭像是用了腳架,再下一秒是穩穩的滑軌即視感,再下一秒又只可能用搖臂,而這些切換是無縫銜接!!同學甚至開始推測是不是滑軌隨拆隨用的……看了貝拉塔爾幾部電影之後已經整個人都凌亂了……無怪乎這部39個鏡頭的片子就用了7個最頂級的攝影師。還是要回到個人認為全片最牛逼的一個鏡頭上來,即醫院暴亂。當鏡頭跟隨著暴民進入一個個病房不同的空間暴力毆打無辜的病人,鏡頭沒有做一絲一毫切換,真實的時間和真實的暴力讓人難以忍受。當暴力結束一片狼藉,長鏡頭回到一個角落,男主躲藏在後面,一雙眼睛裡滿是憂傷和震驚——原來他一直在看這一切。在這時,客觀鏡頭被巧妙地轉換為了主觀鏡頭。另外,仔細看貝拉塔爾的運動鏡頭在表現同一處場景時,幾乎沒有一樣的,在這部片子裡不是很典型,《都靈之馬》裡父女倆對坐吃馬鈴薯就很典型了,四次吃馬鈴薯就換了四個機位。但《鯨魚馬戲團》中有兩個鏡頭的運動調度卻很酷似,這是貝拉塔爾有意為之:之前有一個鏡頭是鄰居看著男主離去,背後是他開的鞋店廣告牆;之後有一個鏡頭是鄰居的妻子看著男主離去,背後是她家的鞋店的廣告牆。這兩個鏡頭之間發生了什麼?鄰居拉尤什先生已經在暴動中死去了,而他的妻子還不知道,久久注視的目光中有對男主的擔憂和丈夫歸來的期盼。這一形式上的相似讓人聯想其拉尤什先生那個鏡頭,產生物是人非的淒涼感。
為什麼談到貝拉塔爾的長鏡頭不得不說其電影配樂?我想大概米夏伊‧維格(Mihály Vig)的音樂一直是其電影靈魂的一部份,這位貝拉塔爾的御用作曲一直高度參與了和貝拉塔爾合作的每一部電影的初期創作,甚至在電影拍攝現場演奏以營造出電影需要的情緒。Vig的配樂跟貝拉塔爾的電影在風格上同樣的優雅、沉穩、簡潔乾淨,或者說相得益彰。在每一部中電影中,他的配樂都幾乎只有一個調子,《都靈之馬》《倫敦來的人》都是這樣,以反覆的變奏和提琴加入的和弦來避免單調感,但這種重複幾乎和呼吸的頻率一樣自然流暢,與貝拉塔爾攝影機的緩慢運動同步。他的音樂密密麻麻鋪滿了貝拉塔爾的電影,已經和他極其冷靜、客觀的鏡頭語言融為了一體,少有情緒表現功能,更多是為人物營造一種生存環境。然而在《鯨魚馬戲團》中,在那個乾淨優美的鋼琴曲調之外另有一個用來抒情的旋律,富有強烈的煽情色彩地出現了兩次:一次是在醫院暴亂浴簾掀開,皺巴巴的老頭子渾身赤裸地、無助地垂著雙手,病懨懨的身體肋骨突出,巨大的震撼簡直讓人落淚;另一次是在結尾處,巨大的鯨魚標本被暴亂的煙火掀翻在滿地狼藉之中,跟男主一樣孤獨。很少在電影中發言的貝拉塔爾此處突兀地用音樂情緒展現了自己強烈的在場,寄予了深深的悲憫和譴責。接下來就可以分析主題了。
貝拉塔爾在《鯨魚馬戲團》中清晰地劃分了兩大對立的派別:以「王子」為首的、受「王子」蠱惑的暴民,和以唐德嬸嬸、警察局長這一對勾連的「狗男女」代表的鎮壓暴民的官方權威。每個人都在憂心忡忡城鎮的未來,但他們的行為有讓城鎮變得更好嗎?瘋了的男主、死去的鄰居拉尤什、醫院裡的病人代表了為數更多的平民/「貧民」,他們成了兩大派別之下的犧牲品,像是對沖的鋼塊瞬間把螺絲釘們齏成粉末。在這其中,男主有一點特殊,他更像是一個來自平民的哲學家。他關心地球運轉和日全食,家中牆壁上掛的是世界地圖。所有的人都在抱怨鯨魚帶來了城鎮的厄運,只有他為上蒼這種美麗的造物驚奇不已。他孤獨地去看望鯨魚,當和鯨魚的眼睛對視時似乎找到了唯一的夥伴,而這夥伴卻已經從本來所在的海洋販賣到了貨櫃里,不會說話、不會呼吸、被製作成了標本。這和男主最後的結局類似,被關在了精神病院裡,沒有了思想,沒有了語言,只能吟哦出一些無意義的音節。整部影片,是他從一個順從的孩子成長為一個見證了暴力摧殘的青年,而他的結局卻是變瘋,似乎在預示哲學家(愛智者)唯一的出路。另外,他的音樂家叔叔也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他比平民們更有才能、更聰明,始終希望自己能游離在這場鬥爭之外,但最後卻依然沒能倖免地被波及失去了家園。從這個人物類型上可以體味到貝拉塔爾的嘲諷。
最後,這部電影依然有很多晦澀之處,比如,為什麼原題目叫做《殘缺的和聲》?和影片中音樂家叔叔說的那段和聲的演講有何關係?鐵軌上方盤旋的那架直升機是用來做什麼的?男主到底為什麼會變瘋?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討論。
如果要問貝拉塔爾的場面調度有何特色,我想大概可以用精確和唯美來形容,幾乎每一幀截圖都可以用來做屏保。在整部片子中有600多名非專業群眾演員,他們的走位和表演都紋絲不亂得讓人震驚,這在醫院暴亂和廣場兩場戲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在第一個鏡頭中,群眾開始表現日全食之舞瘋狂地旋轉,男主混在他們中間指揮著他們,像是一群醉鬼中唯一一個藝術家,是最格格不入的孤獨的一個。黑白色彩的表現和燈光的運用也是他場面調度中的重要部份。當第一個鏡頭男主示範完真人日全食後,第二個鏡頭是男主在空蕩蕩的馬路上走過一盞燈,燈光越變越窄最後變成了一條細線,是對日全食的隱喻,極其富有美感。當男主第二次趁著夜色偷偷溜進貨櫃看鯨魚,全黑之中有一束光照在鯨魚令人同情的眼睛上,而後來男主偷聽馬戲團負責人和「王子」的談話時,也有一束光準確地照在他的眼睛上,鯨魚和男主形成了隱喻上的關聯。當然關聯不止這一處,39個有限的蒙太奇中至少有兩處都在強調這種對應關係。貝拉塔爾極其重視黑與白之間的對比,在醫院暴亂這場戲中,在漆黑色調的醫院一系列打砸搶燒之後,暴民們拉開了浴室白色的簾子,一個渾身乾癟的老頭站在浴缸里垂著雙手和無法勃起的陰莖,整個底色是全白的,極其刺目和耀眼讓人無法適應,就像是看到了天堂裡的耶穌而耶穌如今已經成為了一個無助的老頭子。
主導的運動鏡頭大概是貝拉塔爾長鏡頭最大的特色了。平均時長3分鐘的鏡頭可以平穩地遊走在人物之間,穿梭過一個又一個空間,環繞、旋轉、變焦,不停地挑選我們視覺的停留點。記得戴爺在分析《人類之子》時說過,這部電影里長鏡頭中的場面調度和運動鏡頭的戲劇性已經完全可以和蒙太奇媲美,那麼貝拉塔爾這部《鯨魚馬戲團》中長鏡頭抓人的現場感和緊張感則完全可以完爆好萊塢。話說我一直好奇貝拉塔爾的運動鏡頭都是怎麼拍的,上一秒是平穩的不規則運鏡像是用斯坦尼康,下一秒是紋絲不動的固定鏡頭像是用了腳架,再下一秒是穩穩的滑軌即視感,再下一秒又只可能用搖臂,而這些切換是無縫銜接!!同學甚至開始推測是不是滑軌隨拆隨用的……看了貝拉塔爾幾部電影之後已經整個人都凌亂了……無怪乎這部39個鏡頭的片子就用了7個最頂級的攝影師。還是要回到個人認為全片最牛逼的一個鏡頭上來,即醫院暴亂。當鏡頭跟隨著暴民進入一個個病房不同的空間暴力毆打無辜的病人,鏡頭沒有做一絲一毫切換,真實的時間和真實的暴力讓人難以忍受。當暴力結束一片狼藉,長鏡頭回到一個角落,男主躲藏在後面,一雙眼睛裡滿是憂傷和震驚——原來他一直在看這一切。在這時,客觀鏡頭被巧妙地轉換為了主觀鏡頭。另外,仔細看貝拉塔爾的運動鏡頭在表現同一處場景時,幾乎沒有一樣的,在這部片子裡不是很典型,《都靈之馬》裡父女倆對坐吃馬鈴薯就很典型了,四次吃馬鈴薯就換了四個機位。但《鯨魚馬戲團》中有兩個鏡頭的運動調度卻很酷似,這是貝拉塔爾有意為之:之前有一個鏡頭是鄰居看著男主離去,背後是他開的鞋店廣告牆;之後有一個鏡頭是鄰居的妻子看著男主離去,背後是她家的鞋店的廣告牆。這兩個鏡頭之間發生了什麼?鄰居拉尤什先生已經在暴動中死去了,而他的妻子還不知道,久久注視的目光中有對男主的擔憂和丈夫歸來的期盼。這一形式上的相似讓人聯想其拉尤什先生那個鏡頭,產生物是人非的淒涼感。
為什麼談到貝拉塔爾的長鏡頭不得不說其電影配樂?我想大概米夏伊‧維格(Mihály Vig)的音樂一直是其電影靈魂的一部份,這位貝拉塔爾的御用作曲一直高度參與了和貝拉塔爾合作的每一部電影的初期創作,甚至在電影拍攝現場演奏以營造出電影需要的情緒。Vig的配樂跟貝拉塔爾的電影在風格上同樣的優雅、沉穩、簡潔乾淨,或者說相得益彰。在每一部中電影中,他的配樂都幾乎只有一個調子,《都靈之馬》《倫敦來的人》都是這樣,以反覆的變奏和提琴加入的和弦來避免單調感,但這種重複幾乎和呼吸的頻率一樣自然流暢,與貝拉塔爾攝影機的緩慢運動同步。他的音樂密密麻麻鋪滿了貝拉塔爾的電影,已經和他極其冷靜、客觀的鏡頭語言融為了一體,少有情緒表現功能,更多是為人物營造一種生存環境。然而在《鯨魚馬戲團》中,在那個乾淨優美的鋼琴曲調之外另有一個用來抒情的旋律,富有強烈的煽情色彩地出現了兩次:一次是在醫院暴亂浴簾掀開,皺巴巴的老頭子渾身赤裸地、無助地垂著雙手,病懨懨的身體肋骨突出,巨大的震撼簡直讓人落淚;另一次是在結尾處,巨大的鯨魚標本被暴亂的煙火掀翻在滿地狼藉之中,跟男主一樣孤獨。很少在電影中發言的貝拉塔爾此處突兀地用音樂情緒展現了自己強烈的在場,寄予了深深的悲憫和譴責。接下來就可以分析主題了。
貝拉塔爾在《鯨魚馬戲團》中清晰地劃分了兩大對立的派別:以「王子」為首的、受「王子」蠱惑的暴民,和以唐德嬸嬸、警察局長這一對勾連的「狗男女」代表的鎮壓暴民的官方權威。每個人都在憂心忡忡城鎮的未來,但他們的行為有讓城鎮變得更好嗎?瘋了的男主、死去的鄰居拉尤什、醫院裡的病人代表了為數更多的平民/「貧民」,他們成了兩大派別之下的犧牲品,像是對沖的鋼塊瞬間把螺絲釘們齏成粉末。在這其中,男主有一點特殊,他更像是一個來自平民的哲學家。他關心地球運轉和日全食,家中牆壁上掛的是世界地圖。所有的人都在抱怨鯨魚帶來了城鎮的厄運,只有他為上蒼這種美麗的造物驚奇不已。他孤獨地去看望鯨魚,當和鯨魚的眼睛對視時似乎找到了唯一的夥伴,而這夥伴卻已經從本來所在的海洋販賣到了貨櫃里,不會說話、不會呼吸、被製作成了標本。這和男主最後的結局類似,被關在了精神病院裡,沒有了思想,沒有了語言,只能吟哦出一些無意義的音節。整部影片,是他從一個順從的孩子成長為一個見證了暴力摧殘的青年,而他的結局卻是變瘋,似乎在預示哲學家(愛智者)唯一的出路。另外,他的音樂家叔叔也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他比平民們更有才能、更聰明,始終希望自己能游離在這場鬥爭之外,但最後卻依然沒能倖免地被波及失去了家園。從這個人物類型上可以體味到貝拉塔爾的嘲諷。
最後,這部電影依然有很多晦澀之處,比如,為什麼原題目叫做《殘缺的和聲》?和影片中音樂家叔叔說的那段和聲的演講有何關係?鐵軌上方盤旋的那架直升機是用來做什麼的?男主到底為什麼會變瘋?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討論。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