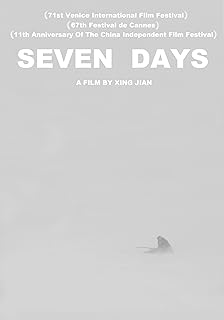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6-08-09 04:19:44
掀一掀極簡主義的蓋子
的確,極簡敘事發生在許多大師級導演的電影作品中。極少的人物、簡單的場景、壓縮的情節、節約的對白、寓言化的意向以及形式感的影像語言等等,往往在不同的導演手中構建出不同的語言體系,被公認為可以代表「作者電影」,以對抗好萊塢的類型片體系。不過需要知道的是,極簡主義(Minimalism)最早奉行於藝術創作中時,就被敏感的批評家們提醒,它同時極易令作品以驚奇效果代替藝術審美,讓創作者以為找到了一條捷徑,沒有以「極簡」的手法抵達事物的「本質」,只迎來譁眾取寵的短暫喧譁。
73分鐘的黑白片《冬》極簡的形式追求意圖明顯。漫天飛雪的長白山山腳下,七天之內,一個老人與一條魚、一隻鳥和一個小孩兒之間一段無對白的寓言故事。加上古琴和梵音的配樂構思,似乎是以禪意為托,描摹生命孤獨的存在,推演人性的貪慾。然而通片讀過,卻發現極簡的蓋子下面,是風格與內容的對立,人物的缺乏邏輯,對於善與惡、貪與欲的缺乏判斷和價值混亂。禪意沒有表達,功利心偷梁換柱地意外側漏。影片甚至為觀影體驗帶來了意外的侵害,其原因並不是年輕導演對生命與人性的理解深度不夠就急於表達,而是對電影這一媒體的視覺倫理完全喪失敏感度,對視覺上的冒犯與暴力渾然不覺。而這種渾然不覺又與影片中老人的惡同質,影片文本內部的寓言是失敗的,但影片本身之於當下社會,卻可以解讀為一個可怕的影射。
一般來講,影片風格的確立來自開頭和結尾。在《冬》中,當然是那為攝製帶來極大挑戰的白雪皚皚的長白山景地。影片首先用3分多鐘極具視覺衝擊力的雪景定調,幾聲叮咚的古琴聲後,鏡頭由遠及近調用航拍、遠景、近景、靜態特寫描摹一個唐詩中「獨釣寒江雪」的老人,再從特寫回到近景、中景、遠景、大遠景,加深渲染暴風雪中老人煢煢踽踽的處境。逆著暴雪,迎著風口,如此冰天雪地的殘酷環境中,老人物我兩忘地釣魚,這是影片的基調,也是故事的出發點。觀眾勢必會產生疑問:老人如此自在的生存態度是如何造就的?影片結尾老人更是化身一隻鳥,一格仰面為山的雪景畫面後,飛入惟余莽莽的天地間,在《八吉祥頌》的藏地梵音下,回應片首。
然而如此唐詩宋詞水墨山水畫的景片背後,這個老人並非修行有道。鏡頭跟著老人進入木屋內景後,隨著那貼近耳邊的喘息聲越來越壓抑刺耳,隨著鳥與小孩的相繼出現,這形象氣質俱佳的世外高人怎麼成了一個自私殘忍的猥瑣大爺了?佛稱貪淫致老,瞋恚致病,愚痴致死,除三得道。貪淫、瞋恚與愚痴,老頭兒幾天內把事幹全了。
影片將基本場景分成對立的兩部份:外景是高光雪域,內景是低調木屋。老人的飾演者王德順現年80歲,因練健美、走T台成為網路紅人,並活躍於近年的幾部國產片中。觀眾很快會發現,這個老人提上魚缸進入木屋後,並不能回答片首帶來的關於艱苦環境下生存態度的問題。此後,老人在外景雪天裡是釣魚/放生、救鳥/悅鳥、尋孩兒/念孩兒;在木屋暗室裡則是嚼馬鈴薯、吸溜粥;一日沒釣上作伴兒的魚晚上就暴砸鏡子、輾轉自慰;然後來了隻鳥馬上把反覆放生的魚屠首割肉;來了個小孩馬上就把逗他嬉笑眼開、捉蟲報恩的鳥活活生烤;不接納小孩時隨意推搡,陪他睡了一晚為他做什麼都成;小孩跑了就委屈地想老婆想到了又是哭不自己又是幻覺不斷——可謂貪瞋愚痴,患得患失。這已經完全偏離了預設。並且為影片帶來顛覆性的置疑:如此狀態的人怎麼可能一個人活到那麼老?風吹草動就得殺人放火啊。牆上的照片顯示他的妻子年輕早亡,他並無子女親人,可如此狀態的人又怎麼可能鰥寡孤獨這麼多年?並且怎麼可能離群索居,還選擇那麼艱苦的環境?
一個定調為禪意詩境的影片不是不可以討論人性的殘酷。金基德的《春夏秋冬又一春》,寧靜超然的山水景物與其中人物的罪與貪、暴力與死亡並不衝突,並且相互觀照,共同實現主題表達。而在《冬》的冬景,刻意營造了東方美學意境,不但沒對內容髮生關係,反而是相悖。《都靈之馬》的視覺風格與它們相反,但是人家陰鬱的影調和乏味的運鏡,與影片中骯髒羸弱的老馬、粗鄙邋遢的內景是統一的,包括平庸殘疾的人物走不出遠景中的一棵樹,都與「絕境中消磨活力、放棄抗爭」的主題有關。
換個角度講,《冬》的問題還出在它極簡主義地讓一個人物同時承載三個敘事角色。寓言故事中往往將敘事者(敘事視點)與惡人的故事以及故事的代入者保持距離,在《冬》中敘事者、代入者與惡念的投射對象合一了。試想將《農夫與金魚的故事》中第三人稱改為第一人稱,農夫與他的老太婆合為一人,貪婪者不再是一個肥胖粗魯的老太婆,而是一個高大帥氣的青年。故事就變成這樣:天大地大,我撤網打魚,一天網到一條不平常的金魚,她答應我,只要放了它,要什麼都給。我要了又要很多東西,她都給,我最後要做海上霸王,要她伺候我,她再也沒搭理我。這時,「我」直接淪為喪失可信性的傻缺,湯姆蘇講的寓言,效果直降為零。
《春夏秋冬又一春》則變成這樣講:我小時候將石頭拴在小動物們身上,害死了魚和蛇;我青春期的時候迷上姑娘,放棄了做和尚;我青年的時候由於殺人逃回廟裡還是被抓了回去;我中年的時候想回到寺廟修行,在冰上鑿洞,又淹死了個女人;我老年的時候撫養的女人之子長大了,他繼續虐待小動物;最後,我呆的地方佛光萬丈,普度眾生。這時,「我」已經自以為是「蘇」到神魔不分,還談何禪理。
《冬》中無論是魚,還是鳥,小孩還是女人,都成為老人解乏孤獨的他者,在這個層面上他實現了眾生平等。老頭兒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害我孤獨者,佛來斬佛,魔來斬魔。這樣的修行最後還能度化成鳥,大地萬物皆以我為形。這老頭兒「蘇」到能行多大的膽啊!假設影片除獨釣的老人外還有一個年輕人,來行孤獨中各種難以按捺的惡,影片在敘事上將合理得多。當然,這就太金基德了。
魚和鳥明明在影片中已被人格化,甚至作為角色主演在字幕中被強調。但是《冬》中仍直接將魚和鳥曝露在暴力之下,非常刺目。案板之上,魚被割成幾段,刺耳的齒刀割魚聲連綿了三個畫幅,魚頭呼吸與跳躍異常生動。炭火之上鳥被簽子插穿,撲棱著的翅膀轉瞬成為油滋滋的烤肉,成為笑嘻嘻的老人和充滿期待的小孩的視覺焦點。導演甚至毫不忌諱地承認,烤死的鳥就是他為影片攝製訓練了三年的一隻。這種漠然不僅忽視了電影「視點」與觀眾的本體性關係,並且完全就是娛樂主義至上的當下社會,對於媒體的視覺暴力視若無睹的一枚例證。
藝術電影允許創作者對天對地對自己的團隊對想像的觀眾說:我的電影很牛逼很牛逼。但是不能心裡想的是:我很牛逼我很牛逼。這個差距很大。前者執著創作本身,牛逼感引來火花四濺的創作興奮狀態,振奮自己、團隊,也必將感染到觀眾——不管這觀眾的範圍有多大。後者讓自我迷失,說白了自我體驗大於電影表達,會令創作出現一個漏鬥,才華的空殼還擺在那裡,裡面的靈氣漏光了不說,創作會失真,會扭曲,更不可原諒的是會為他人帶來「視覺侵犯」。高逼格的瘴氣,能讓沒入門的電影愛好者暫時蒙圈兒。明明觀影有如嚼口香糖嚼出了大蒜,一看標籤上貼的就是蒜味口香糖,美其名曰「藝術香口膠」。老實孩子帶著一嘴的蒜味逮誰跟誰說:我今天藝術了,卻把別人給嗆著了。最壞的是很多人客氣地躲著走,一邊敷衍著說:您這風格有哪位歐洲電影大師的影子。
原文發於7月20日《中國電影報》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