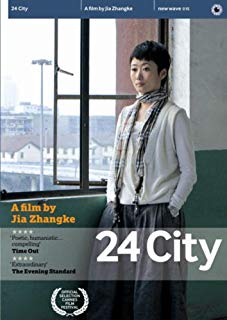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6-12-29 17:00:40
看完電影的發散,其實和電影沒太大關係了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三線建設」這個名詞。當我開始認真去了解這個名詞的時候,那個時代早已離我們遠去了。
從出生到初中二年級,我一直生活在陝西漢中城外一個叫「鋪鎮」的地方,就是電視劇《武林外傳》中多次提到過的「十八里舖」的原型。不過,除了週末偶爾溜躂到城上享用一碗香噴噴的熱麵皮,大部份時間,我的生活和漢中市、和鋪鎮沒有什麼交集。
原因正是「三線建設」。鋪鎮邊上,是成片的農田和起伏的丘陵,六十年代後期,這裡湧入山南海北不同地方的人,操著各種口音,在這片農田和丘陵里憑空建起了一座工廠。這些都是依據當時中央的指示:大城市人口和工業過於集中,如果突然遭遇戰爭襲擊,風險巨大,因此要在三線地區(長城以南、京廣線以西)的各種窮山僻壤建設新工業基地。漢中位於中國腹地,秦嶺屏障於北、巴山橫亘於南,地形險要,氣候溫和、資源豐富,成了三線建設的重點地區。鋪鎮邊上這個工廠,代碼3157,隸屬於航空工業部012基地,正是當時在漢中地區集中建設的大批軍工廠之一,專門生產軍用運輸機的配件。
70年代初,我父母還在陝北農村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為無法回京而發愁,收到三線建設的招工消息,便去了陝南,從此在這個秦嶺巴山之間的軍工廠里奮鬥了二十年。工作、戀愛、結婚、生子,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光都在那裡度過了。
工廠雖與鋪鎮近在咫尺,周圍還有不少山村,但一道圍牆把工廠和周邊隔絕開來。廠子裡除了廠區、還有家屬區、燈光球場、露天電影院、大禮堂、商店、食堂、公共澡堂、招待所、託兒所和學校,生活設施一應俱全,完全是個幾千人的獨立王國。除了週日工廠會安排一輛班車,拉職工們去漢中城裡買些大件商品,日常生活需求可以不出大院,全部搞定。
我是個地道的三線子弟,後來看到一些其他三線子弟的文字,他們有的在四川、有的在貴州,和我家地理上離得很遠,卻有著幾乎一模一樣的童年記憶。
工廠是準軍事化運行的。每天清晨,家屬區的大喇叭就開始響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幾千人同時起床、洗漱早餐,職工們就著音樂匆匆從家屬區湧入廠區,小孩子被送到廠區和家屬區中間的託兒所,大孩子脖子上掛著鑰匙自己步行去子弟學校。傍晚大喇叭再次響起,這回是「歌唱祖國」,意味著下班了。工人們再次潮水般湧出工廠大門,回到家屬區自己家裡,給放學的孩子們做飯,孩子們則滿家屬區追跑打鬧玩耍、弄得渾身髒巴巴地回家,在爹媽的罵聲中吃飯做作業睡覺。所以小時候最不愛聽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最喜歡「歌唱祖國」。
燈光球場幾乎每晚都有單身職工們打籃球,孩子們也偶爾摻和到裡面。節假日有時在這裡,有時在大禮堂舉辦聯歡會,我和同學們塗得滿臉油彩,拿著我爹手工製作的木頭長槍,唱游擊隊之歌,全場職工都是觀眾,嘩嘩拍巴掌。還有露天電影,一放電影全廠的人都搬小板凳來看,人太多的時候我們幾個小孩兒就跑到幕布反面看,全是反的,倒也能看明白。
工廠的職工們來自全國各地,什麼口音都有,只有國語是通用的,所以我們下一輩兒人既不會說當地方言、也不會說家鄉話,全是國語。伴隨著口音的區別,也會產生頭痛的身份認同問題。爹媽們都認為自己是北京人、上海人、東北人、四川人、江蘇人,然而父母的家鄉對於我們來說相當陌生(漢中被夾在秦嶺與巴山之間,當年穿山鑿洞的西漢高速尚未開通,只有一趟慢吞吞的火車到安康,再從那裡倒火車,去趟北京要兩天兩夜,票也很難買,十多年間我只回過兩次北京,其他家庭也各個類似);漢中也不是我的家鄉,周邊當地人和我們口音不同、生活習慣不同,各方面都似乎離我們十分遙遠。我們生活在鄉村,卻吃麵包喝牛奶住樓房,享受著子弟學校比較優質的教育資源,普遍有著城市子弟的優越感,是「城裡人」,但回到北京城,又覺得自己是山旮旯里來的,土里土氣,北京人並不認可我們是同類。直到很多年以後,我還會時常產生這種漂泊感,覺得自己是個沒有根的人。
賈樟柯導演2008年上映的電影《二十四城記》裡的420廠,現實中真實存在,和我父母的工廠各方面都非常類似,只是規模更大些,而且位於成都市內,不像我父母的工廠建在山溝溝里。巧的是我父親當年去成都培訓,就是在420廠。這些三線建設中勃勃而起的工廠幾乎都曾經輝煌過,如電影《二十四城記》中陳建斌扮演的辦公室主任所言,當年是很不錯的企業。然而到八十年代後期,都逐漸衰落了。420廠遷出成都市中心,原址蓋起了華潤地產名為「二十四城」的房地產項目。我父母所在的工廠算是軍轉民比較順利的,至今還在原址,是當地工業園區的重要企業,還在生產我父母當年做過的那些精密儀器。而更多的工廠已經消失不見了。去年看到過一篇文章,記錄同在漢中的另外一家軍工廠,曾經是萬人大廠,如今已是人去樓空。芳草萋萋,一片蕭索,機器轟隆聲似乎還在山谷間隱隱作響,而那些曾經在車間奮鬥的工人們、我的長輩,他們的青春和記憶,都已經湮滅在了歷史的煙雲中。
《二十四城記》里,破舊的廠房、斑駁的牆壁、雨水一滴滴落在窗台上、靜默的工人,每一個鏡頭似乎都不是電影,而是我記憶深處的影像。幾十年回不了家鄉的大嬸、打籃球的車間主任、江南來的美麗廠花,他們就是我的父親母親和身邊的同事。我熟悉他們的面孔,也記得他們的故事。我的父母入廠時剛剛二十出頭,年輕單純,意氣風發,勤奮上進,最初的那些年基本都在加班中度過,以致於我週日掛著鑰匙自己在空無一人的家屬區轉悠,時常恐懼是不是自己記錯了時間?今天並不是週末?應該去上學?
為了子女,父母在九十年代設法離開了工廠,回到北京。而北京已經沒有他們的立足之地。胡同裡的老家早已不復存在,沒有住的地方,到處租房,有一年甚至搬了六次家。在北京簡陋的出租屋裡睡覺,有時會夢到3157廠里分配的寬敞明亮的兩居室,應該又有新人住在那裡了吧!直到我上了大學,一切才算穩定下來。這些年北京的外來人口不斷增多,迅速超過了老北京,走在這個超大城市裡,身邊的人大都是北漂,終於不再覺得自己是個外來異客。
我父母這一輩子,十六七歲還是個半大孩子時便隻身下鄉,從此一直遠離家鄉和親人、顛沛流離,著實不易。當年的那座工廠讓他們拋擲了青春,同時也給予了他們許多庇護。我覺得父母對工廠的感情是非常複雜的。作為他們的下一代,我們,更加徹底地離開了,現在與未來,恐怕都不會和當年山裡的那座工廠有什麼聯繫了。
當年我還是個小屁孩兒,只覺得生活平淡,來日方長,並不覺得眼前的生活有什麼意義。然而多年過去,以為過去早已被遺忘的時候,過去忽然以另一種姿態出現了,那些當初習以為常的事物,似乎都有著某種涵義,並且默默地、深深地刻印在了腦海里。歷史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趟過,我們不知不覺就成了歷史的一部份,也見證著歷史。電影看罷,這一刻,我忽然想起當年廠區外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心中湧起難以名狀的惆悵與傷感,眼淚不住地流下來,不能停止。 舉報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