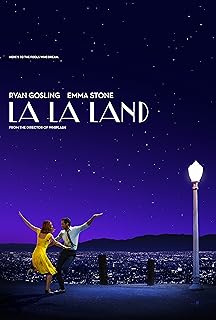爱乐之城/爵士情缘/啦啦之地
導演: 達米恩查澤雷編劇: 達米恩查澤雷
演員: 雷恩葛斯林 艾瑪史東 Amiee Conn Terry Walters Thom Shelton

2017-02-19 08:58:14
《愛樂之城》:不是為理想分開,而是理想暗示了他們根本是兩種人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去看了《愛樂之城》。本來想作為週末放鬆,結果猝不及防被戳了淚點,而且持續時間異常久,大約片子後面一個小時全程眼淚汪汪。礙於旁邊人多,盡力忍著,但中途眼淚還是不受控制流出來好幾次,看完之後,整個人幾近虛脫。
感覺身體被掏空。
從正式成為編劇到現在日子裡,應該還是第一次完全拋卻理性看一個片子。
《愛樂之城》有雙重催淚彈:理想和愛情。不少人看過覺得塞巴斯蒂安和米婭幾乎是天生一對,難得的甜蜜眷侶,卻最終因為理想而分開,深感遺憾,深深嗟嘆。我反而覺得,他們必然會分開,不是為了理想,而是各自的理想很早就暗示他們——他們根本就是兩種人。
當然,他們看起來是很相似的:從事藝術,有想法,肯奮鬥,以及最重要的,理想主義。所以走到一起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之後的衝突也就出在理想主義上面。
塞巴斯蒂安是個爵士鋼琴師,痴迷於「老古董」級別的爵士樂,年輕人基本不會聽。他的理想就是開間俱樂部,演奏他的古董爵士。
米婭是演員兼劇作家,愛好上來看,她喜歡許多老電影,但至於理想,隨著劇情的逐漸推進,觀眾很快會發現,和老電影似乎沒太大關係,她的理想很簡單,就是做一個成功的演員。
為了各自的理想,他們互相支持,一起努力,共同前行。
乍一看,兩個人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
問題在於,他們是完全不同的理想主義者。
塞巴斯蒂安是有藝術潔癖的,他的理想非常具體而微:不是做音樂,不是做爵士樂,甚至不是做所謂「好」的爵士樂,他的理想還要更具體——做他喜愛的那種沒人聽的「古董級」爵士樂。在這方面,他十分偏執。賽巴斯是個客觀的理想主義者,就像客觀唯心主義一樣,他的理想,老派爵士,是一種客觀存在,對他而言,也是一種客觀絕對精神的存在。他想做俱樂部,很大一部份也因為不能容忍那家和爵士相關的餐廳墮落成賣那個叫塔什麼食物的存在。對於這種人來說,理想至上,他們服務於理想。
而米婭則是個主觀的理想主義者。我想編劇和導演應該都沒有刻意為之,但因為他們對人物形象和劇情邏輯的處理都十分到位,所以人物形象的背後邏輯也能自然而然地呈現出來——編劇沒有想刻意去定義米婭和她的理想,但在全劇的對白中,除了「試鏡通過」,米婭其實並沒有真的提到過自己想做什麼。後來在她最後那次試鏡中,她唱了首很動人的歌,她的阿姨告訴過她,因為那些敢於做夢的人,世界才能不斷開發出多樣的顏色。而這些人,因為追逐夢想,也讓自己的人生變得豐富多彩。這種情況下,理想服務於個人,對她們來說,她們想成就的不是某種客觀存在,而是她們自己。
所以幾年後,米婭事業愛情雙豐收,不但大紅大紫,還組建了幸福的家庭,有體貼的丈夫,可愛的孩子。這是許多人眼裡的美滿人生。和塞巴斯蒂安的那段戀情雖然刻骨銘心,但於她理想中的圓滿未來已經不再有干係。米婭窮其一生的作品,將是她自己,是作為一個成功演員的一生。美好家庭也一定會是這個作品中的重要組成部份。如果從潛意識層面來推測,她和塞巴斯蒂安之所以分手,可能連她自己都不會意識到的深層原因,其實是她不可能跟隨塞巴斯蒂安去過漂泊的生活,不可能從塞巴斯蒂安身上找到她理想生活的樣子。從這個角度說,塞巴斯蒂安是她最終作品的敵人,也就是她理想的敵人。
而塞巴斯蒂安,在流行爵士樂隊裡得到觀眾歡迎,他自己的心理感受,很可能是「痛並快樂著」。他不可能全無喜悅,坦率些講,沒有人會在最初就完全對世俗眼裡的成績無動於衷;但同時的,他內心也伴隨著許多掙扎和痛苦。米婭第一次看賽巴斯在流行樂隊彈琴的時候,打在她身上的光滅了,她似乎驚慌失措,隱沒在人群中。我想那時候她應該也沒那麼清楚心裡的感受究竟是什麼,但直覺已經告訴她,有什麼事情不對勁。賽巴斯在他不喜歡的事,以及,賽巴斯和她不是同一種理想主義者。
很快賽巴斯內心的掙扎和痛苦起作用了。
兩人爆發了導致分手的最嚴重一段爭吵。那段對話裡,米婭直言塞巴斯蒂安並不喜歡他做的事,賽巴斯當場發怒。那是他對傷害的本能反應——稍微換位思考一下就不難感受到,米婭的話,無疑戳中他內心最薄弱的痛點。對賽巴斯來說,他加入流行樂隊的行為,其實是在背棄自己的理想,因為他的理想只有老派爵士樂。他一直不願意面對,但現在米婭一刀結結實實地紮下去。非常疼。而讓他這樣做的理由,正是米婭和母親的那一通電話,是為了兩個人的愛情。現在卻結果如此,他的心疼和憤怒可想而知。
然後塞巴斯蒂安像被潑了盆冰水一般醒過來,他從樂隊成功的快感和背棄理想的糾結中做出選擇——他還是要追求理想。客觀的理想主義者就是這樣,他們的人生服務於理想,甚至奉獻給理想,運氣好的話可能在為理想奮鬥的時候也能稍帶著實現人生圓滿,但運氣不好,很可能就要把自己搭進去了。就像歷史上那些革命者一樣,為了理想,頭斷血流也在所不辭。只是賽巴斯的理想沒這麼高風險而已。
至此,塞巴斯蒂安與米婭之間的分歧已經十分明顯:他們無法滿足彼此的需要。塞巴斯蒂安想實現他自己的理想,想在流行樂隊裡臥薪嘗膽,賺到錢之後開爵士俱樂部,就很難配合米婭完成她圓滿人生的理想。更何況,時日越長,這種分歧帶來的衝突就會越大。
很多年後,米婭已嫁作人婦,賽巴斯蒂亞則維護了自己的藝術潔癖,也繼續著情感潔癖——打開家門,空蕩蕩的屋子,他還是一個人。他們在一個沒有預期的期間重逢了,也許就是最後一面。他對她一笑,動人無比。我想他沒說出的話是:無論結果如何,愛過很好的人,本身就是一種幸運,就足夠美好了。
至於理想,我無意評價兩者的高下,我只覺得他們都是很好的人,面對好人我從來都很難苛刻。但我確確實實為塞巴斯蒂安這種偏執的理想主義者動容。
也慶幸,還好這個故事不是在當代,否則,五年後沉浸在老派爵士世界裡的藝術殉道者,在自傢俱樂部邂逅整容整得幾乎認不出來、高聳著演藝圈均碼的胸脯、睡過一圈製片人的舊日愛人,他還做的出像塞巴斯蒂安最後那動人無比的一笑嗎?
生活會把分歧加工得更明顯。
但還好有電影可以造夢。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