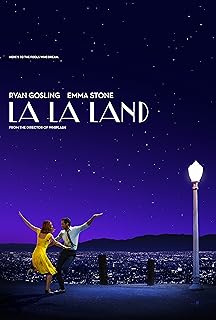爱乐之城/爵士情缘/啦啦之地
導演: 達米恩查澤雷編劇: 達米恩查澤雷
演員: 雷恩葛斯林 艾瑪史東 Amiee Conn Terry Walters Thom Shelton

2017-03-15 01:43:54
《愛樂之城》絕非華美的空殼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抱歉,一個標題黨,但這就是我最想說的一句。以下解讀僅僅是個人觀點。
「主體」的撕裂與「成功學」的悲鳴——談《愛樂之城》的複雜屬性《愛樂之城》自從上映以來引起了頗為廣泛的輿論關注。相對多數的讚美聲之外,對達米安塑造的「成功學」迷夢的批駁可謂不可忽視的一派觀點。從「毫無公德阻擋觀影」說到「X生活缺乏」說,從「爵士樂泡妞」目的論到「無處不虛偽」的一刀斬定。截然不同的欣賞視角帶來了迥異的觀點,客觀上也為更進一步探討這部影片帶來了更多可能。
由於對這部影片特殊的熱愛,本人在不同地區不同影院不同規格不同區位總共觀賞了5次。私以為,將《愛樂之城》概括為徹頭徹尾的成功學讀本加以抨擊雖有零章碎句可循,卻無法統攝整部影片的故事域;而將其看做一個美好的圓夢故事雖然可以基本包容大部份情節,卻又落了俗套且有些微片面。
達米安·沙澤勒的影迷當然都領略過這位青年導演在上一部作品《爆裂鼓手》中橫溢的才華。《爆裂鼓手》所呈現的不僅僅是技藝的習得,更關乎藝術、成功與器道之分。從中可以窺探達米安對藝術、夢想與成功學的複雜態度。
《爆裂鼓手》劇照而以此為互文(多面態度的一脈相承),《愛樂之城》展現的同樣不是一個瘠薄的平面。個人對這部作品的欣賞除了種種絢麗的呈現形式之外,在於對這個再簡單不過的追夢故事的立體呈現。在輕盈的歌舞與炫目的光影之下始終存在另一種隱伏的力量。它拉扯著我讓我無法真正完全沉入歡愉與幻想——而最終的悲劇結局不過是這股深流的餘波——這種感受最終讓我確定它不僅僅是一部技藝上值得銘記的作品,而且具備頗為深刻的當下意義。個人認為,它反映了在目前社會(不僅僅是好萊塢)年輕追夢者在融入資本邏輯過程中自我「主體」的撕裂,這與資本主義成功學不無關係,卻更像是淪陷其中的悲鳴。
一、「主體」意識與成功學的根本對立
「主體」在此處不同於一般意義上「有認識和實踐能力的人」。我們可以從接下來的史實陳述中體會此處「主體」的意義。
人民公社時期,一切生產資料成為公有。在農業領域,由於一刀切的分配模式,農民的積極性顯著下降。而在工業領域,生產積極性的下降反而在該運動之後。工業作為流水線作業方式決定了同一批工人共同參與勞動的集體共時性,勞動的成果本已處於相對穩定的結構中(不同於農業)。此時,當工人意識到公有的性質與勞動中「主人翁」的地位,他們在勞動中獲得的驅動力便成為這種以自身為「主體」的「參與感」。當家做主的地位使得勞動本身成為一種自我「主體」的建設,從而具備了更充分的動力。
毫無疑問,冒進的共產試驗最終還是由於生產力的落後等種種原因而以失敗告終。同樣,時至今日我們也並不能想像真正的共產主義構想中的「自由勞動」到底是如何面目。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這段歷史進程中體會「主體」的含義:勞動者自己是生活的主人,勞動本身成為自我實現的過程,成為物質與精神財富的養料——而不是最終的勞動成果,因而勞動者對待勞動是近乎純粹的熱愛與投入。
在現代化進程突飛猛進的社會,「主體」的含義似乎更具備了刺骨的現實意義。「主體」的意識不再成為勞動的主要驅動力,而「客體」即勞動的對象(或是勞動成果)成為另一種無形的壓迫推動著人們前進。越來越多的人們集中於「目標」與「結果」,而「目標」的達成意味著這一充滿怨憤與頹廢的勞動過程的終結。一個環路的終結意味著新的一環的開始——而如此的勞動循環再也沒有「參與感」的構築,「主體」最終失語。
其中的原因用最通俗的語言並不難表達:找不到自己真正喜愛的工作。過程無法達成自我的實現後,結果成為實際上唯一的標尺。而資本的邏輯將結果量化,理所應當地將勞動者參與勞動的感受量化——最終這一切被納入社會的體系。多數人為其所困,再也無法重拾那種作為「主體」的參與感。
在如此慘澹的現實中,「成功學」應運而生。它教導勞動者從根本上融入「客體」至上的邏輯,通過千百種輾轉騰挪鞭笞著人們為了資本運行最終的果實而努力——「成功學」的命名即如此,它最終是關乎「成功」的方法論。而內含於「成功學」的心靈雞湯則負責營造虛假的「主體」意識,讓勞動者更進一步沉溺於這一邏輯鏈條之中——如一頭推磨的驢幪著眼追趕著近在咫尺的鈴鐺聲。
因而這種「主體」意識與成功學在根本上是對立的。而在當今社會,尤其是仍然在追求自己人生定位的青年群體中,這兩種力量的矛盾尤為突出。
《愛樂之城》的故事中,Mia與Seb二人的故事恰好交錯地展現了兩種邏輯的博弈,以及造就這種困境的社會體系。
二、
共同家園的歸屬感是真的嗎?影片在開頭結尾都展現了頗為典型的公共場景:一個是高速路上的堵車與群舞,另一個則是Seb’s中的爵士樂會。
在高速公路的群舞將「愛樂之城」中濃烈的「愛」通過肢體進行了淋漓盡致的表達。在音樂的共同召喚下,所有人從「堵車」這一躁動不安的文明話語中抽離而出。整條高速公路被流動的彩虹佔領,陌生人之間產生了奇異的親密聯結,不同膚色、性別的歌聲舞步輪番演繹——彷彿是一個懸置於之前窘境中的烏托邦。而中:
It called me to be on that screenAnd live inside each scene恰好證明,他們被這種神聖的「主體」意識召噢,選擇去做自己生活的主角(注意,此處是「選擇」而非「能夠」)。
在此影片構造了盛大的虛像:他們,每一個生動而獨特的人,都是這座「愛樂之城」的主人,他們在音樂中獲得了「主體」的體驗。
And even when the answer's noOr when my money's running lowThe dusty mic and neon glow are all I need在這種「主體」意識的驅動下,所熱愛的事物本身成為最核心的需要,只要每日朝陽升起,生活的主人便能夠延續這種理想化的澎湃激情。
*多嘴一句,第一首歌的第一句歌詞就劇透了結尾……
影片關於「主人」、「主體」與「家園」的暗示不止如此。比如Seb坐在露天小圓桌旁時背景中鮮明的「加州人」意味,比如Seb的姐姐(或者不是姐姐)第一次出場便以侵入Seb的「家」為途徑,比如Mia在流連片場時一句「I love this」,比如Mia在逃離與男友兄長的聚餐後進入影院站在了螢幕前的正中央,比如Mia的獨角戲名稱正是對故鄉的告別,比如首演失敗後Mia否定了Seb對洛杉磯「家」的定位轉而尋找真正的「家」博爾德城。
追夢者是否真的是「加州人」?而影片最終,Seb’s酒吧中呈現的是一幅與開頭呼應的景像:在更為純粹的音樂環境中,黑人與白人談笑風生,Seb與樂手之間的關係平等而親密,顧客與服務者輕輕律動而不疏離……Seb在Seb’s中構建了另一個微縮的「愛樂之城」。
然而最大的區別正在於此——從開頭外景到結尾內景的微縮。烏托邦的理想最後僅僅停留在了這個地下的爵士酒館。音樂給予了最後的歸宿,然而這種「主體」的歸屬感最終也無法擴展到藝術以外更廣闊的生活圖景之中。
因而站在「城」的公共理想角度,它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後撤?這種後撤如何通過Mia與Seb二人鋪展隱喻?這便是之後要探討的問題。
三、
< Someone In The Crowd >的段落拍攝得極為精當。一首歌包蘊了Mia心理的跌宕起伏,同時第一次展開了對洛杉磯世情耐人尋味的描摹。
鏡像在電影中一般表示的是人物的多面甚至是分裂。短短七分鐘出現了兩次Mia的鏡像描繪,鮮明刻畫出了Mia處於動搖狀態的「主體」。第一次,Mia在試鏡失敗後沐浴更衣,「主體」意識無法得到外在認可的背後依然是「成功」無果的慘澹;第二次,Mia在「好萊塢套路」與「人性」交織的派對中備受冷落身心俱疲。
「好萊塢套路」還是「人性」?「Someone In The Crowd」可以解讀出兩層含義,一方面是認可「主體」性的伯樂,而另一方面是同樣具備「主體」意識的同行人。這一段落的描繪顯然是「主體」願景的雙重失語。
Mia不是能夠自如遊走於紙醉金迷中的交際花。推杯換盞,煙火飛旋,人群最終爭相躍入池中,而Mia的世界已然雪落。此時產生了反諷的效果。Mia的伯樂與同行者都不可能出現在這個「主體」缺位而交際「成功學」瀰漫的場域中(注意,這個公共場域完全不同於開頭結尾)。
之後的故事中依然有對第一層「someone」的描繪,而幾乎每個可能的伯樂都以高高在上的姿態用既定的標尺衡量Mia的「主體」性——甚至是不完整的僅有幾秒鐘的「主體」。他們是這個社會體系中更高階層的人,他們在試鏡中採取的都是以最終的「客體」即表演成果論定的評價體系(此處筆者只是從比喻含義出發解讀而非批判目前的試鏡制度)——這種評價體系也許並不是出自他們的本意,但卻是「成功學」思想瀰漫的條件下最簡便快捷達到目的的方式。在這一過程中,參與者本身的「主體」特性並未得到真正的延展與實現。
幾次試鏡過程中,非常典型的衣著變換反映了身份敘事與心理變化。最明顯的是外套,Mia在襯衣潑髒後用藍色外套包裹自己,在第一次試鏡結束後馬上拉開了拉鏈——在電梯中陷入兩個衣著光鮮神態高傲的成功人士的夾縫中;而「第二次」(特指那部電視劇的二輪)試鏡中,Mia在表演了不到五秒鐘馬上被拒憤懣而出,甩開了紅色的夾克。在這樣的試鏡中Mia始終需要那一件外套,它所象徵的層層包裹的壓抑感讓她無法真正自證「主體」的意義,從而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勞動」。另外,Mia在交際酒會中與人攀談時的笑容和第二次試鏡失敗後擠出的笑容如出一轍,可以看作Mia的心理變化軌跡。
縱觀全片,這第一層的「someone」還可以引申出「他者」的含義,這包括受成功學邏輯浸染的上層「他者」,也包括受消費主義裹挾而「什麼都追求卻又什麼都不尊重」的人群。他們在無形中凝視著二人的「主體」,最終構成「主體」的後撤與「成功學」滲透的控制力。
而另一層面的「someone」,對應的正是志同道合基礎上的愛情追尋。與第一層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在根本上是「主體」的外延與實現。
四、&
Mia和Seb的愛情正是出於被「成功學」傾軋後的相互確證。愛情是整個故事中二人「主體」意識得到最充分釋放的過程——不僅僅是對所熱愛的事業,也是對愛情本身。
「一個無趣的夜晚」的歌詞反覆強調了二人在此時此刻與對方毫無火花的狀態,真正的戀火也正從此燃起。Mia脫下了工作應酬專用的高跟鞋換上了Seb的情侶款,而Seb加入了踢沙子等喜劇性肢體動作。
在我個人的觀影體驗中,除了最終的夢幻蒙太奇之外,最動人的一幕莫過於Mia逃離餐廳奔向電影院。黑夜中飄飛的花瓣當然是心理映射。但回想起來,我甚至無法確定Mia在餐廳中聽到的那段音樂是否真實,也許那同樣是Mia潛意識中「主體」追尋的投射。Mia逃離餐廳甚至罔顧公德不自覺地站在螢幕前,二人在深夜潛入天文館成為老電影的新主角——這正是另一種「無因的反叛」。更不必說那一段凌空的想像:繁星之城中的舞步只屬於愛情中的二人,他們在這場並無事先張揚的叛逃中獲得了「主體」極致浪漫的實現。
影片中另一首歌曲同樣也提及了「戀火」這一語詞。此處「火」的燃起反而預示了愛情的幻滅。Mia的表情層次變化,她不得不因洶湧的人潮而後撤,而映照Seb的燈光也從暖黃變得蒼白。愛情中的「主體」開始動搖,而夢想的「主體」也遭受拷問。
五、&
可以看做是整個故事的核心意象。不同於整體旋律上揚的,似乎更具抒情小調的幽婉色彩。
City of stars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City of stars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City of starsYou』ve never shined so brightly儘管歌曲最終走回了對夢想與所在之「城」的歌頌,卻又不可否認這種自我實現的過程中流露出的惶然。而這只是所有洛杉磯追夢者的縮影。他們的熱愛所抽象而成的自我「主體」本身匯聚成了這座繁星的城市,而所有的繁星又渴望著光芒的相互映照。
在Seb家中,二人第一次一起合唱這首歌曲。中間插入的是二人各自「追夢」過程的蒙太奇。而在這之前則是Seb的唱詞:
Think I want it to stay此處歌曲再一次承擔了反向暗示的任務。之後這一段落中,Mia與Seb二人的夢想路途已然走向分裂。Mia儘管心懷上座率、債務等顧慮,但她依然以自我的「主體」為中心實現自己,表演依然是她的鍾愛。英格麗·褒曼的海報被揭下,一方面是某種新的期許,另一方面則代表著Mia在這一段為自己的獨角劇奔忙的過程中對勞動成果——即最終的「客體」對象的淡化。
而Seb的生活則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加入Keith的樂團後他的個人意願被不斷剝蝕。在加入樂團之前,影片呈現了一段與Mia的外套相似的衣著敘事:Seb打上了領帶,聽著房間外的Mia向父母解釋他們的現狀,目光則停留在房間浸了水漬的天花板一角。在之後間奏的蒙太奇中,Seb簽了約,接受了服裝定製公司對自己的「度量」,錄製網站中看似淡定實則尷尬的視訊。
歌曲唱罷二人還沉浸於濃情蜜意之中。而兩種幾乎完全相反的追夢走向決定了在同樣的迷魂記燈光下的分裂。二人的爭執點集中於Seb的夢想是否是自己的。在夢想與愛情上雙重的「主體」確證是這段關係能夠維繫的充分必要條件。Mia察覺了Seb在夢想路途中的沉淪——陷入「錄新歌—巡演—錄新歌」的閉環之中甚至幾乎拋棄了爵士酒吧的念想——因而反覆強調對待夢想的「主人翁」態度。而Seb的反駁證明了他內心此時的「成功學」邏輯:你的愛只是為了獲得自己「主體」的滿足感,而我是懂得「變通」並最終能獲得「成功」的人。飯桌上正是「主體」意識與「成功學」的交鋒,這也決定了這段關係的崩解。
接下來故事出現了全片最重要的轉折。Mia被Brandt相中參加了試鏡。這次試鏡的模式與以往完全不同。以演員本身作為標尺創作的模式正是對「主體」的肯定。演員的自由選擇被提升到空前高度,而演員本身同樣需要反饋「主體」的實現度——某種程度上其意義甚至與想像中的共產主義「自由勞動」有些類似。而對比此前Mia的服裝敘事,此時的她沒有繁冗的外套,沒有高跟鞋,恰好吻合了這種「主體」與「參與」為核心概念的勞動模式。歌曲完美契合了Mia的「主體」。
She smiled,Leapt, without lookingAnd tumble into the Seine……Her, and the snow, and the sand同樣是「跳水」的行為,獨自跳入冰冷的塞納河與先前酒會中的競相湧入構成了完全不同的隱喻。Aunt(此處暫不模糊翻譯)的行為對Mia存在著直接的導向作用。如果說之前交際酒會的躍入是一種沉沒於無法共感的客體之中,躍入塞納河則是選擇如雪花與沙礫一般融入其中並真正成為塞納河的「主體」。塞納河底的雪花、泥沙與洛杉磯的繁星都暗含著某種來自社會下層群體的聲音。Mia歌唱的是「someone」的故事,卻也是自己的故事。
Sky with no ceilingSunset inside a frame……A bit of madness is key to give us new colors to seeWho knows where it will lead us?And that's why they need us,So bring on the rebelsThe ripples from pebblesThe painters, and poets, and plays「成功學」的環境中設置了層層「天花板」(ceiling),與之前Seb所注目的角落呼應,指向了固化的資本邏輯與社會階層。畫框中的夕陽與Seb獨坐時背景中的「加州人」廣告共同傳遞了「主體」的歌頌。「主體」的秉持是唯一突破與「反叛」的革命方式。而在「成功學」的環境中堅持「主體」是毫無疑問的「幼稚」與「瘋狂」——如此種種不過是「卵石」相互碰擊時的小小漣漪,而這些漣漪匯聚成最終的塞納河。
I trace it all back,to thatHer, and the snow, and the sandSmiling through itShe saidShe'd do it, Again最終需要「回溯」的同樣是真正的「主體」意識。對這首歌曲的影像處理某種程度上正是還原了Mia的「主體」:拋棄眼花繚亂的蒙太奇,把角色交給演員自身,簡單的環繞特寫長鏡頭。甚至從石頭姐的表演中我們看到了一般情況下有些誇張而讓人不適的表情——而這正是具有真實的自我與反叛情結的「主體」本身。「主體」實現的過程中呈現的正是多樣甚至是粗糲的美感。沙與沫且歌且舞,他們依然選擇躍入其中。
之後的對話中,Mia一方面希望Seb的夢想「主體」意識回歸,一方面仍然渴望尋回自己的愛情「主體」。因此他們在此刻復合幾乎順理成章,之後的故事卻在意料之外。
六、&
的類似旋律在片中出現了多次。它召喚著Mia逃離筵席,是Seb無奈於雜誌照片拍攝時心中的第一旋律,是中間星空的高潮,也是最終的開頭——基本可以看作兩位追夢者的「主體」意識的存在證明。
然而當二人復合為已知條件,「主體」兩全的即將實現——我們便很難想像這種突然的分離。「冬季」與「五年」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冬季」是一張虛幻的幕布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也許可以從另外一個問題入手:最終的夢,到底是誰的?是二人共同的嗎?還是一個人?假如是一個人又是哪個人?
我們多麼希望這是二人共同的願景。但實際上這種說法似乎除了觀眾的一廂情願很難有更多的支撐。
從死板的邏輯上說,最後的夢中經歷了從Mia家中到酒吧的路程並不是二人可以共享的記憶而僅僅是Mia的。另外,我們還可以衡量,當聽到這段對「主體」意識強烈呼喚的旋律時,誰會受到更深的觸動?
從影片中不難看出,Seb最終回到了原初的夢想軌道之中,爵士酒吧的小型烏托邦是不同人「主體」釋放交融的場域。除了愛情以外,Seb的「主體」感受可以說是貫穿了他目前的生活。而Mia的境遇似乎並不相同。
我們不妨再一次從Mia的服裝敘事與心理變化入手。五年後Mia一出場便是極為高貴甚至頗有壓迫感的高跟鞋,在似曾相識的買咖啡過程中我們除了相同的禮節外並不能看出什麼別的。然而Mia一回到家便脫下了高跟鞋,端莊面容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鬆弛而疲憊的笑容……Mia是否並未過上應許的「主體」生活?
再回到這個平行時空之中來:與現實的關鍵不同都出自Seb的改變,但Seb的改變正是Mia的心理補償;而其他的變動部份則主要是Mia「主體」實現的強化(比如滿場的觀眾)。那麼我們也許在留白的故事中摸索出如下可能:
儘管Mia在「第二輪」試鏡中獲得了「主體」的認可,但是「Someone In The Crowd」的大環境依然不曾改變。在留白的最初時段,Seb還在樂隊中工作,這種「主體」的錯位並不能輕易彌合,因而二人分手。之後Seb回歸了他先前的夢想道路,並最終覓得實現「主體」的勞動方式。Mia儘管成名,卻免不了繼續在之前的被「客體」與「成果」衡量的體系中掙扎——她的「主體」依然不能獲得完全的實現。
此時,更需要一個夢境作為補償的恐怕不是Seb,而是Mia。
現實已然如此。他們最終還是走上了分叉的道路。Mia身陷社會體系的羅網之中,而Seb雖然沉浸於自由勞動卻依然孤獨。相比五年之前,二人的「主體」境況彷彿被命運置換。最終,二人相視一笑,Mia彷彿重新看到了「主體」實現的願景,Seb則打著節拍開啟了新的樂章。
恐怕沒有比二人的分離更為「完整」的結局了。「主體」與「成功學」的對視,在「成功學」的浪潮中對「主體」的悵望,「主體」仍需要更進一步實現的渴慕,在最後沉重的笑容中都已道盡。
《愛樂之城》內容上的優點並不在於其創新性,而在於其對這個當代青年群體中極具現實感與代表性的故事細緻入微的呈現與表達,並恰到好處地排布了其中夢幻與悲劇的比例。從中我們並不能一概地籠括創作者的價值取向,卻能夠身臨其境地讀出被兩股力量裹挾的矛盾感。
我依然會感動於Mia的一句台詞:
I』ve seen better.更好的風景究竟是什麼?影片並未給予一個完整的答案。也許是自我的「主體」永遠處於追逐與實現的過程之中而沒有終極,也許是這座由不同「主體」構成的繁星之城依然有更多的可能——而不再僅僅侷限於音樂之中。
或許這也是《愛樂之城》對於我自身的意義,對它的更進一步的探索,也是對我自身「主體」存在的不斷確證。
「主體」的舞台*所有圖片來自你瓣
本文可見微信公眾號
風影電影紀 《愛樂之城》:「主體」的撕裂與「成功學」的悲鳴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