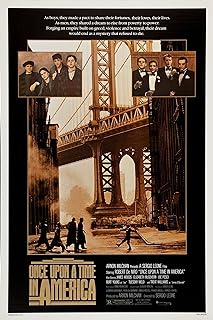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09-01-22 00:39:45
教授分析 《美國往事》(轉)
儘管這是一個關於欺騙與背叛的故事,但敘事人並未將努得爾斯呈現為一個愚忠者或弱智兒,他始終以自己的方式洞察著事實與真相。他甚至明確地推斷出麥克斯的行為邏輯:「今天他們雇你去殺掉約翰,明天也許會讓我來殺掉你。也許你能這樣做,我可不行。」他同樣看清了麥克斯不斷膨脹的野心,他譏諷一心做人上人的黛布拉:「我從你嘴裡聽到了麥克斯的聲音。」他甚至告訴麥克斯:「什麼時候想清洗我,通知一聲。」但他對麥克斯的洞察不可能超越兄弟情誼的神話。他永遠不可能想像的是,當清洗降臨的時候,不會有「通知」,不會有預警,甚至在麥克斯的大行動實施前片刻,在努得爾斯的視點鏡頭中,仍是麥克斯三兄弟擁抱在一起、共赴兇險的情境。當他面對這一事實的時候,它仍包裹著「生不同時,死當同穴」的表象。在序幕的滂沱大雨中,麥克斯三兄弟的屍體並排暴屍街頭(一如麥克斯所說:「淚水迷住了你的眼睛,你沒看清被打死躺在街上的不是我。你太痛苦了,以致於無法認出我。」和努得爾斯一樣,在這一時刻,觀眾也必然忽視了那具被掛上「麥克斯」識別牌的屍體,只是一個面目燒焦的不明死者)。在豪華墓室裡,作為努得爾斯視點的平移鏡頭依次展現出潔白的大理石墓碑上的銘文:死期為同一年份,同一時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似乎除了努得爾斯,他們都以驟死於華年的事實實踐了友誼的承諾,只有努得爾斯是一個卑怯的苟活者——直到另一個借屍還魂的生者露面。
影片中另一個重要的敘事修辭策略,是將麥克斯的視點存在有效地隱藏在努得爾斯的第一人稱敘事之中。在影片的觀片過程中,人們毫不懷疑,一如原作,這是一部「自傳體」影片。故事的講述、事件的呈現,都不僅內在地限定在努得爾斯的視點(目擊、在場)之中[參見筆者:《電影與視點敘事》,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函授教材。筆者認為電影中的人稱敘事所呈現的場景必須以此人物在場、目擊為前提],而且作為努得爾斯的回憶,它還為努得爾斯的憂傷、追憶之情所浸染。事實上,這只是影像的類比結構所呈現的,而在影像的獨立結構中,始終存在著麥克斯的視點鏡頭,在一些重要的場景中,是麥克斯而不是努得爾斯的視點鏡頭充當了敘事的施動(agent)者。早在麥克斯第一次闖入了努得爾斯的世界,敘事人已將優越視點賦予了麥克斯:一個由高處——麥克斯所在的馬車頂端俯拍的視點鏡頭,將努得爾斯和他的小兄弟呈現為一群鬼鬼祟祟、難成大器的街頭遊蕩兒。與此同時,麥克斯、努得爾斯間俯仰拍的對切鏡頭,已然確認了未來的權力與位置關係。而努得爾斯與黛布拉第一次約會這個極為隱秘的場景則暴露在窺視者麥克斯的目擊之下。
在組合段15中,20世紀20年代故事的結束處,隱含著一個重要鏡頭段落,其中包含了一個視點鏡頭的反轉[參見筆者:《對切鏡頭與電影敘事》,《電影創作》1991年第3期。筆者認為在電影敘事中視點鏡頭的分配,一如福科所論述的,是社會生活中話語權力的分配;換言之,電影中的視點權和話語權的等價物。]。在押解努得爾斯的囚車緩緩駛過街角的全景陳述鏡頭之後,是囚車鐵窗後努得爾斯的近景鏡頭,他依戀地望著窗外的遠方。反打為他的大遠景視點鏡頭,在監獄對面的高牆下,麥斯三兄弟站立在那裡,莫胖子也匆匆趕來。再次切換為努得爾斯的近景,他含著淚,努力對朋友們展露出一個微笑。視點/反打:攝影機緩緩地平移拍攝遠景中四個患難兄弟,努得爾斯的一次無限深情的凝望與飽含留戀的告別。第三次出現努得爾斯的近景,他抬起手向朋友們揮別。再次反打為遠景中麥克斯等人時,畫面以囚車鐵窗和努得爾斯揮別的手為前景。但接下來,卻是全景中的囚車,似乎是一個客觀的陳述鏡頭。可此後麥克斯的近景,卻將前一鏡頭定義為麥克斯的視點。反打:囚車緩緩駛入了監獄,沉重的鐵門似乎在我們的面前關閉了。再次切換為麥克斯的近景,同時攝影機漸漸推為大特寫。在這一頗長的鏡頭中,麥克斯若有所悟地抬起眼睛,將目光投向遠方的未知處。這不僅是一個視點反轉的時刻,也是意義反轉的時刻,同時是麥克斯心路歷程的轉折點。在這一時刻,麥克斯從努得爾斯的遭遇中否定了街頭小流氓/黑幫強盜的道路,這條路只有兩個目的地——一個是巴格西般地暴屍街頭,一個是努得爾斯般地鋃鐺入獄。這無疑是電影敘事人、影像的獨立鏡頭的特定呈現:因為此時,敘境中的敘事人/努得爾斯已不在現場,他已被關閉在鐵門背後,這扇門要到12年後才會對他開啟。然而這一明顯的麥克斯視點鏡頭,再度被成功地遮蔽在文本之中。接下來,是仰拍鏡頭中白色大理石墓室上的金色銘文:「你們年輕而強壯的人將倒在刀劍之下。」似乎是前一個鏡頭中麥克斯的視閾。但鏡頭反打,畫面呈現出1968年老邁的努得爾斯,他百感交集地仰視著銘文。
而更為更要的一場,是悲劇的解除禁酒令之夜(組合段25)。事實上,這一段落是以麥克斯的大特寫鏡頭開始的。在這一鏡頭中,麥克斯的面孔大部份隱沒在陰影中,只有他的雙眼冷酷地閃爍著。這一段落的視覺敘事,建立三個人彼此交錯、而又彼此迴避的目光。首先是焦慮而負疚的努得爾斯,他拒絕與任何人交換視線。為了實踐生死同心的諾言,為了救他「淪入瘋狂」的朋友,他必須去做他最為不恥的勾當:向警察告密。其次是卡蘿焦慮、盡力掩飾的目光,她一次次地將目光投向努得爾斯,敦促他去做他「應做」的事情。而最為重要的,是麥克斯敏銳而似乎若無其事的目光,努得爾斯和卡蘿兩人的目光與行為始終在這目光的監視、控制之中。麥克斯如同一個導演,在監督著這一劇目的每一個細節的執行。事實上,甚至努得爾斯與卡蘿的共謀、努得爾斯的告密,都是麥克斯行動與計劃的一部份。卡蘿正是從他微妙的暗示中獲得了「靈感」,從而向努得爾斯提出建議的。(所謂「我是從你的朋友那裡得到這個主意的。他老是取笑你,說你每次經過這裡,都要尿濕了褲子,說你總是想盡辦法讓警察戒備,好搞不成這次行動。」)於是,通過努得爾斯,麥克斯將不露一絲痕跡地假借警察之手消滅他的全部同伴,奪取他們的財產,同時成功地「消滅」私酒販子、黑幫麥克斯,以便他能改頭換面、平步青雲。而在這一段落中,正是卡蘿的目光遮避了麥克斯的視點以及他真正的動機。此刻,觀眾在努得爾斯的視點及影像的獨立結構的認同中,傾向於將麥克斯的目光指認為某種疑慮。實際上,當努得爾斯痛下決心,走向辦公室的時候,是麥克斯的目光目送著他,直到他帶上了身後的房門。一直等到時間足夠充裕之後,麥克斯才去敲門,他走進房間,似乎隨手將努得爾斯慌亂中掛反了的電話聽筒擺正。此時,他完全放心了:一切已萬無一失。影片《美國往事》由此成就了一部迷人的故事,一個關於美國的神話,同時成為了對美國神話的拆解。
Ⅲ.男人·女人·結構
在影片《美國往事》中,萊昂內依照主流話語的另一重要參照系——女人——結構起努得爾斯/麥克斯這一美國夢的正反面。在經典敘事的動素模型中,女人作為客體這一動素最為多見的扮演者,始終是男性/英雄扮演者的追求、尋找對象。「英雄救美」——英雄為了美麗的女人去戰鬥、去歷險,而女人則是英雄獲勝的錦標,一種僅次於聖盃或王冠的錦標。對女人的成功征服與佔有,是指認、衡量英雄成功的潛在參照系,同時直觀地成為法勒斯(Phallus)權力的行使與實現。而在《美國往事》中,女人同樣成了萊昂內「成人寓言」中重要的參數。
在敘事的表層結構中,努得爾斯始終是一個粗野的、極具攻擊力的強暴者,他不斷出現在色情場景里,兩次被呈現在強姦場面之中。這似乎是通常意義上的男性性格、男性力量的表露。與他相比,麥克斯則「文弱」或冷漠得多。然而,正是在與女人的關係式中,萊昂內在一個完整的男權話語系統中將努得爾斯呈現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首先,在《美國往事》這一強盜片敘境中,為數不多的幾個女人,都曾以種種方式與努得爾斯相關,都曾為努得爾斯所佔有或強暴。但他卻不曾真正「獲得」或「佔有」她們中的任何一個。而每一個「努得爾斯的女人」,最終將為麥克斯真正獲取並徹底佔有。努得爾斯旺盛的慾望、野蠻的強暴行為與其說是一個男性英雄的業績,不如說是對他失敗的印證。在第九組合段,努得爾斯/麥克斯憑藉敲詐成功地從路段巡警手中接管佩姬,從而獲得了他們的第一次性經歷。然而正是在這一場景,影片敘事人極為含蓄地使努得爾斯、麥克斯一現其「優劣」。儘管是努得爾斯急匆匆、興沖沖地率先進入樓頂的棚屋去佔有他覬覦已久的佩姬,但片刻之後,他便一臉沮喪地「敗退」出來。繼而進入的是麥克斯,他久久地滯留其中。由棚屋輕拂的簾子(後面久久地傳出佩姬的笑聲)的中景,鏡頭切換為近景中的努得爾斯,少年的臉上泛起一縷不無酸楚的、無奈的微笑。接下來,是在鑽石劫案中,努得爾斯野蠻地強姦了卡蘿。但這與其說是粗野的衝動,不如說是努得爾斯的一次「道德行為」,一次「好男人」對「壞女人」——背叛丈夫、向情夫出賣商業情報——的懲戒行動。然而這一被努得爾斯首先佔有的女人,卻在此後不久成了麥克斯忠貞而痴心的情婦。也正是麥克斯最終奪走了黛布拉,努得爾斯生命中惟一的愛與寄寓。
不僅如此,努得爾斯作為本文意義結構中的失敗者,還在於他非但不是一個成功的女性的征服者,事實上,他經常處於性別角色倒置的尷尬情境之中。他對女人的窺視、侵犯性行為,不僅常常是為女人所誘發的,而且女人的大膽與主動,則不斷使努得爾斯處於被驚嚇、遭侵犯的境況里。努得爾斯對黛布拉的窺視,實際上是為黛布拉所默許、鼓勵並期待的,而且黛布拉有意地在努得爾斯的窺視中裸露出自己的身體,有如一個穩操勝券的、殘忍的貓在和老鼠玩遊戲。而當努得爾斯在廁所的鎖眼中看到佩姬走來,有意拔開插銷,暴露出自己時,換來的只是佩姬的輕蔑、戲弄。當卡蘿毫不掩飾地表達她對努得爾斯的興趣、慾望,並採取了一種無恥的主動時,努得爾斯的全部反應只是厭惡和退縮。在《美國往事》的敘境中,對於女人,努得爾斯是富於魅力而又無足輕重的。除卻作為一個強悍的男性,他全無價值可言。
顯而易見,在影片所呈現的人物關係中,至關重要的一組是努得爾斯/黛布拉/麥克斯。事實上,《美國往事》是一個關於超越性的男性情誼的影片,同時也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愛情故事。在影片的雙重主人公努得爾斯/麥克斯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個極為重要的聯繫與障礙:黛布拉,三人間始終存在著一種微妙的三角關係。早在20世紀20年代的故事中,少年努得爾斯躲在公寓廁所中閱讀的書籍《馬丁·伊登》,作為一個文化符碼,不僅已清晰地確認了努得爾斯在本文的男權話語系統及意義網路中作為失敗者的位置,而且暗示著努得爾斯/黛布拉故事的結局。在傑克·倫敦這部著名的小說中,來自下層社會的馬丁·伊登愛上了一個富家女。前者有著強健的體魄,後者則柔弱纖細,如同「一枝淡金色的細莖花朵」,但她背後的金錢、權勢和女人的無常無情,終於使馬丁·伊登備嘗了在心理上遭挫敗、被閹割的命運。當然,努得爾斯/黛布拉的故事並非對傑克·倫敦小說的重述。在故事之初,努得爾斯和黛布拉之間,並不存在著任何階級的溝壑,兩人都是紐約布魯克林貧民區長大的孩子,一對儘管說不上兩小無猜,但畢竟青梅竹馬的夥伴,而且他們顯然深刻地相互吸引。這是一個或優美或淒婉的愛情故事的開端,這個愛情故事確乎在努得爾斯那裡延伸開去,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正是這個愛情故事,使努得爾斯呈現為強盜片/情節劇中的經典美國英雄:一個粗漢,但柔情俠骨,心細如絲。在他殘暴、粗野的黑幫生涯事,他的心中始終保持著一處聖壇、一塊淨土。從影片的第三大組合段開始,敘事人已然將少年努得爾斯對女人的行為呈現在雙重標準之中。一邊是他對黛布拉的痴情,一邊是他對佩姬的慾望。黛布拉始終是他心上的女神,純潔的戀人,而洗衣女佩姬則是他發洩青春期騷動慾望與好奇的對象。然而,略去了史前史,在20世紀20年代故事的第一個「愛情」場景之後,麥克斯立刻闖入了努得爾斯的天地。在回瞻與追述的視野中,十分明顯的是,麥克斯和努得爾斯一樣深深地為黛布拉所吸引,但在努得爾斯和麥克斯之間,並不存在著任何真正的競爭,更不必說公平競爭。因為對努得爾斯的情感,麥克斯和所有的人都洞若觀火;而對麥克斯的隱情,努得爾斯和其他人卻近乎一無所知。事實上,這正是通過敘事的類比結構對獨立結構的遮蔽來完成的。對於麥克斯來說,他不僅將努得爾斯對黛布拉的迷戀一覽無餘,而且他更為深刻地洞察了努得爾斯本人也不甚了了的、他與黛布拉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如影片的獨立結構所呈現的,在故事的開端,努得爾斯與黛布拉之間已然存在著比馬丁和富家女之間更為深刻的鴻溝。它並不顯現在現實之中,而是呈現在未來的設計里。除了一份赤誠的愛,努得爾斯不能給野心勃勃的黛布拉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因而他也難於在這幅未來圖景中擁有一個真正的位置。麥克斯對這一隱秘的深知,同時也成為他的一份自知。他比努得爾斯遠為清醒地意識到,對於黛布拉說來,一份一往情深的愛和一個堅強有力的懷抱是遠遠不夠的(而且在這種意義上,他顯然不是努得爾斯的對手),如果他不能徹底改變他的現實,他永遠不可能真正得到或佔有黛布拉。於是,他並不去著手進行類似「無用功」式的嘗試。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有效地隔離開努得爾斯和黛布拉就足夠了。他隱秘地將黛布拉安置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未來圖景中,也只有在這幅未來圖景中,黛布拉才具有她真正的價值和意義。他可以等待,而這正是另一種經典「男子漢」的品格。在影像的類比結構中,觀眾可以清楚地意識到麥克斯不斷在離間著努得爾斯和黛布拉,但我們和努得爾斯一樣,傾向於將麥克斯的動機理解為情深意篤的朋友對異性戀人的忌妒。在努得爾斯/黛布拉/麥克斯這一微妙的三角關係中,有趣之處在於,黛布拉的情感無疑是傾向於努得爾斯的。她愛努得爾斯,儘管從一開始就極為無奈而清醒地意識到這愛的無望,一如少女黛布拉的那首情詩:「我親愛的,有著水晶般的心靈,有金子般的頭髮,他永遠潔白無瑕,他的眼睛又大又亮,他的身體如象牙一樣潔白堅實。然而他永遠也成不了我的愛人,他是個窮光蛋,哦,多遺憾!」但她仍忍不住要傾吐,「努得爾斯,你是惟一的,我一直……關心的人。我總覺得親切……」而對於努得爾斯來說,黛布拉是他心靈中最重要的支點,正像他對黛布拉的傾訴:「(在監獄裡)我每天晚上都在想你,沒有人能像我一樣愛你。你不能理解我是怎樣地想念你。我想,黛布拉活著,她在外面活著,她給我活下去的意義。」但和努得爾斯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黛布拉遠比努得爾斯更為清晰地洞穿了麥克斯的離間和這一行為的真正動機。正是她兩次用:「去吧,你媽叫你呢!」回答了麥克斯對努得爾斯不近情理的呼喚。不僅如此,她對麥克斯的洞悉還在於那是一種同類間的深刻的相互理解與默契。他們同樣野心勃勃,同樣出身微賤而不甘居人下,即使成了無冕的黑幫之王或布魯克林的舞蹈女王,街區的小天地也絕不足以滿足他們做人上人的慾望。在黛布拉一無返顧地前往好萊塢/「太陽城」(在失魂落魄的努得爾斯的視點鏡頭中,列車窗旁的黛布拉決絕地拉下了窗簾,並不把一線留戀的目光留給故鄉)之後,麥克斯花費8000塊錢買來一把17世紀教宗的座椅,只為了「我坐呀」,正是作為一個闡釋符碼定義著麥克斯惡性膨脹的慾望。他和黛布拉與努得爾斯一樣,也有著豐富的情感和記憶,墓室大門上菲利普的排簫曲和麥克斯/黛布拉之子的名字:大衛(努得爾斯的名字)似乎成了另一組重要的闡釋符碼,但他們絕不會為這一切所束縛。一如美國影評人S.卡明斯基所指出的:在萊昂內的影片中,「家庭生活很渺小,不斷被自私的惡人所毀掉。這些惡人不是出於仇恨,而是為一種冰冷無情的利己興趣所驅使而行動。」[〔美〕斯圖華特·卡明斯基:《評萊昂內》,《美國電影作者詞典》,轉引自北京電影學院《教學編譯參考》,1991年第1期]在全片最為溫情、豪華的場景(組合段22)之後,努得爾斯粗野地強姦了黛布拉。這與其說是男性極力/暴力的行使,不如說更像是一種孱弱而絕望的哀鳴。正是那種深刻的理解與默契,而不是情感,使黛布拉最終投入了麥克斯的懷抱,而且事實上成了麥克斯罪行的「事後從犯」,以更為殘忍的方式參與了、至少是預設了麥克斯對努得爾斯的劫掠、欺騙與叛賣。麥克斯成了最後的勝利者。是麥克斯,不是努得爾斯徹底地實踐了美國夢的全部:富甲一方,躋身高位,並擁有了少年、青年時代可望而不可即的姑娘。
然而,萊昂內顯然不曾認同於實踐了美國夢的成功者:麥克斯和黛布拉。一如努得爾斯是片中人物化的敘事人,是影片的空間視覺結構與敘事結構的中心,他也是萊昂內的認同點。於是,在影片的結局中,萊昂內設置了兩個重要的場景,以呈現35年之後——1968年,努得爾斯與黛布拉、麥克斯的重逢。第25組合段的最後一個鏡頭,是攝影機緩緩推成貝里慈善院奠基留影上黛布拉的特寫鏡頭,伴著憂傷的音樂,鏡頭疊化為劇院化妝室內、鏡中的黛布拉。與貧窮、衰老、孑然一身的卡蘿形成對照的是,豪華劇院的化妝間、名劇《埃及豔后》的巨幅招貼、室內的無數鮮花所包圍著的黛布拉。但有趣之處在於,在這一特定場景中,剛剛結束演出的黛布拉,頭上戴著假髮、臉上塗著厚厚的油彩。在整個段落中,她一直在卸裝,但始終未能完成。於是,黛布拉濃重的化妝猶如一張假面,遮蔽起她真實的情感,並如同一個標示符號,喻示著她試圖繼續掩藏的、沉沒於35年歲月中的真相。而一個與之對應的重要的修辭手段,是此段落中鏡中像/謊言與鏡外像/真實間的交替使用。在黛布拉不無傷感的鏡中像之後,努得爾斯出現在這一鏡中的、雙人中景里,這對少年時代的戀人在「鏡中」相逢,他們並沒有四目相向,相反他們只是在鏡中彼此凝視。儘管這是努得爾斯揭秘之行的起點,儘管從這裡開始,努得爾斯的一生、他的全部記憶與歷史將重新估定,但此刻,這幅雙人鏡中像,只是一次感傷的重逢,只是久遠的過去、一次「水中月、鏡中花」式的、少年之戀的指稱。此後,在這一段落中,努得爾斯的多為鏡外像,歲月書寫在他蒼老、疲憊的臉上,但他專注、幾乎是痛楚地要求答案與真實;黛布拉的鏡頭則多呈現為化妝鏡中的中景,歲月幾乎沒有在她臉上留下痕跡,儘管不無溫情,但閃爍其詞與微妙的疑懼使她失去了應有的雍容。用努得爾斯的話說,她「現在的演技很拙劣」。終於,當她和麥克斯的兒子來到門外,當努得爾斯的追問已不能再迴避,黛布拉被迫艱難地面對真相,攝影機緩緩地以一個180度的搖拍,由鏡內而至鏡外,由鏡中的黛布拉搖至鏡外、對鏡而坐的黛布拉。此時,也是此段落中惟一的一次,黛布拉對著鏡中的努得爾斯,說出了她所能說出的告白:「努得爾斯,我們都老了,多少保留著一些美好的回憶。如果你出席星期六晚上的派對,這一切將蕩然無存。那是後門,從那兒出去,一直走,別再回來。我求你,請你……」當黛布拉意識到她已無可迴避時,她並沒有懺悔或直言,她只是以哀懇和告誡的方式肯定了努得爾斯的猜測。而正是這一段告白,第一次暗示出黛布拉和麥克斯一樣,對努得爾斯其人有著深刻的洞察與理解,她深深地懂得:對努得爾斯說來,即將發生的一切比曾經發生過的陰謀更殘酷。也正是在這一告白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黛布拉試圖在麥克斯的網羅面前保護努得爾斯,試圖阻止麥克斯最後一次實現他「冰冷無情的利己興趣」。但是,當完美的謊言的景片既經撕裂,當返歸舊日、探明真相的旅程既經開始,努得爾斯已不可能停下。因此,儘管他的問題「如果我從正門出去,我就會變成石頭嗎」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仍毅然打開了前門。答案已昭然若揭:伴著憂傷、淒婉的音樂,台口,站起一個紅髮的少年,彷彿少年麥克斯的再生,強烈的逆光為他勾勒出了一道眩目的光環,攝影機緩緩地推上去,如同舊日歲月的重現,猶如一個心靈的幻影,同時是對那一切的粉碎。淚水無聲地淌過黛布拉的面頰,「他是貝里部長的兒子,叫大衛,和你一樣。」大衛的近景鏡頭緩緩地疊化為長島貝里宅邸一扇半掩的窗口,窗子半推開來,近景鏡頭中,露出貝里/麥克斯蒼老的面容,他望向畫外。第一次,未經任何掩飾與遮蔽,影片出現了麥克斯的視點鏡頭,並將他指認為一個仍強有力的控制者,一個真正高明的、隱身的惡魔「導演」。
極為有趣的是,如果說,在組合段26努得爾斯與黛布拉的重逢時刻,鏡中像與鏡外象形成了謊言/真實、追索真相間的對抗,那麼,在組合段27、努得爾斯與麥克斯重會的場景中,努得爾斯則成了記憶/謊言的護衛者,是麥克斯在無情地暴露著真相。和前一組合段一樣,在這一段落中,努得爾斯和貝里/麥克斯之間不存在真正對視,他們彼此迴避了對方的目光。而且,在這一段落中敘事人的重要行為之一,是幾乎摒棄使用努得爾斯/麥克斯之間的雙人中景。如果說共有畫面空間意味著共有心靈空間,那麼,此時,在人物化的敘事人/類比結構的中心/努得爾斯那裡亦不復存在那一同生共死的幻覺與謊言。此外,在這一段落中,努得爾斯/麥克斯間的對切鏡頭,不存在著任何意義上的對稱,甚至不存在著人物間對切鏡頭所必需的視覺上的均衡。與努得爾斯的正面中近景鏡頭相對應的,是大景別中被置於畫面邊角處的麥克斯,而且特定鏡頭的選用,在視覺上拉開了麥克斯與努得爾斯之間的空間/心理距離。在這一段落中,記憶與真實的對抗,被結構為稱謂使用上的抗衡。麥克斯使用了「努得爾斯(麵條)」這一少年時代親昵的綽號,因為他希望抹平35年歲月的鴻溝,聯結起記憶與現實;而努得爾斯則自始至終使用「貝里部長」這一尊稱,他拒絕承認面前的這位要人是他35年前死於風雨之夜的摯友,他必須固守他為血淚所浸染的記憶,否則他將一無所有,他生命的意義將被呈現為一個悲慘的笑料。似乎是一次公正或報應,麥克斯將懲罰、處決他的權力交給了努得爾斯;似乎是一次懺悔或人類良知的發露,麥克斯至為清晰地描述他對努得爾斯的全部作為:「我奪走了你全部生活,佔據了你在世界上的位置,奪走了你的一切。我搶了你的錢,搶了你的姑娘,讓你忍辱負疚35年,以為是你殺了我。」但是,如果說這是一次機會,那麼一如昨日,它是屬於麥克斯,而不是努得爾斯的。所謂「給我一次機會來了結我欠你的」,因為「我已經是一具殭屍」,而且「他們要清洗我了」。對努得爾斯來說,這與其說是一次公正,不如說是一個更為殘忍的剝奪。因為不論是真相還是金錢,都歸還得太遲了,而他將失去的卻是惟一的「財富」——他生活賴以支撐的信念以及他的全部記憶。麥克斯將再一次成為勝者,他將獲得他「惟一能接受」的處決者,全無屈辱並內心安然地死去(因為他已無法逃離逼近的「清洗」或審判);而努得爾斯則必須一無所有地繼續活下去,並且繼續絕望地背負著殺死自己「生死朋友」的痛苦。於是,是麥克斯一而再、再而三地試圖喚起記憶,這記憶指稱著背叛、索求著復仇。為了徹底地在喚起記憶的同時改寫一切,麥克斯甚至取出了那塊懷錶——它正是麥克斯與努得爾斯友誼的開端,同時也是麥克斯對努得爾斯的第一次掠奪和勝利。事實上,當麥克斯把手槍推向努得爾斯,並誘導:「你為什麼不開槍?」時,對努得爾斯說來,誘惑太強烈,以致和麥克斯一樣,他必須藉助於記憶——「真實」的記憶,洗淨謊言和為謊言所編織的記憶。於是,當鏡頭緩緩推成手槍的特寫之後,切換為努得爾斯的推鏡頭。特寫鏡頭中,努得爾斯朦朧的淚眼似乎穿過了歲月的暮靄:坐在馬車上的麥克斯(組合段7);努得爾斯焦慮地在哈德遜河上尋找著「落水」的麥克斯(只是這一次,畫面上方,劃向駁船的手臂消失了)(組合段13);建立基金時,五兄弟拍疊在一起的手(組合段14);小多米尼克最後的話:「我要睡了。」(組合段15)有趣之處在於,他的回憶終止於1921年。事實上,一如影片的獨立結構所呈現的,正是在1921年組合段15的結尾處,在那一重要的視點反轉的時刻,麥克斯開始了他朝向「貝里部長」的攀緣。努得爾斯必須再次從記憶——「真實」的記憶中汲取力量,20世紀20年代的故事成了他最後的防線,他必需在麥克斯——謊言的製造者面前護衛謊言,因為那便是他的一生及其全部意義。他以自己的「故事」(僅僅是一個「故事」、一次「敘事」)向「貝里部長」/麥克斯告別:「你看,部長先生,我也有一個故事,跟你的故事很像。很多年前,我有個朋友,一個生死兄弟。我想救他的命,沒想到卻殺了他。要說報復,對我對他都是。別當真,貝里部長。」他成功了,只有這一次,在麥克斯面前,他成了一個勝利者,一個因拒絕審判而宣判了麥克斯的勝利者,以拒絕真實的方式,努得爾斯絕望地挽救了自己滿盤皆輸的生命記錄。於是,在一個情節劇/強盜片所必需的、懲惡揚善的「大團圓」結局中,麥克斯自戕於垃圾車中。然而,悄然駛去的垃圾車的尾燈,在努得爾斯的視點鏡頭中幻化為一輛迎面駛來的汽車的前燈,車上,擠滿了三十五年前廢除禁酒令之夜狂歡的青年男女,他們高唱著「上帝保佑美國」,沿路拋擲著酒瓶。當車燈眩目的光環隨汽車遠去時,鏡頭反打為貝里部長後門旁,努得爾斯蒼老、恍惚的面容。努得爾斯終究慘敗了:他已不能分辨,這究竟是長島部長官邸中的重聚與永別之夜,還是35年前那個狂歡而慘烈的夜晚,得而復失,他再一次失去了他的「生死兄弟」。這一次,他沒有「錯」。同時因「沒有錯」而兩手空空,一無所有,甚至不能痛悔、不能自責。
影片《美國往事》有著首尾相銜的封閉結構。影片的第一組合段開始於1933年那個廢除禁酒令的暴雨之夜以及倖存者努得爾斯的翌日。而從第一個鏡頭起,時空交錯的情節段落中始終貫穿著一聲似乎全無來由的、尖銳刺耳的電話鈴聲,直到場景6,才顯露出聲源:一間無名的辦公室,辦公桌上的一支電話響了,桌上的身份牌上寫著:哈洛因警長。繼而,電話鈴聲在場景7中變為了一聲尖嘯,「中國劇院」中的努得爾斯瘋狂驚懼地翻身坐起。而當影片結束時,場景再次回到了「中國劇院」,回到了1933年,那個暴雨、暴力之夜的翌晨。所不同的是,刺耳的電話鈴聲已悄然消失,同時洗去了這一場景中曾無處不在的噪動、威脅,在舒緩、憂傷的音樂聲中,一切顯得寧謐、從容,甚至有幾分寂寥。於是,這序幕和尾聲,成了努得爾斯心靈的告白:序幕中,那貫穿了不同場景的刺耳的鈴聲,無疑是努得爾斯向警方告密的電話。它如同一個無所不在的無情的指控,貫穿了努得爾斯此後的一生,貫穿了他35年間漂泊流浪、埋名隱姓的絕望生涯。那是努得爾斯對1933年那一悲劇之夜的惟一解釋:由於他的「出賣」,他的三個情同手足的兄弟一道暴屍雨夜的街頭。對努得爾斯來說,這尖銳的鈴聲,甚至比復仇女神的追逐更為殘酷而恐怖,那是永恆的痛悔、負罪和絕望。然而,35年後的「還鄉之行」徹底地倒置了一切。似乎是一個來得太遲的赦免,實際上,卻是一個更為徹底的摧毀與剝奪。宣告努得爾斯無罪的同時,是宣告他人生意義之根基的崩塌。於是,努得爾斯必需為保有他痛苦的記憶而搏鬥。他必需執著於這一謊言與「幻覺」,於是,在一個更為荒誕、殘酷的夜晚之後,他再次讓記憶停泊在35年前那個心碎的雨夜和清晨。但這終究是一個改寫過的記憶:濾去了絕望與驚懼,留下的卻是無盡的留戀與悵惘。那一夜成了努得爾斯最為珍視的時刻,那一夜的心碎與痛苦成了努得爾斯難於再度擁有的幸福。因為那是一個篤信友誼的時刻,那是一次為兄弟情誼而獻身的實踐:為了挽救友人的生命,努得爾斯竟可以向警方告密;而為了兌現同生共死的誓言,麥克斯三兄弟共同赴死;此後努得爾斯行屍走肉的生活則是苟活者的自我懲罰與贖罪苦行。因此,影片的尾聲,終止在努得爾斯的特寫鏡頭之上,畫面中,年輕的努得爾斯突然綻露出一個燦爛的微笑。畫面便定格在這張幸福的笑臉上。如同一個反諷,一次對迷人的美國夢的倒置與拆解,同時又是對這一迷夢的一次飽含辛酸的流連。
萊昂內用《美國往事》成就了他影片序列的一個高峰,一個為歐洲文化的「悲悼」意味所改寫的美國故事。一個好故事:「從前在美國……」一部「成人寓言」,關於友誼與叛賣,關於成功與失敗,關於男人與女人。「美國夢」在展露了它的正反面的同時,展露出這一特定文明的殘忍與無情、病態與頹敗。
(完)
【作者簡介】戴錦華,1982年畢業於北京中文系,曾任教於北京電影學院電影文學系,現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系教授。從事電影史論、女性文學及大眾文化領域的研究。
本文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5f9190100blxs.html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