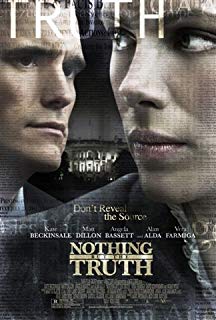2009-06-18 10:50:12
把好題材拍成爛片的原因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我只從電影的角度來評論。而不是政治的角度。
這本是一個很不錯的題材,卻被拍成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爛片。
硬傷之一:錯綜複雜的理念
美國電影和歐洲電影的差別之一是他們的思維方式。歐洲電影的思維方式和中國教育模式有點像,都是先理論再實踐。先確定一個想要表達的哲學精神,再構思一個故事去表達它。美國的電影製造方式則反了過來,先從一個精彩的場景,擴展至一個精彩的故事,然後往這個故事裡添加一些精神、原則and理念etc.
這個片子很明顯的展現了美國電影的思維方式,主創人員受到一個精彩的真實事件的啟發,決定把它製作成一部影片。然而在為這個故事添加某些精神和理念的這個環節,創作者陷入了困境。這樣一個非凡的事件,折射出的角度太多,可添加的理念太多,讓創作者難以取捨。究竟什麼才是他們最想添加為核心理念的呢——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母愛的共鳴?人性本善?高貴的誠信?……?選擇太多,讓創作者無所適從,拋棄任何一個都覺得不忍心,選擇任何一個又覺得太單薄。於是,他們選擇了這樣一種模糊的定位,藉由片中那句話:「我在這裡是代表她,而不是代表原則。然而對於一個高貴的人而言,原則和人格是合二為一的。」這樣一句話充分暴露了創作者試圖模糊理念的做法:既沒有說清楚原則是什麼,也沒有說清楚是什麼高貴的人格。一盤大雜燴,吃不了你就兜著走吧。
硬傷之二:失敗的敘事
對於劇本創作者來說,有一個經典的小故事:假設有四個人在打麻將,而桌子底下有一顆定時炸彈,到了某個時候,炸彈就會爆炸。怎樣讓觀眾覺得整個故事更精彩,是一直讓不知情的觀眾看這四個人打麻將,直到突然之間炸彈爆炸呢,還是一開始就讓觀眾知道桌子下有顆炸彈?
這個小故事聽起來好像很簡單,但操作起來往往很難。對於本片來說:「炸彈」無疑就是泄密者是誰這個懸念。那麼,我們來看看,創作者究竟選擇了哪種方式來引爆炸彈呢?
顯而易見,影片選擇了瞞住不知情的觀眾,讓這顆炸彈最後才爆炸。但是,果真如此嗎?非也。我相信,不止我,還有許許多多的觀眾,在看過幾分鐘後,就能夠馬上猜出最後的答案是:孩子。在影片的最初幾場戲裡,密集的交織了兩類場景,一類是關於總統刺殺和情報人員身份暴露的場景,另一類則是兩個母親和孩子們在一起的場景。從電影創作的專業角度來看,影片(尤其是美國電影)的第一幕,是必須建置主要人物和事件環境的,兩類場景的密集交織,無疑暗示、甚至是明示了謎面和謎底之間的必然關係。就更不用說好幾處別有用心的鏡頭對準孩子的面部大特寫了。即使不從專業角度,只從一個普通觀眾的經驗出發,一個如此嚴肅的、政治的、懸疑的影片,卻在開頭幾分鐘花費寶貴鏡頭對準母親和孩子,這是絕對可疑的。
那麼,就是說創作者選擇了讓觀眾一開始就看到桌子下的炸彈,然後替打麻將的人著急上火?顯然也不是這樣。在整個影片的中間部份,除了幾處輕描淡寫的親子戲,完全沒有正面描寫、甚至沒有提到泄密者的真正身份。影片想保留這個懸念,想讓炸彈突然爆炸,以製造震撼效果。正因為如此,正因為這個懸念必須保留到最後,我們無法看到女主角心裡真正的掙扎是什麼,我們無法看到,是什麼讓女主角堅持,是什麼讓女主角動搖,是什麼讓她痛徹心扉,又是什麼讓她堅定立場。我們能看到的,就是她的「堅持」,而不是「堅持的原因」。看不到就只能揣摩,而似乎創作者也希望我們胡思亂想,於是引導我們朝各個可能的方向,各個可能的理念: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高貴的誠信?……事實上,當最後這顆炸彈爆炸的時候,作為一個觀眾,我們已經累了。我們揣摩了太多,而那些僅僅只是我們自己的揣摩而已。甚至,我們連女主角做過什麼都不記得了。因為我們在整個影片的過程里都沒有看到她的「原因」,就更別提和她產生共鳴了。
硬傷之三:人物
美國電影最擅於尊崇的原則之一是,人物們必須在影片的一開始有一個明確目標,無論在影片結束之時,這個目標實現與否,人物們都必須在這個實現目標的過程中受到改變:或者是領悟了什麼真諦,或者是發掘了自己的什麼內在,或者是意識到自身的什麼錯誤,或者是受到了情感上的某種啟迪。總而言之,人物們追求自己的目標是一條外在的線索,人物們改變自己(或被改變)是影片真正的核心線索。而一部成功的影片的精彩往往在於,人物們是怎樣改變自己的。
在本片中有兩個主要人物,一個是女主角,一個是非要找出「真兇」的律師。他們的目的都相當的明確,女主角的目的是保守秘密,律師的目的是讓她說出秘密。現在我們來看他們兩個有沒有改變什麼。先來看律師,他不可理喻的強悍、執著、不服輸,一直堅持到了最後,既沒有交代他的心理活動,更沒有解釋他這麼做的「人性的原因」。我理解。因為他不過是一個符號,一個「政府」的符號。然而政府(或者說政治立場)是一個不具有人格的主體。再來看女主角,不能說她沒有改變,因為在影片的末尾,她妥協了——然而這個「改變」是否屬於「內心的,自身的,人性的」改變呢?退一萬步,即使是,即使是基於「內心的,自身的,人性的」改變,影片對於這個改變只有幾秒鐘的交代:女主角略作思考後說:「如果我答應,我只想滿足一個條件」。我們完全看不到她的心理活動。我們看不到這個過程。這個過程被徹底簡化了——簡化成了無過程。
除了以上三點,還有許多細節上的詬病,在所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