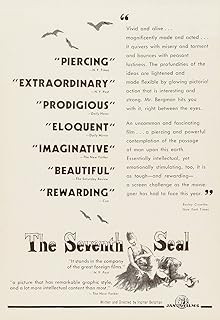2012-12-03 02:10:02
馬戲團約瑟夫的道路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該片片名來自《聖經•舊約全書》中的最後一部份《啟示錄》:天主的羔羊(耶穌)打開「第七封印」,這是世界末日和最後審判的信號。整部影片圍繞著這個歐洲文化的傳統主題展開,即個人如何獲得救贖。表面是在寫歐洲中世紀的那個混亂、黑暗的時代的事,實際卻是藉此探討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生存狀態,探討現代人內心深處的矛盾。
影片的基本情節講的是參加十字軍東征歸來的騎士和他的僕人返鄉的一段旅程。路上騎士先是遇到了死神,他請求與死神對弈來決定自己的生死。之後騎士和他的僕人遇到了馬戲團的夫婦倆、馬戲團老闆、神學院學生、鐵匠和他的妻子等等人物,到最後騎士回到家,除馬戲團夫婦外所有人都死去為止,死神一直陪伴著。從騎士和他的僕人一路所遭遇的可以看出,當時的歐洲大陸正在鬧瘟疫,到處佈滿著死亡和恐懼的陰影。
這是取材於真實的歷史的,歐洲中世紀歷史上確實有過幾次大的瘟疫,主要是鼠疫,導致整個歐洲陷入一片荒涼,人口大約銳減了三分之一。十字軍東征也和這次大瘟疫有著直接的關係。瘟疫大範圍的破壞了歐洲的生產力,農民沒有出路,活不下去,社會動盪不安。教會就趁機出來作宣傳,說東方有多少多少財富,並且套上從異教徒手中收復聖城耶路撒冷的宗教的外衣,鼓勵大家組織十字軍進行聖戰,去征服東方。
伯格曼把影片的時代背景安排在這樣一個時候,無疑是有深意的。整個的畫面顯示的就是一幅世界末日的景像。上帝要把這個世界毀滅,重新來一遍。在這個時候,人的信仰發生了動搖,人類感到無比的迷茫,找不到方向。一切原來信仰的東西在末日來臨之際都顯得蒼白無力,生命的意義瞬間蕩然無存,人在這個世界上無法把握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這正是二戰後歐洲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伯格曼試圖通過這部影片向人們展示出一條通往光明的道路。他否定了騎士的道路,也否定了騎士的僕人的道路,更否定了以鐵匠、鐵匠的妻子、劇團老闆有代表的那種渾渾噩噩或者玩世不恭的態度。他最後的答案是馬戲團夫妻所代表的那種生活。其他人都被死神帶走了,受著末日判決的煎熬,只有約瑟夫一家人過著平安幸福的生活。
騎士所代表的是人類探索和追尋上帝的一種方式。他希望通過理性去認識上帝,認識死亡。他當初本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紳士,為著崇高的宗教理想,踏上了東征的道路。結果到了東方,發現教會所許諾的那些都是空的;回到歐洲,到處都是瘟疫、混亂和騷動不安。他相信人類知識的力量,這從他選擇與死神對弈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就可以看出,他有信心自己會贏,也就是說,神能做到的事,他也能做到。他向死神詢問所發生的一切是什麼原因,也體現了他的求知慾,他強烈的希望用理性來把握這個世界。
騎士的僕人所代表的一種人類的處世方式,和騎士本人稍有不同。如果說騎士是一個忠誠的教徒,他對人類自身力量的信心是在於他覺得通過人類的理性思考能夠理解上帝的對世界的安排,並且他認為這正是人類理性的任務,那麼騎士的僕人便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對人類自身力量的信心來源於他覺得人類就是這個世界的主宰,人類完全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需要任何神學上的繁瑣解釋。也許當他出發參加十字軍東征時,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他是,當他再次回到歐洲、回到故鄉的時候,我們看到,他已經對一切關於上帝的崇拜、關於人類罪孽的宣傳徹底失去了興趣。他拯救那個失去親人的年輕姑娘,懲罰神學院的學生,在酒館替約瑟夫解圍,打抱不平,所有這些行動,他都是在發揚一個「人」的精神,後面不存在神的力量。在他的思維里,全然沒有他的主人對神的那種敬畏之情。
如果我們套用柏拉圖對人類靈魂的三分法,我們可以說,騎士所代表的是人類靈魂的理性部份,騎士的僕人所代表的是人類靈魂的意志部份。理性部份追求對世界提出人類所能理解的知識性的解釋,而意志部份純是在發揚人本能的、原始的生命力。理性部份追問在神的主宰之下的人類世界何以可能,問的是「為什麼」,而意志部份追問的是人類怎麼樣控制身處其中的這個世界,問的僅僅是「怎麼做」。
神學院的學生,代表了腐朽、僵化的教會勢力。他們宣稱自己是上帝和人類之間的橋樑,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可是在這件華麗的、神聖的外衣之下,他們做的全是最世俗的、甚至最骯髒的事情。其實他們一點也不配做上帝的代表;在末日臨近之際,他們早忘記了自己的職責,有其他一切最普通不過的人們一樣只關心自己的私利——他們同樣將受到公正的審判。那些假借神的名義行惡事的人,比一般行惡事的人罪孽更大。騎士和他的僕人,以及眾多和他們有著相似遭遇的人,他們所受的苦,其實都是直接拜這批虛偽的神職人員所賜,這些神職人員用謊言騙取了他們的信仰,把他們送到遙遠的東方。
劇團老闆和鐵匠的妻子,代表了世上一類玩世不恭的人。這種人佔了人類的一大部份。他們貪圖一時的人世的享樂,不計較末日審判時的懲罰。鐵匠的妻子跟著劇團老闆私奔,可是在鐵匠找到他們,她看到沒有機會逃脫之時,她又轉而對丈夫獻起了慇勤,藉口說自己是被劇團老闆迷惑的(明明是她自己先賣弄風騷引誘別人的),轉眼之間就變了副臉孔,拋棄情人而重新投向丈夫的懷抱。劇團老闆先是勾引有夫之婦,後又作虛偽煽情的表演,騙取鐵匠的同情和原諒。這些都是人性中醜陋一面的寫照。人類自以為耍的這些小聯明很高明,實不知在上帝眼裡,這些都是看的清清楚楚的。無論耍多少伎倆,每個人都逃不出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命運。劇團老闆沒被鐵匠砍死,但隨樹倒下而摔死:結果都是一樣的。
鐵匠呢,鐵匠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他對事情沒有判斷力,別人怎麼誘導他就怎麼想,生活渾渾噩噩,似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從不對這個世界進行反思。他沒有騎士那種探索的精神,也沒有騎士僕人的勇氣。他的生活是無意義可言的。
至於死神,基督教是一神教,本沒有死神這個人物的,柏格曼在這裡創造出這樣一個形象,不過是把他作為一個執行上帝意志的工具而已,他本身並不具備神的屬性。當騎士詢問他時,死神說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的,世間的所有安排只有上帝一人知道。索取人類性命的任務在影片中由死神執行,在現實中由各種各樣的疾病、瘟疫、戰爭、饑荒等執行,兩者之間並無實質的差別。
死神由於酷愛下象棋,答應騎士通過一局對弈來決定騎士的生死,雙方之間的這盤棋其實像徵了人與神的鬥爭。人不甘心就這麼接受神為自己安排的命運,他要反抗,他要發揚自己的力量去對抗神的力量。在騎士這方面,代表的是人類偉大的、不屈不撓的進取精神。雖然他最後失敗了,但是從影片中我們看到,並不是他的棋藝不及死神,而是一來由於死神的欺騙,他泄漏了自己的戰術,二來,更重要的一點,是騎士遇到了約瑟夫一家,從他們身上他似乎找到了自己一直在追尋的問題的答案,因此當再次回到棋盤上時,他顯得有些心不在焉,好像不再屑於與死神交手,把生命也看的淡了。
最後說到約瑟夫一家,他們是解讀整部影片的關鍵所在。影片中的其他人物代表的都是黑暗、痛苦,整部影片的基調也是陰森的,只有約瑟夫一家,在這黑暗陰森的世界之中,散發出一片溫暖,他們一家是光明的、歡樂的,這不但與騎士、騎士的僕人、鐵匠、神學院學生等等人相反,也與當時的整個社會相反。
我們看到,每當鏡頭對準約瑟夫一家的時候,總的白色壓過黑色,光明、愜意、溫暖。死神的臉是沒有一絲血氣的,蒼白可怕,與他那套地獄般黑暗的大風衣搭配起來,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切生命都在這裡枯萎了。騎士的臉上佈滿了歲月的蒼桑,他的深邃的眼神、舒緩的舉止、風塵僕僕的著裝,整個給人的印象就是,他歷經了無數的世事的洗禮,有著洞察一切的智慧;不過,與這種深刻相伴隨的,常常有另一樣東西:憂鬱。而在約瑟夫那裡,這種憂鬱消失了,無影無蹤了,只餘下純樸、天真的歡笑。那麼智慧呢?他的智慧比其他人多,只有他和騎士才能看到死神。他的「智慧」也比騎士多,因為他還看到了聖母,並且最後只有他和他的家人沒有受到死神的侵犯。也許這裡這個「智慧」,說成「信仰」更準確。
約瑟夫不像騎士,去追尋一個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人類的理性是不能徹底理解神對這個世界的安排的。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看,如果說騎士代表的是理性,那麼約瑟夫代表的就是信仰。伯格曼對約瑟夫和騎士的命運的不同安排,其實要回答的是基督教神學中的一個基本的問題,那就是理性和信仰的關係。按照奧古斯丁的說法,信仰比理性更為根本,信仰是第一位的,理性是第二位的,有的東西,比如神蹟,理性是不能解釋的,在理性看來「神蹟」是荒謬的,但是信仰卻能夠解釋「神蹟」,而且,「正因為它是荒謬的,所以我信仰它」。哲學是在理性的範圍之內思考問題,遵循的是理性的原則,而神學是在信仰的範圍內思考問題,遵循的是信仰的原則,這就是神學高於哲學之處。人們說《第七封印》這部影片有著濃重的宗教氣息,而不僅僅是哲學的深度。單看它的題材,也就是以《聖經》中的一個典故為核心展開,還不夠,只有深入到基督教神學的內部,發現這部影片所回答的基本的神學問題,即信仰和理性的關係,才能深刻的理解伯格曼的寓意。
約瑟夫在塵世生活中的遭遇很差。他僅僅是一個跑江湖的馬戲演員,人們把他當小丑一樣看待;他是一個隨處都可能被欺凌、被侮辱的弱者,在酒館裡的遭遇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是,就是在這個塵世的弱小人物身上,我們看到了許多可貴的東西。他是一個心地的純潔善良的小伙子,懷著對上帝的誠實的信仰,對生活的樂觀積極的態度,對家人和朋友的無私的愛。他的生活很簡單,但是很令人羨慕。他過的日子也很普通、很沒趣,但他並不是像鐵匠那樣渾渾噩噩的;他信仰上帝,但他並不像騎士那樣穿入沒有出路的牛角尖。有什麼他能看到聖母和死神?因為他心無雜念,心地純潔。套用禪宗的話來講,那就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其他人之所以沒有約瑟夫那樣的眼光,只是因為他們被自己所犯下的重重罪孽裹住了,他們的信仰已經失去純潔性了。
這部影片最後不是以哲學的方式告訴我們答案,而是以神學的方式。伯格曼告訴我們,要以約瑟夫那樣的方式去信仰上帝,才能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