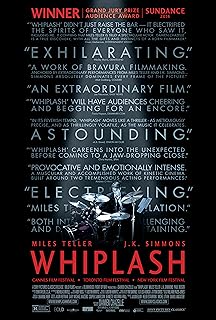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5-01-18 06:17:53
造才記
片子的觀賞度算是上品。但這樣的本子,為了將兩個角色閉合在一個關係簡化的衝突情境裡擠出最大的張力,肯定要犧牲不少合理性。果然,還沒過20分鐘,某些不能深究的就冒出來了:從開頭看,安德魯對老師的名氣和專業水準早有耳聞,不然不會一臉求認可,那為何對此人的魔鬼性格卻一無所知?那些過去被弗萊徹虐過的學生就沒有一個在非死不可上吐槽?而如果他事先有所了解的話,怎麼還會把他對自己的假親熱當真?還敢飄飄然地露出一副找抽樣(還真的被抽了)?
一個出身單親家庭、在原來的樂隊裡還頗不受待見的人,按常理不會這麼容易骨頭輕。如果他真的這麼輕了,那說明:1.陳丹青說的,米國人都沒怎麼被人欺負過。2.這人正處在「我果真與眾不同」的滿中二狀態。3.挨抽是活該。
有種說法是,天才不通人情世故很正常。可這個故事裡,根本沒有天才什麼事。真正的天才是不用人去逼的。我想弗萊徹自己對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一張嘴就問對方是不是出身音樂世家。 如果安德魯回答說「是」,那戲就不好演了。這個劇要的就是這種「一對一」的關係。安德魯身邊沒有別的參照物,弗萊徹的評價對他來說就是權威、判決和唯一的標尺。
於是「核心鼓手」成了關鍵詞,代表著弗萊徹賜給他的「位置」和認可。一路奮鬥、爭奪,直到鬧出了車禍。看到這段的時候,我很期望下面的情節是他在這次車禍中失去左手、終身殘廢什麼的……好吧,我總比編劇更邪惡。
但那完全有可能發生。在現實中,這種焦慮、暴躁和情緒失控更容易白白毀掉一個有才華的人,而不是成就他。安德魯對「核心鼓手」的捍衛和暴走,令人想起《上帝的寵兒》中的薩維埃里:因為我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在孤獨中奮鬥到血肉橫飛,所以連上帝都不可以奪走我的所得;哪怕有確實高於我的天才,也得滾開。
這是種「狠人」的邏輯。安德魯之所以把自己的心靈交給弗萊徹操控,是為了換取這個「上帝(或魔鬼)」把他塑造成一個「天才」。而後者儼然也沉迷於以這種「主宰」自許,儘管他從來沒造出過一個查理·帕克。他最後的設局表明,在「捍衛位置」這個問題上,他和他造出的「狠人」一樣,心如針尖,容不得一點觸碰和質疑。
「狠人」才會great嗎?也許。然而對藝術偏執的人,未必都「狠」到了藐視眾生的境界。貝多芬性格孤僻易怒,終身未婚,卻還得為平庸的親戚們花錢,無理由地溺愛幹啥啥不行的侄子。梵谷離精神病院只有一步之遙時,仍然畫著身邊平凡的郵差、醫生和農婦,還在努力「渴望生活」。用「狠」來變得great並無不可,但想great到在耳聾的狀態下邊打官司邊寫出《歡樂頌》,恐怕是夠嗆了。況且,對藝術本身的偏執,和中二病乃至對某個魔鬼教師的偏執,是兩回事。後來弗萊徹把學生的平庸歸結為聽了太多的「good job」,這使我忽然想起房龍在《人類的藝術》中寫的一段話:
「米開朗基羅的偉大,在於他深刻的不滿。不是對別人不滿,而是對他自己。像我們這個地球上的一切偉大人物一樣,像貝多芬、倫勃朗、哥雅、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這樣功底深厚的藝術大師一樣,他深知『完美』一詞的含義……這塊答應的福地,是不會白給我們人世上的任何人的。我們也永遠別想到達我們不可能到達的地方。因此,一切智慧,都出自這種深刻的不滿;一切偉大的藝術,也出自這種深刻的不滿。」
是的,真正的天才不用人去逼他,因為他會自己逼自己。鮮花和掌聲不會令他滿足,「good job」只會博他禮貌地說聲謝謝,之後什麼都不等於。勞倫斯・奧利弗爵士在後台聽著觀眾的歡呼,說「明天恐怕演不了這麼好」;巴爾扎克從午夜0點寫到8點睡下10點又起來,為的是在印刷廠的人來取之前大修自己的稿子;果戈理一遍遍改到臨終,終於還是燒掉了《死魂靈》的第二部;塞尚躲在埃克斯,沒完沒了地重畫同一座石頭山……他們所追求的高過任何世人的讚許,他們自己就是最嚴厲的魔鬼教師,那鞭策至死方休。
結尾與其說安德魯超越了極限,不如說他終於超越了中二病,知道等別人來賞飯吃是靠不住的,得自己主動逼自己一回。但他的前途呢?這又不能深究了。因為莫扎特只有真正的上帝才能製造,冒名頂替的「上帝」最多只能教人當薩維埃里。順利的話,將來能當上宮廷樂長。再往後,你是弄垮了別人,還是弄垮了自己,都悉聽尊便吧。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