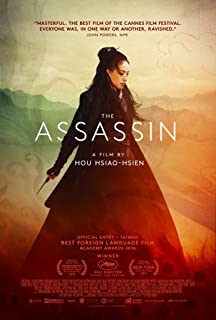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5-09-02 02:24:26
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也談《刺客聶隱娘》
看《刺客聶隱娘》,我的想法跟你不同。
你說窈七最終與新羅磨鏡少年遠走他鄉,是因為情愫暗生,心傷得以療治。你說窈七終歸如師父所言,看透自己「劍術已成,然人倫之情未斷」,自己終歸放不下。你說這個故事在講「一個人,沒有同類」的孤獨,你說窈七終歸明白孤獨是不可破,承認了宿命。
可我想到的,卻全是關於「青鸞舞鏡」。
「青鸞」的隱喻是什麼?「鏡」又是什麼?鏡中那讓青鸞欣然赴死的影子又是什麼呢?
我想到的答案,讓我自己也有些驚詫。
這個答案建立在對一個沒有直接言明的細節的思考之上,於是影片傳達給我一個編碼,我以自身體驗為出發,破譯出來。
這個細節我想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足見其重要性),因為導演用了一個很殘忍的方法讓我們不得不去注意到這一點。這個辦法就是預設了一個重要的交代鏡頭——面具下的那張臉,到底是誰。
這一點,簡直跟《全面啟動》最後的旋轉陀螺一樣讓人內心糾結,夜不能寐啊。
樹林裡的決戰是克制美學的高度體現——高手對決不必太過繁複,有時只在一招。
然而,如何才能一招就決出了高下呢?
還是一位朋友的影評點醒了我。他說聶隱娘將玉玦送還給田季安就已經算是任務失敗了,因為她已經違背了「不暴露身份」的刺客信條。
所以,聶隱娘斬下對手面具這一招是非常狠。這種狠倒不在於暗示「我可以一刀斃命卻手下留情」,而在於她拆穿了對手的身份,將一個刺客應持有的尊嚴打翻在地。於是,這場比武高下立見,二人沒有一句對話,表面上也看起來毫髮無傷,然而結果卻昭然若揭——聶隱娘贏了。
而後,我們看到了一個美到讓人動容的鏡頭,兩位刺客少女背向而去,一個走向平面移動,一個縱深移動,形成了一個美麗的夾角構圖——那感覺就如同鏡像一般,相互呼應。
我的同伴告訴我,劇本里寫著這個刺客的名字,喚做「精精兒」。如果稍微留心一下,會看到影片最後的演員名單上,精精兒與田元氏均為周韻扮演。所以,這個刺客的身份真實身份其實就是「主母」田元氏。
在唐代裴鉶《聶隱娘》的小說原著里,精精兒也只是一個敵方殺手,與聶隱娘素不相識,一番打鬥之後便「身首異處」。而電影之中,卻為精精兒安排了一個複雜的、不見光的身份(這種「不見光」在電影裡極簡處理到令人咋舌的地步,那個缺失的鏡頭該讓多少觀眾迷惑不解),想來是別有用意的。
這次比武結束之後,磨鏡少年為聶隱娘療傷,在這個段落里舒淇念動了那句經典的台詞「一個人,沒有同類」,更向磨鏡少年訴說了對嘉誠公主的追憶。或許有朋友認為二人關係由此破冰,因為「療傷」這個舉動本身是帶有隱喻的。這個段落之後,整個故事進入了後半段,情勢大為轉變,聶隱娘從刺殺田季安轉為暗中幫助,並且內心的狀態也似乎從「委屈」、「陰鬱」轉為了「坦蕩」、「通透」,那麼這種轉變到底是為什麼呢?
解釋不通的話,就只能歸結在磨鏡少年那裡了。不然,如何才能讓一個怨氣十足的姑娘突然變得盡釋前嫌呢?
其實問題的關鍵還在「青鸞舞鏡」這個隱喻之中。
這個反覆出現的意象,往淺處理解,可以就按照它直觀所示,講得是不得同類的孤獨。而我卻看著螢幕上聶隱娘與精精兒一言不發漸行漸遠的鏡頭,心中如一片玉匣打開,光照兩面,我看到了互為表裡的兩個少女,心中豁然開朗。
這個故事很怪啊。我當時就想,竟然兩個刺客都是逝去的少女。
這奇怪的身份對應,讓我覺得有趣。再回想一下,似乎忽然就明白了。
我明白了聶隱娘聽得嘉誠公主遺言說自己讓窈七受屈時,為何幪面慟哭。那是一種委屈,這種委屈讓這個螢幕上的聶隱娘與我們心目中的「聶隱娘」符號相去甚遠。唐代小說中的俠客,按照唐代李德裕的散文界定,稱之為「豪俠」。這篇文寫到,所謂「俠」者,乃「氣蓋當世,義動明主」。所以,那時的豪俠,不僅要有好的武功,更重要的是要對明主盡「義」。裴鉶的《聶隱娘》小說里,也的確提到了聶隱娘對自己投奔的明主百死而不辭。
在這種為明主盡「義」,報知遇之恩的傳統下,身為一個絕世高手,應該硬氣灑脫,事實上小說塑造的正是一位「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刺客形象。而電影裡的這個聶隱娘顯然不是這樣。她很不甘心,甚至對於嘉誠公主(自己的明主)心懷怨氣,對嘉信公主(自己的師父)一樣不能盡義。這是一個十分個人化的刺客形象,無怪當時在影院聽到有觀眾感慨,「這是中國版的殺手不太冷。」
但我覺得,這個「聶隱娘」最大的特點還不在於她有人倫之情(溫情脈脈,婦人之仁),而在於她有一種「哀怨」之氣,對於自己的命運覺得頗為不平,十分不痛快。
所以,周圍的人,無不覺得愧對於她,但即便是都向她正面表白了這種歉意,可她內心的缺失卻是無法彌補的。片子裡的聶隱娘陰鬱而神秘,可唯獨對一類人下不了手,就是「幼兒」。第一次失敗是因為這個原因,第二次解釋不對田季安不下手,解釋依然為孩子還幼小。如果我們單從表面理解這是一個有著天生憐憫,有著自己原則(不對弱小下手)的刺客,當然也說得過去。但我覺得,她之所以不能對那些幼小的孩子下手,倒不僅僅因為對方是弱勢群體,而最主要的,是因為在她的內心深處,這樣的幼兒恰恰就是自己當年孤獨無助被送往山裡的心靈映射。所以,在聶隱娘的心裡一直住著一個幼兒,這個幼兒是她小心呵護不忍殺死的。即便自己劍道已成(有了成人的技能),卻輕易敗給手無縛雞之力的幼兒(仍然不具備成年人的心智)。正因為她內心深處住著這樣一個不能成年的孩子,所以,她不能夠擺脫對於家庭的嚮往(站在樑上遙望著別人家的天倫之樂)和對於幼兒的保護(那就像保護曾經無能為力保護的自己)。
事實上,內心住著一位兒童也是人之常情,誰不曾在心底埋藏一處柔軟。但可怕的是,如果這個「孩子」失去了控制,就會生出一種孩子氣的怨毒之情。「中二病」就是這種怨毒的一種體現——你們都對不起我,這世界對不起我。這樣的怨毒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戾氣與陰鬱,像一道影子跟隨著看似(或者說「本應該」)能力很強的成年人。
那麼,能夠讓這樣的一個戾氣十足的孩子放下執念,則唯有打開她心裡久久不去的心結。
這個心結的關鍵,影片中是有多次暗示的。片中,無論父母、嘉誠公主還是田季安,幾乎口徑一致表達了對於窈七的愧疚——當年送窈七走。其中最最關鍵的資訊來自張震飾演的田季安一角的台詞。通過這段漫長的獨白,我們了解到,田季安與窈七因嘉誠公主的期許,從小定有婚約。而且這段青梅竹馬的情感絕非僅止於政治利益交換,而是有著兩小無猜的天然信任。可以看出,田季安也好,窈七也罷,心裡是有過對方的。但這段美好的姻緣還來不及開始,就因為元氏的到來戛然而止。如片中台詞所示,出於政治的考慮,田季安受命迎娶了元氏。影片惜字如金,不肯過多交代。又或者是導演思慮再三,毅然剪掉了那場幼年的戲份。但無論如何,一份美好初戀因為另外一個女孩的到來而終止,換了誰,會不嫉恨呢?
但我猜想,像窈七那樣的姑娘,她起初對於這個中原來的少女,抱有的情感會很複雜。一方面,這種來自中原的強勢文明會讓這個偏遠藩鎮的姑娘十分好奇、嚮往,另一方面,這種政治性的情感剝奪另她十分困惑、不解。所以,片中台詞說到,當初窈七擅長爬樹,經常站在樹上觀望著元氏。這一切引起了嘉誠公主的不安,擔心窈七做出什麼出格的事(劇本中原本是有打馬球擊向對方一場戲),所以才決心將窈七送與嘉信公主,學習劍術。以一個成年人的角度考慮,這樣的推測倒也合情合理的心理。可是,如果站在一個孩子的角度上來思考問題,或許窈七樹上的觀望就不僅僅只是一種嫉恨。那種情緒很複雜,想來應該是對這個有著自己所沒有的中原少女,感到非常困惑罷了。她站在樹上的觀望,無過是想把這種強烈的失落搞清楚而已,可在那些成年人眼裡卻理解成了惡意。而且,這種誤解所帶來的結果在窈七看來應該算是一種懲罰——從此過上了非人的生活,而這種生活顯然非她所願。這種不被理解的情緒日積月累,就化為了怨恨,這種怨恨持續太久,會上升成為一種對於命運的不解——為何那個遠方來的少女可以替代了我?而又為何這樣的命運需要我一個人來承擔?
窈七像一隻被命運捕獲的青鸞,在日月更迭之間,忘記了歌舞、鳴叫,只記得滿心的哀怨與憤恨。
所以,我覺得面具下的那張臉應該是全片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恰恰是看到了這張臉,聶隱娘內心深處那個長久以來不能釋懷的情結,一下子被動搖了。
長久以來,藏著聶隱娘心底的窈七一直在呼喊著,為什麼是我被選為刺客,為什麼我不能像普通姑娘那樣過著正常人的生活?
我想,如果有一瞬間影片中的角色真有此念,那她想到的那個「普通人」,那個她認為的參照物,一定會是取代她成為「主母」的田元氏吧。
可是面具被劃開,精精兒站在那裡,面具下露出了田元氏的臉。
我想,在那一瞬間,她們一定認出了彼此,那會是怎樣一種震撼呢。
你以為取代了自己,嫁給自己喜歡的人,過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相夫教子、鸞鳳和鳴的幸福生活的「|普通女子」,終歸也成了一個像自己一樣的刺客。
這簡直是命運殘酷的玩笑,一瞬間像看到了走上另外一條路卻殊途同歸的自己。
一個少女成為了刺客,另外一個同樣也成為了刺客。
所以,這也就能解釋為什麼聶隱娘回到客棧,被磨鏡少年療傷,從此故事開始轉入後半段。因為得知了命運這個謎底(一如終於看到鏡子裡自己的模樣),聶隱娘心底的那份執念開始鬆動了。她給磨鏡少年講了嘉誠公主的故事,最後得出嘉誠公主就是青鸞。
這個地方,也非常有意思。嘉誠公主與嘉信公主就是鏡里鏡外的另外一對兒映照。從台詞所示嘉誠公主離京遠嫁的種種細節可以看出,嘉誠公主並不想嫁進這樣一個偏遠的城池,但不得不為之。可以說嘉誠非常不自由,為了政治利益犧牲了個人。而與她相對的嘉信公主,可謂仙風道骨,來去自如,是常人想像中無所羈絆的仙俠代表。可事實上,嘉信公主一生也是在為政局穩定而默默付出著。她就嘉誠公主一樣,是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自己的國家。所以,無論是居廟堂之高或是處江湖之遠,無論選擇哪種命運(或者被哪種命運選擇),其結果也不過是殊途同歸。
所以,一個人,沒有同類固然可悲,但最可悲的,是發現自己的同類,雖與自己境遇不同,卻承受著相同的命運。這也就是為什麼,青鸞見鏡中同類卻悲鳴不已的原因吧。
以前看一本書,說中國古代的小說多半是在講「造化弄人之事」,細思來非常有道理。所謂造化,是在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它還不同於命運,而是一種高於個體經驗的因果流轉。造化之所以會傷人,是因為人執著於是,而一朝放下了執著,也就跳出了命運的羅網。
我猜想,見到了精精兒真面目的聶隱娘,真正理解了自己愛戴又怨恨的嘉誠公主,也真正跳出了小我的痴纏,從而能夠從更宏大的角度去看待這個世界。所以,影片的最後,她告訴自己的師父,自己拒而不從的原因有兩點。一點一如從前,田季安之子尚幼,而另外一點,卻不在是從前簡簡單單的「人倫」,她認識到殺了田季安這個國家會發生動亂,百姓會不得安寧。這就跳出了她自己從前的心理關隘,這是一種成年人以大局為重的思維方式,而不僅僅是因為自我能與不能。
我想,這樣的聶隱娘,是真正的成長了。
在《豪俠論》里,李德裕也提出了關於「道」的看法。文中寫道:「學道者,惟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能夠不吝惜身體犧牲,義事明主,應該是唐人觀念里豪俠的風骨了。其實影片裡的聶隱娘的確也表現出了其「猛將」一面(堪稱硬「漢」),但若考查對於明主的忠誠程度,影片裡的聶隱娘是十分反叛的。她不但沒有效忠於任何一個君主,最後還叛出師門。她最終明白,自己的命運不是任何人所造所為,自己嚮往的,自己想追求的,無需再與原生家庭清算,向前去追尋就好(與磨鏡少年去新羅)。這一點,說來是非常女性主義的。
這部影片好就好在沒有簡單把「聶隱娘」這樣一個婦孺皆知的豪俠形象符號化,而是給了她作為人的一面,尤其是作為女性的一面。她的怨、她的恨、她的憐憫與軟弱、她最終的成長都如此真實,喚醒了我內心深處在青少年時代對於孤獨和黑暗的漫長記憶。所以,我能明白,面具下的那張臉,鏡子裡的另外一隻青鸞,是命運無情的嘲弄也是最善意的寬容。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沒有誰是被刻意挑選出來承受沒有同類的孤獨。人,生而如此。
庾信有一首詩寫鏡,說「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我覺得這首詩用在此處很貼切,鏡子兩邊,是聶隱娘與精精兒,是嘉誠公主與嘉信公主。有趣的是,這首詩出現了「光」、「影」二字。或許,電影本身就是那枚鸞鏡,我們作為觀眾何其有幸,在他人的電影裡窺見了自己的人生。在黑暗裡聽到風聲一波波從螢幕里吹襲過來,鏡頭以4:3的畫幅橫向移動,左右往復各兩組。暴力驟然發生,又輕盈地結束。就像那些風掠過樹頂,帶著力度與速度,卻始終歸於無形。
爾後,聽到了巨大的蟬鳴。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