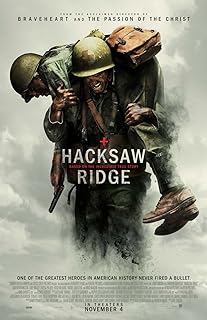電影訊息
電影評論更多影評

2017-01-06 19:17:23
一個真實的故事?
醫務兵道斯被擔架緩緩放下,他正抓著戰友冒死為他找來的《聖經》,突然天空變得透亮,擔架開始上升,影片結束在一個如此有寓言意味的鏡頭裡。梅爾·吉勃遜的《血戰鋼鋸嶺》在最後走到了和他的《耶穌受難記》相同的一邊,一個男人在接受了血腥現實的洗禮後終於來到了信仰至上的天國。
這是一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故事:來自小鎮的青年滿懷熱情奔赴戰場,在戰爭中成長。梅爾·吉勃遜在「反猶」風波被好萊塢封殺後用來自自己故鄉的投資拍攝了一部純正的美式主旋律電影(本性難移的梅爾·吉勃遜依然在影片中藉助軍官之口對一個波蘭猶太士兵冷嘲熱諷)。當然,其中不變的是大量血腥殘酷的肉體之苦,唯有超越肉體的苦痛,信仰的故事才能圓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梅爾·吉勃遜的暴力只是一種手段,通過修辭學層面上的辭格來傳達出力量,如果說在美學層面的暴力所構築的真實是帶有真理的客觀屬性的話,那麼修辭學意義上的暴力也最終只能被結構化為符號本身。《血戰鋼鋸嶺》的開篇就是火焰噴射器掃射的火龍,這段閃回剛好結束於道斯受傷被抬上擔架,一前一後形成的受難到昇華、弱者到英雄的封閉圓環,《勇敢的心》中的冷兵器、《耶穌受難記》中的木釘和十字架、《啟示》中的毒箭,是自由、博愛與尊嚴在支撐著華萊士、耶穌和瑪雅戰士戰勝這一切。《血戰鋼鋸嶺》中的道斯選擇不拿槍,他的雙手只能救贖不能殺戮,對信仰的堅守讓他超越了戰爭本身的殘酷性。在影片中導演簡單地將道斯的父親作為了其信仰的對立面。被戰爭的陰影困擾的父親酗酒、家暴,讓道斯在童年在恐懼中度過。道斯在「生父」與「天父」之間的選擇並未經歷太多戲劇性的時刻,他能用責任、愛國主義的世俗價值觀和生父和解,也能用嚴守信條和祈禱來接受天父的祝福。在因為不遵守上級命令被關入牢房時,房間上方的窗戶框如十字架般散發著光芒,道斯的掙扎真的就如同耶穌在受刑前的最後一刻,而聖母瑪利亞會來安慰他。
鋼鋸嶺只是整個沖繩戰役的最後收尾階段,在1945年日本戰敗已經無可挽回之時,美軍對沖繩的戰爭關係到能否儘快攻入日本的本土。在前期海戰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日本「神風」特工隊在空中對美軍造成了階段性困難,但美軍很快靠米徹爾航空母艦群重新掌握了局勢,這時就只剩下衝繩島南部的鋼鋸嶺了。日軍由於失去了空中和海中的主動權,所以只能利用沖繩的特殊地形做地面防禦。沖繩南部不再是茂密的叢林和密集的漁村,而是佈滿了石灰石的貧瘠之地。日軍利用石灰石築建了密佈的地下隧道,就像他們在硫磺島所做的一樣。美軍顯然過份自信了,他們在擁有了海空優勢的同時,陸上3個陸戰師軍隊也比日軍的殘兵敗將有優勢。但事實是殘酷的,美軍兩個陸戰師的進攻接連被瓦解,就像《血戰鋼鋸嶺》中道斯剛到沖繩時所面對的畫面,他們第一次感受到了戰爭的殘酷。《血戰鋼鋸嶺》是部斷裂的電影,前半部份的閃回顯得過於冗長,像是《珍珠港》的翻拍版本,伊斯特伍德的《硫磺島的來信》在處理戰時生活的手法顯然更加高明。提到《硫磺島的來信》就能想到戰爭電影常說的「視角」問題,是戰勝方的視角還是戰敗國的視角?伊斯特伍德在《硫磺島的來信》和《父輩的旗幟》中的實踐顯然不能讓人滿意,因為我們發現其中的日本人仍然是構建在某種想像性質的圖景之上,這與陸川在《南京,南京》中所犯的錯誤一樣。他受天皇思想洗腦到內心殘存的對家人的愛,這種愛擊潰了這看似堅固的信仰,但事實真能是這樣嗎?梅爾·吉勃遜全然的戰勝者視角下,包括日軍指揮官牛島在內的任何一個日本人的名字甚至沒有出現在影片中,我們看到道斯為日本兵處理傷口,這與其說是站場上的人道主義還不如說是道斯基督教信仰的展現。在影片結尾出現的一組交叉蒙太奇中,道斯手持《聖經》得到拯救,牛島卻不得不破腹自盡,基督教信仰擊敗了武士道精神,不管是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
梅爾·吉勃遜對戰爭場面的處理明顯「老派」,雖然其中不乏他喜歡的血腥和暴力。梅爾·吉勃遜放大了「突然性」,你不會知道子彈何時何地在哪裡出現,人物被擊中都是突然性的。《血戰鋼鋸嶺》中的戰爭重新回到了傳統好萊塢敘事上,就像史匹柏們所做的一樣。鏡頭和剪輯都如同教科書般的工整。回想下近年來伊戰主題的電影,大部份戰爭場面都是用手持跟拍長鏡頭來完成的,觀眾視角和士兵的視角重合,音軌中傳來厚重的呼吸聲,我們對他們的恐懼感同身受。在德·帕爾馬的《節選修訂》中導演甚至在士兵頭盔上安裝攝影鏡頭,然後將這些錄像片段剪輯成一部電影。但《血戰鋼鋸嶺》中的視角重合鏡頭非常少,在第二次進攻中出現了少量幾個但也是一閃而過。影片中道斯和戰友聯手打掉狙擊手的橋段也是標準的美式幽默,幾乎是所有好萊塢戰爭電影的標配。梅爾·吉勃遜用保守的方式來拍攝戰爭場面反而更加有力地襯託了道斯的傳統價值觀。在影片中那些殘酷的殺戮鏡頭中同樣也穿插著詩意慢鏡頭和特寫鏡頭,這讓人不得不聯想到馬利克的《細細的紅線》,梅爾·吉勃遜的詩意是關於戰靴跨過屍體、老鼠肆虐和恐懼的眼睛,而不是樹木、花草和詩歌本身。這與其說是特漢柔情不如說是戰爭暴力的另一種釋放,火焰噴射器在鋼鋸嶺最後的戰役中對摧毀日軍堅強的防禦陣地功效巨大,其巨大的火焰在吞噬著生命和罪惡,猶如《聖經》中被燒掉的罪惡之城索多瑪,上帝的榮耀終將降臨於此。
在「視角」之外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血戰鋼鋸嶺》究竟是一部「好戰電影」還是一部「反戰電影」?在梅爾·吉勃遜之前的作品中都傳達出戰爭必要性的態度來,雖然戰爭殘酷,但不經過戰爭就無法獲得自由。道斯拒絕拿槍看似是反戰主題的獲勝,但不可否認的是道斯信仰的樹立或者說建立的基礎是在暴力性之上的。每個人都有擁有自己信仰的自由,在當今新自由主義思潮氾濫下,人們愈發感覺到這是個自我中心的陷阱。道斯手持《聖經》和牛島手握短刀是否都是某種尊嚴與信仰的體現?好萊塢電影經常告訴我們,戰爭中的殺戮是必要的,因為這是為了保護我們的親人和我們堅守的價值觀。這種模式下的敘事要跳出「好戰電影」的批判就必須藉助情感的力量。所以我們看到《拯救大兵瑞恩》里犧牲戰友生命拯救這個家庭僅存的兒子以及《血戰鋼鋸嶺》前半部份的情感主線,但《血戰鋼鋸嶺》中家庭個體的犧牲與國家利益的矛盾卻相較前者被淡化了許多,意識形態上的自我救贖進一步得到彰顯。在《硫磺島的來信》中,小部份日本軍隊不可理喻地野蠻、未開化現象也許暴露了伊斯特伍德自己身為美國人的優越姿態,但本質仍然沒有溢出現實的邊界,同樣《血戰鋼鋸嶺》中的牛島和他的軍隊只是得到了一種片段化的「展示」,似如無血肉的木偶,戰爭場面中觀眾也感覺日本人似乎永遠殺不完,但美國軍隊在戰爭剛剛開始就已經成片倒下,實際情況是在沖繩戰役中日美軍隊損失總數是11:5,美軍死亡1.25萬人,這是美軍太平洋戰爭中的最高作戰損失。
牛島和他的軍隊如果不放棄防禦戰略(日本人認為戰爭中只採取防禦戰略是可恥的),美軍也許更難攻破鋼鋸嶺,電影中日本兵如同一個個鬼魅般遊蕩,奪取人的生命,道斯的夢境在現實主義的框架內反映了他對死亡的恐懼,但他從來沒有因為恐懼而懷疑信仰,救出的75條生命都在佐證著道斯對信仰的堅守。梅爾·吉勃遜的電影總是以男性主人公最終與信仰世界和諧共存作為結束,無論其掙扎的過程是多麼的血腥與冷酷,這些足以讓觀眾窒息甚至避之不及,但最後他還是會伸出雙手來擁抱現實世界。單就戰爭本身來說,《血戰鋼鋸嶺》在呈現殘忍的殺戮時卻沒有在個人救贖之外給予戰爭更多的反思,在敵我陣線分明,主人公「不死」前提的引導下殘忍的殺戮也變成了和平年代過剩的男性英雄主義的譫妄,但和平不能單靠信仰來維護,戰爭的批判也不能僅侷限在「非正義」層面,任何對人性善的歌頌都不能忽略掉惡的另一面,否則道斯從鋼鋸嶺黑暗地道中離開後見到那神啟般的光明也不過是一片幻影。
評論